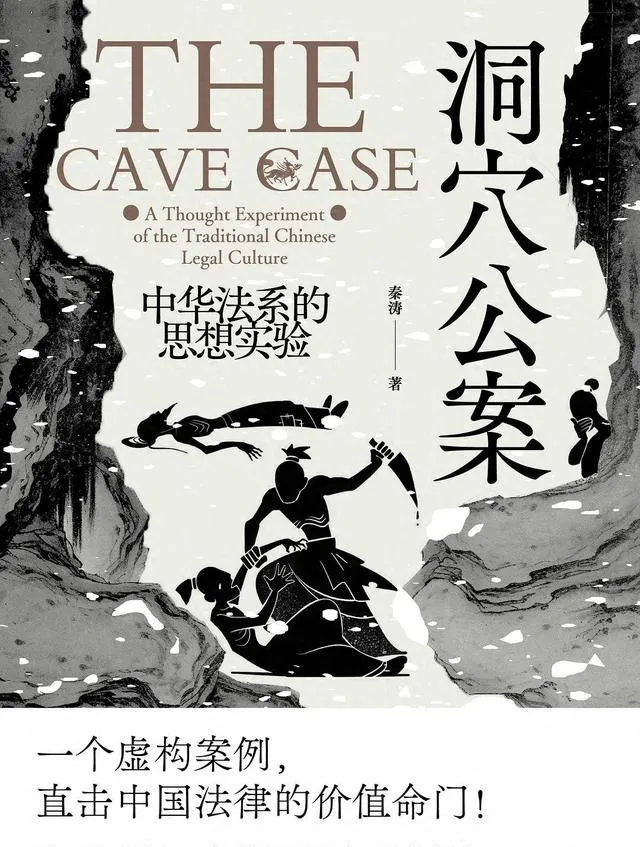
【洞穴公案: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秦濤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4年5月出版,192頁,69.00元
作為個案的洞穴
洞陰縣的大旱,從華朝本元二年的五月以來,已經持續了將近八個月。大旱引發的大饑荒已經奪走了將近七千條人命,要知道全縣總人口也不過十一萬。政府的賑災又遲遲未到,逃荒幾乎成了洞陰縣百姓想要活命的唯一選項。到了十二月,一對名叫陳千秋、陳祥的父子在把家裏事情安排妥當以後,帶著所剩無幾的糧食也踏上了他們的求生之路。他們的目的地是最近的洞陽縣,但前方那片無人荒原正等待著他們的穿越。
在路上,陳氏父子遇上了一對楊氏兄弟。這對兄弟也是洞陰縣的災民,因為在無人荒原裏迷了路,再加上他們已經無糧可吃,兄弟二人實在可憐。陳氏父子先是勻出了一些糧食給楊氏兄弟,隨後答應了他們結伴同行的請求。傍晚,四人找到一個洞穴,準備在這裏歇腳,往裏一看,裏面還有一個逃難的醫士,於是,五人一起夜宿於此。
但就在這個夜晚,無情的暴雪席卷了整片荒原。第二天一早,五人發現洞口已經被封。楊氏小弟不信邪,非要鉆出去看看,結果再也沒有回來。剩下的四個人覺得情況不妙,哪裏還敢輕舉妄動。五天後,全部糧食吃完了。又過了六天,父親陳千秋餓暈過去,醫士診斷,三日之內得不到食物,陳千秋必死。經過一番內心掙紮,陳祥最終選擇殺死了楊氏大哥,用他的血肉救父親。
提問:陳祥是否有罪?
以上便是法律史學者秦濤的【洞穴公案】設定的故事背景與案情梗概。對於「信法律、得永生」的人來說,陳祥殺人一案幾乎鐵板釘釘,沒太多值得思考的必要。但形成對照的是,在秦濤虛構的那個時空裏,這個案子卻激起了全國上上下下的關心,以至於朝廷不得不啟動了集議制度。十四個官員在集議這個平台上,輪流發表對此案的看法,唇槍舌劍,好不熱鬧,儼然就是古裝版的【十二公民】(徐昂導演,何冰、韓童生主演的電影,2014年上映)。
如果僅僅就這本書寫了什麽而言,介紹就算完了,但總有人不滿足於平面的復述,而試圖看出更多立體的圖景。當然,任何文本的解讀,角度都是無窮的,但搞清楚作者的思路始終是第一步。註意,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這個標題非同小可,秦濤是怎麽駕馭的?他的這種駕馭方式和前面講述的案子之間有無內在關聯?如何理解這一關聯?只是秦濤的主觀建構嗎?但又是什麽塑造了秦濤的主觀建構?此外,從方法論上看,這本書是一個個案研究的套用,用個案切入作為整體的思想史,除了開腦洞,還有別的意義嗎?這些問題的提出將迫使這本書從「詞」轉化為「物」,並進而成為我研究的個案,而我想做的,是追尋個案的盡頭。
不只是「個」案
我們再來看一樁命案,也發生在洞穴深處。
在一個叫做紐卡斯國的地方,有一個洞穴探險協會。一天,協會裏的五個成員,相約前往一個石灰巖洞穴。不料就在他們深入洞穴時,發生了山崩,五人全部被困。探險者一去不復還的跡象往往暗示了某種不祥,他們的家人第一時間聯系了協會。一支由工人、工程師、地質學家、醫生、神父等人組成的隊伍迅速趕到了出事的洞穴。但救援難度大大超出了預計,接連不斷的山崩不僅拖慢了救援的進度,而且還造成了十名營救人員的喪生。這一切都讓這五人脫險的希望變得日益渺茫。當救援進入到第二十天時,救援隊終於與探險者取得了溝通。但興奮轉瞬即逝,救援隊說,即使一切順利,救出他們還需要至少十天,但受制於客觀條件,補救無法送達。探險者們頓時傻了眼:剩下的食物撐不了幾天了。
這時,五個探險者中一個叫做威特莫爾的人提議,以抽簽的方式決出一人,為四個同伴「獻出」自己的血肉。殺死一人,保全四人,雖然手段極端殘酷,但結果可以接受,因此,其余人也就同意了。但就在輪到威特莫爾抽簽時,他忽然反悔了。這怎麽行呢?旁邊的人代替他抽簽。求仁得仁,不幸的那個人正是威特莫爾。他被殺了。靠著威特莫爾的血肉,其余四人頑強地等到了救援隊的抵達,那時距離威特莫爾被殺已經過去了九天。當這四個幸存者走出洞穴時,等待他們的除了醫院的治療與休整,還有法庭的審判。
這個故事同樣虛構,它取材自美國法學家富勒在194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Lon L. Fuller,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Havard Law Review , 1949,62[4], pp. 616-645)。富勒不僅假想了案情,還設計了五個法官對此的觀點。這些觀點並非信馬由韁,而是富勒匠心獨運的產物:他力求讓每一個法官代表當時已知的法學知識體系內的一種基本觀點,例如,恪守形式邏輯、探尋法條背後的立法精神、職業主義與社會常識的兼顧,等等。對於法律人,這些觀點差不多都是老生常談了,都很有道理,就像人們常說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現在的問題是面對一個具體的情景,「公理」和「婆理」究竟誰更有道理?這就需要仔細分辨不同道理相互的差異、道理與事實的關聯,以及預測實施的後果。因此,五位法官的觀點不過是「項莊舞劍」,富勒在意的「沛公」是讓我們具象化地理解不同法學思想之間的原則性分歧。
1998年,另一位美國學者彼得·薩伯沿著富勒的思路,在吸納了過去半個世紀法學思想最新發展的基礎上,又續寫了九個法官的意見。前後十四份法官意見集結一體形成了一本書,這就是【洞穴奇案】(Peter Suber,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Nine New Opinions , London: Routledge, 1998;中譯本見[美]彼得·薩伯:【洞穴奇案】,陳福勇、張世泰譯,九州出版社,2020年)。它已經成為向世人展示法學思想復雜性、多元性、論辯性的一部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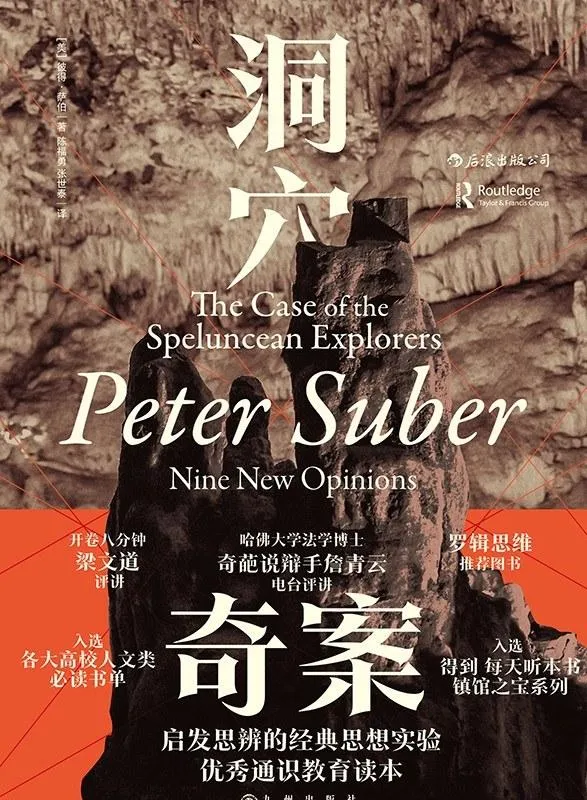
彼得·薩伯著【洞穴奇案】
既然有【洞穴奇案】的珠玉在前,為什麽還要再來一個【洞穴公案】?二者在行文結構、案情設定,甚至書名上都十分相似,難道後者僅僅是前者的中文化,甚或山寨?事實上,這取決於我們如何認識「思想」。當我們談到「思想」時,常常會有高高在上之感,是因為下意識裏我們將「思想」推向抽象的、絕對的、普世的境界,正是如此,我們才會認為「思想」是大寫的真理,是代上帝立言,但問題是,就發生而言,任何事物都是特定情境的產物,都有它存在、發展的外部限制和內在邏輯,「思想」也不例外。
從這個視角再來審視【洞穴奇案】,就會意識到雖然這個故事是虛構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是天外飛仙,事實上,它就根植於富勒、薩伯所在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世界。難道不是嗎?初審法院、上訴法院、陪審團、財產權、契約……這些在故事裏閃現的細節無不暗示了這一點。也就因此,【洞穴奇案】所傳遞的法學思想也相應地打上了特定時空的烙印。一個長期以來被人們視若當然的普遍性問題被轉化為了地方性知識——「奇案,是特定法文化的產物」(導言11頁)。秦濤撕開了第一道口子。
由於消解了普世主義的前提,接下去的事情就變得勢如破竹。那些過去只能委身於【洞穴奇案】的敘事邏輯才能被理解,並反過來,印證、強化這一邏輯的材料一下子容光煥發,因為它們開始有了自己的主體性。這就是秦濤在「導言」中所說的提問方式的轉變:從「如果洞穴奇案發生在古代中國,將會得到怎樣的審判」,轉向「假如為中華法系編織一個自己的洞穴奇案,將會有怎樣的案情」(導言11-12頁)。這是他撕開的第二道口子。
還有第三道口子。秦濤以【洞穴奇案】為外觀基準,對東漢末年管秋陽兄弟殺人案及其審判加以中國式改造,使兩樁洞穴案件互為他者,彼此襯托。之所以要這樣,在於要最大程度地強化二者的對比。只有這兩個案子的對比足夠強烈,作為它們背景的中西法律制度、思想、文化的對比才可能深入人心——可見秦濤的精打細算。這當中肯定會有偏頗,甚至扭曲,但為了凸顯問題,卻是一種必須且合理的手段。中華法系是在這樣的邏輯下被一步一步推到舞台中央。
眾人伸長脖子,仔細看了半天,才認出主角的儀態:人倫。
不只是個「案」
人倫是一個與儒家相聯系的概念。在儒家看來,雖然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系萬千種種,但最重要的,莫過於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他關系都可以視為這四組關系的衍生,例如,師生關系就可以比附於父子關系。因此,用這四組社會關系基本上可以包羅一個普通人遭遇的種種情景。當然,如果這個人介入到了政治領域,還需要加一組關系:君臣。這就是孟子提出的「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最為重要,是為「三綱」。因此,人倫指的是人與人相互關系中最重要的部份。
但人倫並不只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它還意味著一套行為準則,因此具有很強的規範內容。這種規範內容,具體而言,就是把等級制度嵌入到輩分、年齡、親等、性別等領域,形成了尊卑、長幼、遠近、男女等關系架構,從而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總是籠罩在不同形式的支配與被支配之中。在儒家看來,這構成了社會秩序穩定的微觀基礎。以「父為子綱」為例,在家庭內部,很長的時間裏,父子之間基於智力、體力、經驗的差別,是領導、教育、指導的關系。這一原則稍作轉換,就可以為官僚政治、中央集權制提供樣版(參見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14頁)。瞿同祖先生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闡述了儒家的這一秩序觀:
儒家認為這種存在於家族中的親疏、尊卑、長幼的分異和存在於社會中的貴賤上下的分異同樣重要,兩種差異同為維持社會秩序所不可缺。儒家心目中的社會秩序,即上述兩種社會差異的總和。……貴賤、尊卑、長幼、親疏都有分寸的社會,便是儒家的理想社會。貴賤、尊卑、長幼、親疏無別,最為儒家所深惡痛絕。(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29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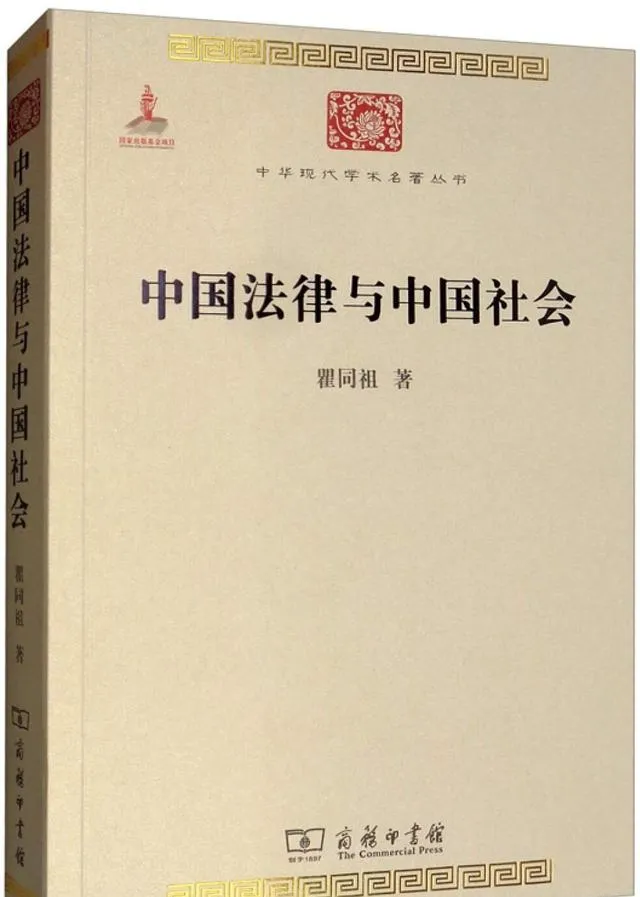
瞿同祖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由此可見,傳統中國的社會規範是以特殊主義為底色的,秦濤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之所以要利用管秋陽兄弟殺人案,就在於這個案子折射了人倫這一因素(兄弟在五倫之內,被殺的人在五倫之外)如何影響中國古人看待殺人這個問題。但是既然已經以案說法了,為什麽不幹脆把事情做絕,讓人倫因素在案子中發揮的作用更加淋漓盡致?再度基於論證價效比的考量,秦濤將「兄弟共謀殺死同伴」的情節,改為了「孝子為了救瀕死的老父,殺死一個陌生人」。將同輩的兄弟替換為了父子,從而引出了傳統中國核心價值觀中的核心:孝道。此時,【洞穴公案】的矛盾沖突就成了:兒子救父親,當然符合孝道的要求,但在當時的情景下,卻只能以殺死一個陌生人作為手段,國法不容。圍繞著這個兩難,所激發的討論指向國法與民本、經常與權變、法律與道德、「忠」與「孝」……而這些正是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目之所及之處(更細致的對這十四個觀點代表思想流派的分析,參見朱林方:【假如洞穴奇案發生在古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5月22日第七版)。
我對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了解很少,不敢班門弄斧,只好虛晃一槍。但我卻可以,也應當揚長避短,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人倫作為傳統中國法律思想的興奮點,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麽?
不妨再折返一下【洞穴奇案】,我們會看到這個問題的映像。這五個探險者,除了都是探險協會成員的身份以外,是否還有別的身份關系呢?不知道,富勒、薩伯沒寫。為什麽沒寫呢?你說富勒、薩伯忘了,但這是你額外加的一個假定,如果這樣做也可以的話,我們可以解釋任何東西。所以,要調整思路,還是要從富勒、薩伯已經寫了的內容之中尋找理解的線索。那麽,他們寫了什麽呢?緊急避難、管轄權、期待可能性、嚴格責任、犯罪故意、司法部門對行政部門的警惕……這也太「現代法學」了!沒錯,富勒、薩伯的【洞穴奇案】呈現的是法律人立足於一套自給自足的法律規則體系,透過概念分析的技術手段,讓法律像一架機器一樣精準、高效、理性地運作的樣子。在這種對事不對人的語境裏,探險者彼此之間有什麽關系身份並不重要。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僅僅限定在文本層面,還是太淺了,而應該意識到,富勒、薩伯其實不自覺地「匯報」了他們所在國家的主流法律文化。同樣的問題:這種法律文化的社會基礎又是什麽呢?
這兩個問題很大,在一篇書評裏,我充其量只能勾勒一條理論的粗線索,但我力圖把這兩個問題放到一起,同步處理。在【洞穴公案】的「外一篇」裏,秦濤看似漫不經心地寫到,華朝的法律規則體系,除了普遍適用的成文法典,還有專門針對君主、官員或民眾的其他法律淵源(141-146頁),但在我看來,整本書的一條暗線正是這些規則之間的效力賽局。應當看到,成文法在華朝的法律規則體系裏,並不居於絕對支配地位,人倫完全有可能幹預它。當然,華朝就是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就是華朝,這實際上暗示了,傳統中國的治理是多元規範渾然一體的狀態(傅衣淩:【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而這一點在【洞穴奇案】中被大為弱化了。盡管諸如社會輿論等其他社會規範仍然存在,但它們已經無法繞開法律或法院而單獨地發揮作用(漢迪法官的陳詞就是證據)。這表明,法律作為基礎性制度在西方現代國家紮根的現實。
為什麽會是如此呢?從傳統中國這一面來說,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有限性有關。受制於生產力、技術、資訊、交通等客觀約束,傳統中國的公權力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強勢,因此「皇權不下縣」不可避免。這就勢必留出了一片廣袤的治理空間給社會,也就是儒家說的「齊家」。而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村莊生活方式,又給「齊家」提供了條件。這一國家與社會二元化的結構模式被費孝通先生概括為「雙規政治」(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商務印書館,2011年,367-397頁)。在常態下,這兩軌並列不悖,甚至可以相輔相成,然而一旦出現了類似【洞穴公案】裏的陳祥殺人事件,這兩軌無異於發生了一次對撞。因此,全國上下熱烈關註實際上反映了對兩軌界限重新界定的訴求。顯然,對於官員來講,他們不可能只談國家成文法典,而必須綜合權衡各種法律淵源適用的利弊。
再看現代西方國家。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國家是社會之外的一個單一行動者,二者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當然,這不是與生俱來的,伏爾泰曾經抱怨法國的法律,說他旅行時經過的法律體系的變化比他換的馬還要頻繁,他實際上說的是國家法律不統一的麻煩,而背後是中世紀以來政治權力的割據化、封建化的狀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一個全國性,乃至跨國的大市場開始出現,規則統一變得迫切,並且可能。從十八世紀之後,西方國家逐漸走上了理性化、自主化、正規化的歷史行程,有學者稱之為「官僚機構化」(參見[英]麥可·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二卷下,陳海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相應地,法律作為國家治理工具不再需要與道德、習慣、地方政治勢力等競爭,更不需要依賴它們而存在,因此,法律實證主義的大行其道折射了國家權力的集中。雖然從常識或者歷史的角度來說,法律與倫理道德不可分割,但就規則適用而言,它們分明是兩回事,不可混淆。這就是為什麽【洞穴奇案】特別對法學院學生口味的原因,因為那裏矗立著「法律人的城邦」(強世功一書名)。
一旦我們不再把【洞穴公案】【洞穴奇案】裏的敘事僅僅看做語詞,而視之為社會歷史實踐的投影時,我們或許會有一種驚心動魄之感:原來兩本書談的都是國家能力問題,只不過秦濤把問題放在前現代的中國背景下,而富勒、薩伯放在現代的西方背景下。這何止是中西之別,也是古今之變。
不只是「個案」
「一本小書竟然被你看出這麽多東西,是否有過度解讀的嫌疑?」一定會有人這麽說。類似的質疑可能也會指向秦濤:「用一個故事來講述思想史,是否有無中生有的嫌疑?」這兩個質疑關乎個案研究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我和秦濤是一根繩上的螞蚱。我需要做出回答。
基於個案的場景內容,一個抽象的,往往也是不明覺厲的道理可以借助一個具象的,因此也是普通人容易感知的方式娓娓道來。一個好的個案研究甚至可以登堂入室,成為這個理論的專屬代名詞。典型的例子,今天討論中國轉型背景下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糾結,幾乎繞不開「秋菊的困惑」(參見蘇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24-42頁)。因此,個案研究對於追求徹底解釋的社會科學,真是一個好幫手。
如何做個案研究呢?一個幾乎無需思考的答案就是實地調查(參見賀雪峰:【在野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實地調查肯定是做個案研究的一種手段。事實上,只要實地調查,遇到的全是個案,因為調查,說到底,就是向具體的人打聽情況,這些情況往往是受訪者的遭遇、情感、困惑。單獨地看,這些資訊或許都是雞零狗碎的瑣事,但換一個視角,其實也是社會全景裏的一個局部,因此,只要順藤摸瓜,總能抵達社會問題的深層邏輯。而且作為調查者,我們就喜歡聽這種有血有肉的故事,不僅出於尋找好的素材的功利性考量,或許也源自人類喜歡「八卦」的天性。
當然,有的調查不可能去往實地,但找到實地的替代也是有可能的。以孔飛力的【叫魂】為例,1984年,他來到北京,一頭紮進故宮裏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陰差陽錯地拿到這堆叫魂案的材料。後來孔飛力回憶,「之所以會註意到叫魂事件,是因為它的材料比較完整,從開始到結束的檔案,包括很小的細節都有,這是一個理想的案例,非常值得研究」(【孔飛力訪談:我不相信有完美民主】,波士頓書評網站2024年1月13日刊)。孔飛力同樣在做實地調查,只不過他是穿越回了1768年。在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和社會學有互通之處,只不過一個著眼於過去的社會,另一個著眼於未來的歷史。
但個案研究是否只是這種形式調查的特權?對於這種調查來說,資訊的高度集中內在於場景本身,因此,才會有「進村找廟,進廟找碑」這一實地調查近乎自嘲的經驗總結。但有的問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似乎隨處可以感知,但肉眼無從觀察,訪談就更談不上,而這些問題往往又居於整個知識體系的中心位置,不應回避,例如,國家的發生、市場的出現、制度的變遷……能不能找到一個可以為普通人經驗感知的方式,說明這些問題的道理?思想實驗的重要性就顯現了出來。
思想實驗仍然是一個個案,但這個個案並不是一個物理存在,而來自研究者的構想。註意,是構想,不是亂想,它也有經驗基礎,而且要符合事理邏輯,這勢必要求研究者掌握龐大的知識體量。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他能夠按照他的某種思想線索將一些看似沒有關聯的材料從容不迫地「東拉西扯」,這實際上就是操縱實驗條件,從而達到抓出問題要害的目標。所以,做思想實驗的前提一定是研究者自己想通了,剩下的就是組織材料呈現想通的過程、邏輯。這些都決定了思想實驗是高度理論性的。
【洞穴公案】就是這樣。秦濤從本科時代就在琢磨的問題,直到十多年以後才恍然大悟,這種感覺就像柯南每次想通了案子,腦袋背後就會閃過一道光。但這道光牽引的不是時間,而是事理邏輯。所以,雖然【洞穴公案】呈現了中國傳統法律思想史,但秦濤拒絕了「率由舊章,不愆不忘」的歷史模式。相反,他無視歷史,只有這樣,才能讓散落在歷史長河裏的各家各派齊聚一堂,以「獨幕劇」的形式(關於思想史的「獨幕劇」的寫法,參見周赟:【西方法哲學主題思想史論:一種系列劇式的敘述】,法律出版社,2008,第3-5頁),上演一出關公戰秦瓊的大戲,中華法系的價值命門才可能凸顯。我做了一個未必很準確的統計,在這本十萬字上下的小書中,秦濤使用的古籍大約有五十部,就是在這五十部的古籍中,他縱橫恣意地書寫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思想及其表達的理解。我忽然想到,這與蘇力【大國憲制】處理史料的方式完全一致(參見【大國憲制】,554-569頁)。在這個意義上,【洞穴公案】的副標題似乎也可以是:歷史中國的思想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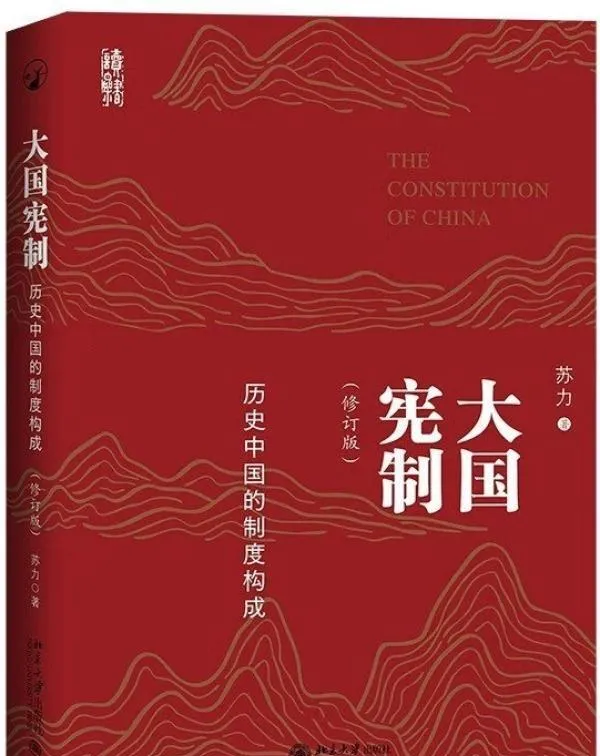
蘇力著【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修訂版
因此,不管是秦濤的【洞穴公案】,還是我對這本書的解說,都是借事說理。至於這個「理」有多大,取決於且僅僅取決於我們對「事」的理解深度。也許我們確實沒有實地調查,但誰又能否認這仍然是個案研究——他的書基於一個虛構的案子,而我的研究則將他的這本書作為起點。因此,個案研究的物件、形式、套用範圍不是一成不變的,也談不上有一定之規,而應當根據我們研究問題的實際需求進行選擇、調整和組合。重要的仍然在於提出理論,這建立在我們對世界要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反思力的基礎之上。
作為個案的自己
一次私下聊天時,我曾經問過秦濤,【洞穴公案】的預期讀者是誰?這個問題關系到這本書的定位。盡管在他看來,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但我想,更多讀者還是傾向於將它視為一本有趣的通俗歷史讀物。而像我這樣將其視為理論作品,屬實暴露了學院派的較真、無聊。
我不想太過糾結這本書學術意味的濃或淡,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我卻想談一談這本書為什麽是有趣的,以及一本有趣的書意味著什麽。當然,首先是形式。相對於今天流行的「大部頭」著作,這本書確實太單薄了,但它其實是「穿衣顯瘦,脫衣顯肉」的典型。一個虛構的案子,十四個官員輪番上台,這是一出戲,但背後卻是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內在張力。所以,它的表述一定是簡潔明快的,而問題卻一定是復雜深刻的,這就將眾人置於一個可以無限思考的空間之上。從一個角度來說,這也可以視為秦濤在向我們示範如何更有效率地傳遞知識資訊:重點不在於規定知識大寫的「真」,而在於構築一個問題意識明確,但邊界開放的場景。因此,講好一個故事非常重要。
但講故事的人更加重要。盡管秦濤在後記中說這本書算是「有趣的學術論著的第一個嘗試」,但事實上,這種寫作風格對於他而言,早已稀松平常。證據是大量的,不僅是他的普及讀物,也包括一些聽上去本應該很嚴肅的學術討論(秦濤:【天理·國法·人情:禮法傳統中的獄訟制度】,孔學堂書局,2019年;這本書也是故事連著故事的寫法,而且,在「唐朝:一個虛構案例的命運」中,秦濤用虛擬案例帶出唐朝獄訟制度,他已經有意識地對照【洞穴奇案】了)。但容我大膽猜想,在今天這種日漸沈悶的學術環境下,這種風格幾乎註定會讓秦濤陷入某種擰巴之中。並不清楚中間發生了什麽,只是當我讀到「如何從個人的興趣出發,憑借這麽多年積累於身的種種雜異資源,完成只有‘我’才能完成的工作」時(160頁),我分明感受到了一股破土而出的力量。也許秦濤終於領悟了,那些在外人眼裏早該被剔除的「不務正業」——無論是他過去的辯論賽經歷,還是他正在進行中的小說創作——只能說明他走的是一條與大多數人不一樣的路子。但不同的路上都有各自的風景,因此,應當尊重自己的經歷,並將其視為自己的大後方,不斷開掘,直至放大。就像只有回到中國本位,才能看到【洞穴公案】,同樣的道理,只有擁抱自己,才能成為法律史學者的秦濤。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與它的作者是同構的。
因此,【洞穴公案】的背後不僅是生生不息的廣土巨族,其實還折射了觀察、構想這一問題的秦濤。但這一視角何止局限於【洞穴公案】?實際上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共性。研究者在自覺表達自己的思路、觀點與結論的同時,也在不自覺中流露著自己的偏好、經歷與情感。所以,人文社會科學一定是「有我之知」(陳嘉映語),「我」是提出問題和探究問題的根源。
正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對個案研究有了新的體會。個案的盡頭到底是什麽?是個案的那個故事嗎?是故事裏的那個邏輯嗎?是邏輯背後的理論嗎?是人,是一個想活得明白的人,借由對更多人的關懷,抵達他可以感知的世界的邊陲。他相信一切知識都可以還原到具體的人,也只有還原到具體的人,才可能理解知識的幽微,理解人背負著沈重的肉身和對不朽靈魂的渴求,理解這個世界的豐富性、歧異性、不確定性。個案是他與世界對話的紐帶,而他自己是第一個,也是最堅實的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