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奕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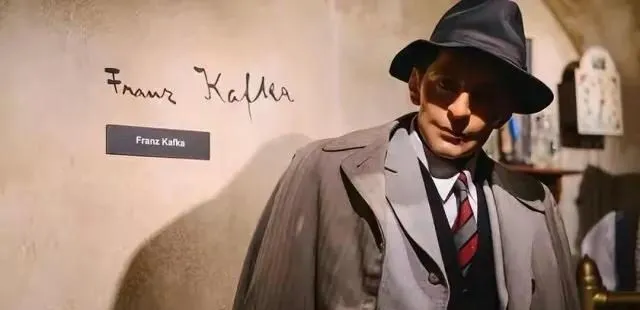
卡夫卡像
一
残雪将审判一书的核心理解为两种意志的对抗,其中的「两种」之意并非指K和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象征性地指向人的内部和外界力量。故事开始的情节就是在承接这两种意志的对峙。我在对【城堡】的初解中说过,卡夫卡就擅长制造矛盾使得人物关系被迅速地建立了起来,因为这两种状况也就是卡夫卡在现实中的所感。现实中社会关系的复杂荒诞已经超越人心感知的最大敏锐程度了。由于卡夫卡是读过尼采作品的人,所以他很清楚要用什么来抵御这种社会关系的进击。于是他把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创造成一个几乎与小说情节中所有其他人物都有矛盾或者是对抗的人,审判中的K与他的叔叔亦然。面对寓所突然闯入了来针对自己的陌生人——自诩自己接受了来自上方莫大的权力来逮捕K的捕手,K非常不屑,因为他漠视了他们上方的权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权力显然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了久也很快就会崩溃,这就是卡夫卡制造K无罪受捕的原因,否则对方是有理由来逮捕他的,也就是他们上方的权力与他有了直接的联系,K没有理由去拒绝它。
然而,与K理解相反的是,从捕手到监督官——从上至下都认可了K的受捕的合理性,而面对K的反问,他们不是回避问题,就是试图抢占逻辑上游。监督官面对K的请求和解,他不但不尝试去缓解关系——即便事态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反而对他说,你把一切都看得太简单了,你应该对此感到绝望。从这种角度看,监督官的形象已经变得十分严肃,他的身份已经开始脱离了实在的状态,变成了人性中恐惧的渊源——如果一种意识已经陌生到任何人都看不清它,那么它带给人带来的直接印象就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接触的深渊,【城堡】中试图表达的就是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意志对抗中扮演着十分微妙的角色,因为说不清这种情况是会制止这种对抗进一步发展下去,还是反却使其深化。于是K处于一种半和谐的状态,他的名义上还处于被捕状态,但是他的人身自由暂时得到了解放,这但这势必会引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K获得者这种至少是被赋予了的人身自由,那他就承认了对方对他的权力——至少在这段自由期间内——是合理的。K从监督官那里获得的参加初次审庭的时间是星期日,而庭审地点是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位置,这让人或许会联想到这些审判机构带有象征性的宗教特征。相比于【城堡】而言,卡夫卡为审判机构的形象保留了一定基础。在到达庭审地点之前,K一直与这个机构强大的陌生性与虚幻性进行斡旋,我们从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
「不过最后他还是踏上了最开始看到的那段楼梯,脑袋里同时回响起看守威廉姆曾经说过的话,法律是由罪行所牵引的。既然如此,预审调查室肯定就在K随意挑选的这处楼梯上面了。」
在任何读者看来,这段话多少都有点唯心的成分,但事实是,审判机构的形象只不过是K内心的深度幻想的一个侧面,就好比【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即便可能性在时间中无限地分岔,但我们还是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一种。说到底审判机构的任何形象或者性质都是依K而定,它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极力的定性。
然而,K找到了庭审现场之后,他发现,庭审的规模不过如同一次小集体会议;庭审的地点也十分令人尴尬,是在一个阁楼内。卡夫卡就通过特意去弱化恐惧对象的现实状态来制造出可以无限延伸的恐惧,因为现实呈现的审判机构露出水面的部分极其有限,而在水面之下的机构就会像冰山下部一样庞大——最可怕的是,还是它们还可能只针对你一个人,只不过其暂时被对方的意志所掩盖了。
K在庭审上措辞激烈且尖锐地批判了预审法官和可能的高级法务人员的低价作风,但在发言过程中,几乎底下的所有的议员——包括台上的预审法官——都默不作声。这种情况往往带给演说者的打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忽视了K的针对他们的意志,或者说是有意以沉默对其进行否认的。K面对这种否认,他不能再依靠思想为自己辩护,因为对方已经沉默了,并将始终保持沉默。在K的发言过程中,台下有人带头进行喝彩,其他一些人(不是全部)才发出些动静,这表明K面前展示出的是虚假的、经过伪装的,这更给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末了,整个庭审过程中,一言未发的预审法官——他还被K当众讽刺过——立刻站起来追随K出门,并对他说,或许你此刻还没意识到,就在今天,你主动剥夺一场审讯调查本应给逮捕者带来的好处。现在K的困境就在于,他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因为他的意志一直处在这个抽象的、虚幻的权力机关的强权的压制之下,他根本进行不了反抗,尽管离开之前,他对预审法官反击道,他们所有人都会在K的行动下得到法律的制裁。
二
K的叔叔得知K受到指控一事后,他带K去见了自己的一名律师好友。K并不认为他的案子已经严重到需要找律师帮忙了,因为他是被无罪指控的,如果反而去过分重视它的话,就意味着连K至亲的人都承认K是有罪的,至少是犯下了什么严重的过失,从而导致K的刑事诉讼。K在律师分析案子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和他的女儿莱妮在一起。当然K即便有外人的辅助,情况也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律师下面的还有一个委托人叫布洛克,是一个商人。他向K透露说,律师的接手并没有使案件的情况得到多大改善,然而律师一再强调,他为商人打的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斗。这也引出了后文K希望去解雇这个律师。这其实也是很微妙的一点,如果让K独自面对这一切,成功的可能性或许反而更大,一旦有了外界力量的加入,这种可能性反而就不可企及了,因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不可预知的个体上就是一种相当冒险的做法,还有一点是自己的权力被这种方式约束了,律师承担为K摆脱这个诉讼的任务的同时,原本属于K的对此事的主导的权力就转移到了律师的手中,现在他更可能地会被事实左右了。
K回到自己的银行办公室后,他经一个工厂主的介绍去了一个画家那里。这个画家说自己是为那些法官画像的,自己也和法院有所往来。K对画家说,我的无罪并不能让审判变得更简单。画家也对K说,一旦有人让K强制性与法院产生联系后,K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进入无罪释放的结局了,因为他们总能找到理由——或创造出理由——让K的名义下背负着罪责。他又对K说,如果我在这张画布上并排画出所有的法官,并且你在这幅画面前为自己辩护,你获得胜诉的可能性都比真实法庭上要高。
可谁知道呢,画家本人也是K必须承担的恐惧的一部分——画家的住所就紧邻着上次庭审地点,就连门口围观的女孩子也属于法院的一部分。画家说,统统都是法院的一部分。K这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他必须与外界对立起来,因为外界任何人都受着某个强大意识的牵引,正缓缓向K涌去。现在不他不得不用手抵挡这一切了。
回到银行后,K被委任去接待一位意大利客户,要亲自带他去参观大教堂,可到达之后却发现客户没来。他只身一人走进幽暗潮湿的教堂内部,他见到了教堂的神父,正当他在想神父应该是在做布道时,被他溘然叫停迟疑离去的脚步。他喊出了K的名字——他是监狱神父——所以对K的案件有所了解。此刻就如我所说,K的命运所面临的严肃性已经处于了一个最庄严、最具有审视意义的时刻了,仿佛在遥远的地平线后面、在遥远的城市里、郊野处正升起数万种目光聚集于K的一身,正等待着他最终的结局。此刻我们可以猜到,那个意大利客户一定程度上是受神父派遣的,小说的严肃性已经上升到宗教层面了——「在他看来,大教堂的宏大体量,几乎已经要超过人类个体的忍受极限了」。随后神父对K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整部【审判】的焦点,卡夫卡曾把它单独抽离出来作为一个短篇,篇名叫【在法门前】。我在前面说过,这时的审判机构已经类似于一个宗教组织了,不论是作为法的守门人,还是试图进入法的大门的人——前者的义务似乎于试图入门者相连了,因为他守的大门是专为专门为试图入门者而设的,可是他又不知道试图入门者应该在什么时候进入大门,因此试图入门者到死都没有进去——守门人的义务与他的事实所为相违背,守门人可能只是站在法的大门的背面认为,入门人是无论如何都进不去的,因为里面有一层比一层更大的障碍,里面的守门人也有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而试图入门者的目光却能透视着所有的门,看到法的中心射出的永不熄灭的光线。从这一点层面上看,守门人才是那个真正被蒙骗的人,他已经被自己义务所束缚住了,不能离开法的大门;而试图入门者是自由的,但他唯一的自由就是通向法的门内,寻求法的解释,但现在他连这点都无法满足了。K的案件的审判结果会从大街上随便哪个人口中说出来,他的命运的审判已经不再是仅由整个审判机构来操控了,它将由任何自然人操控。现在,K必须忍受这件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
几乎是在K的31岁生日之际,他被两个不太像是刑事执行人员的刑事执行人员带到了郊野,接受了死刑。讽刺的是,他在被逮捕的那一天,也正是他的30岁生日,在这一年内,他始终都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过。故事的最后。K从一栋楼的顶部看到一个俯出窗外的人。他想,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心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想要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人类个体,还是全人类呢?此时K心中渗透出的交织的希望和绝望,已让被救赎的可能性变得深沉而博大了。
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