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中法建交迎來60周年的重要節點。回望來路,兩國間良好的交流氛圍為無數個體交往創造了條件,而在這場邂逅中,還有更多屬於個體的奇遇值得講述。60年中,無數中法女性於兩地文化間往來穿梭,在與未知周旋的過程中,尋找著自己的價值和位置,也逐漸打磨出屬於自己的閃耀之美,成為推動中法相向而行的美好力量。三八婦女節之際,我們邀請了7位中法女性,來講述中法交往中那些屬於個體女性的奇遇與閃爍。
福樓拜、雨果、加繆、莫泊桑、瑪格麗特·杜拉斯、柏德烈·莫迪亞諾、安妮·埃爾諾……站在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法國文學大師背後,黃雅琴如是說:「我一直認為無論是做編輯還是做轉譯,最璀璨的都是原作者。」
黃雅琴是一位出版編輯、譯者,在這兩種身份中自由穿梭,暢遊於法語文學的大海中,黃雅琴用文字構築了屬於自己的烏托邦。今年,她邁入了從業以來的第15年,法語已經成為她的一種生活方式。
【情人】中的名句:「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剛學法語時看到這句話,黃雅琴只是覺得很酷,而今頭頂已有白發的她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坦言,2021年拿的傅雷轉譯獎救了自己。在此之前,她也懷疑自己,「這樣一本接一本翻,到底有什麽意義?」但拿獎的那一刻,她感覺就像碰到了一座小島,上去站了一會,又可以繼續遊了。
現在回過頭看,她形容自己是西西弗,想前進就要推石頭,可能今天石頭推上去了,第二天又落下來,但至少她在推。她願意就這麽天天推。黃雅琴身上有一代文化擺渡人的共性:堅韌,勤奮,孤獨。在日復一日的庸常堅守中,她逐漸成為自己的燈塔和島嶼。
以下文字根據黃雅琴口述整理。

黃雅琴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永遠未完待續
我選擇法語,大概是冥冥之中註定的。高三填誌願,我就蠻想學語言的,後來我又想起語文課文【最後一課】裏說的,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最精確的語言,所以下定決心選了法語。
讀了大學之後,外教給我們上歷史課,用了很多時間跟我們講「南特赦令」這一段歷史,當時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對於任何的思潮、宗教或者主義,法國都持著可以接受、可以平等對待的態度,不把自己陷入很多窠臼或既定觀念中。後來法國文化也給了我這樣的感覺,它是一種開放的態度,或者說是一種包容的精神。
小時候我看過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不少書,加上大學時期已經幫出版社做過一些轉譯,對編輯要幹什麽大致是有點了解的,所以2009年我進了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出版社薪金不高,剛拿到薪金的時候,我甚至有點崩潰,想到和同學之間的收入差距,會問自己,讀了這麽多年書出來,我這個選擇真的對嗎?但自己想要的是什麽,我心裏是明白的,既然選擇了這樣的工作,就要承擔它的後果。
後來我編的第一本法語稿子,是菲利普·迪昂的【三十七度二】,也就是經典文藝片【巴黎野玫瑰】的原著小說。學法語的幾乎人人都看過那部電影。那時候同學都來問我,書的開頭和電影是一樣的嗎?我跟他們說不是的,原著是一部蠻嚴肅的文藝小說。後來法國大使館的文化處還邀請了菲利普·迪昂來中國,那也是我第一次接待外國作家。
工作的頭兩年,我是超級有新鮮感的,因為要學很多東西。之前社裏出經典名著比較多,現在想要出新作家的作品,那我就開始狂補這方面的資料,看法國的書訊,找那些作家的資料,跟很多法國出版社以及一些法國機構建立聯系。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從0到1、從無到有的過程,就像自己在開拓一片領地。
做轉譯書的編輯,有點像做售後服務,做一個合適的封面、為書做宣傳、找到它的目標讀者群,對於譯者這邊,某些方面我也是做好售後服務,書出了之後我要給譯者寄書、開稿費,當然還有一些情感交流,在轉譯過程中,譯者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困擾,需要跟他談心、幫忙一起查資料。去年10月我參加了一個法國論壇,其中談到了「AI 到底會不會替代編輯或者譯者的工作?」我記得有個法國的編輯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說可以替代一部份,不可能完全替代。這個工作說到底還是一個很人性化的工作,有關「人」的工作,這部份是沒有辦法替代的。跟譯者或者作者的日常交流,需要一定的情感積累,並不是冷冰冰的檔傳輸。
整本書生產的每一個環節,從頭到尾,都跟編輯有關。我開玩笑舉過一個例子,在法語裏面,過去時還有兩種時態,一個叫完成過去時,還有一個叫未完成過去時。我讀書的時候一直沒想明白這是怎麽回事。上班之後想明白了,我的工作就是一直處於一種未完成過去時,就是你列了很多活,但沒有一個是可以勾掉的,都是一個持續狀態。如果能夠把清單勾掉,會有一種完成感,但是編輯這份工作,永遠是一種未完待續。

黃雅琴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孤獨和團結」
我很認同【天才的編輯】裏說的,「編輯充其量是在釋放能量,他什麽也沒有創造。」作為一個編輯,我的角色就是這樣,如果說需要燈光全部打在自己身上的話,那應該成為一個原創作者。那麽在這個過程中,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價值感?首要的一點是有強烈的信仰,這也是我心目中好編輯的基礎。
這不是一開始就能做到的,新鮮期過去之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瓶頸期,很迷茫,覺得自己什麽東西都沒做出來。直到2014年,莫迪亞諾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當時責編了他的作品【地平線】等,那晚譯者徐和瑾老師發來資訊,說「祝賀」,當時我還在吃飯,心想祝賀什麽?不過很快就有電話打進來了,也知道怎麽回事了。那天幾乎是忙了一個晚上,回答記者的問題,準備資料,從7點多一直弄到 12 點多,但一點也不累。那是我最近距離地接觸諾獎,那天晚上我感覺就像高考查分,知道自己考了一個還不錯的分數,非常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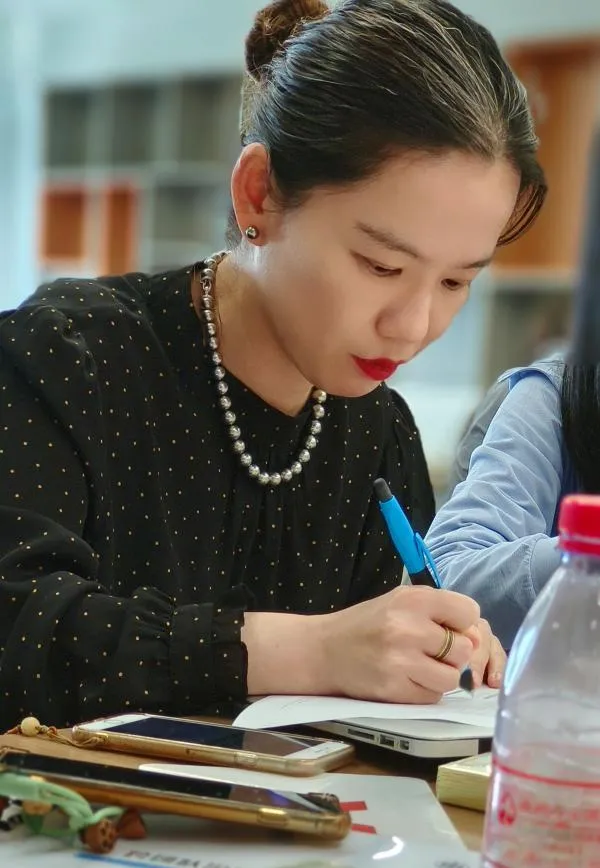
黃雅琴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還是覺得這份工作好像是一份孤獨的工作,苦惱、開心,都是我個人的,時間長了,很容易疲倦。大概2018年,我參加了一個法語出版交流團,我代表的是中國,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法語編輯,一行差不多20人,一起去了巴黎。也是這次交流團,讓我有了不同的認識。
那次交流真的見了好幾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很有意思,本來接待我們的一般都是版權經理,但這家出版社讓我有點驚呆了。辦公室擠了好多編輯,至少十幾個。大家都站著看我們,他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交流機會,問了我們很多問題:你們書是怎麽出的?定價機制是怎樣的?引進書的決策是怎麽做出來的?那一刻我發現,原來這些煩惱全世界都一樣,我的視野好像也更廣闊了一些。
同時我也看到,只要是好的文學作品,全世界都會認可,哪怕在遙遠的保加利亞或者土耳其,大家喜歡的也是同樣的東西,這種感覺就像,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想起入行時,前輩們也跟我說過,一定要做你喜歡的作家的書,這樣才比較容易和作者共情,想象力也更容易展開,知道該給作品一個怎樣的封面、撰寫怎樣的宣傳內容,也能很容易預設它在中國的讀者應該是什麽樣的,也更有動力去說服和我合作的人。
我想作為編輯最基本的,應該就是自己認定的作家,就應該把他的書一本本做出來。這是一個長期的工程,我需要堅定自己,因為那是我熱愛的、喜歡的作家,我就應該持之以恒地把它給做下去。
所有作家裏,影響我最大的是加繆,在我看來,無論是【鼠疫】還是【西西弗神話】,講的都是我們作為脆弱的個體,怎麽面對這樣一個充滿變數的巨大世界,面對所有未知、不確定性。就像西西弗,怎麽重復一天又一天的生活,怎麽樣面對這樣的人生?怎麽繼續活下去?
加繆他常用到兩個詞:孤獨和團結,在法語裏面這兩個詞的發音是很像的:一個是「索利達帶」(solitude,孤獨),一個是「索利帶」(solitaire,團結)。我的世界觀大概是被這樣塑造的。我很同意他的說法,人是孤獨的,人是一個渺小的個體,但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可以有一些連結的,是可以守望相助的。
首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個體一定要保有這樣的善意。我很喜歡【鼠疫】中那句非常質樸的話:每個人堅守自己的崗位。無論這個世界怎麽變幻、怎麽動蕩,我首先會堅守我自己內心的小小火種,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在庸常的日復一日的工作中,熱烈地活下去。

黃雅琴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應當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我承認作為法語編輯,成為法語譯者的機會還是很多的。我小時候看很多轉譯名著,就想過有一天會走上轉譯的道路,包括進出版社,其實也是考慮到會比別人離這個平台更近一點。
有一天,譯者胡小躍老師突然來找我,他做了一套鮑利斯·維昂的文集,有好幾本,問我想不想轉譯當中一本?我說當然想。我看了一眼那套文集裏的書名,說我要翻這本【我要在你的墳上吐痰】,因為這個書名看著很缺德。
雖然我之前也翻過一些小東西,但這本書是我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轉譯作品。對於一個譯者來說,能拿出一個正兒八經的東西時,才可以算是自己轉譯生涯的第一個裏程碑。
我一般是利用業余比較整塊的時間來轉譯,每次幹掉一點。之前因為工作關系,經常需要跟老一輩轉譯家相處,常聽他們講年輕時候的故事。那時候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轉譯是需要時間積累的,勤奮和努力是做轉譯的一個很基本的要求。所以每天回家,我可能都是在做一些看似很枯燥的事情。
壓力大的時候,我喜歡玩解密遊戲,我一直覺得這跟做轉譯其實是一回事,都是一個轉碼、解決問題的過程。所以我也只愛玩解謎類遊戲。朋友偶爾叫我出去玩,我也會說去玩劇本殺吧,去玩密室逃脫吧。他們說劇本殺不就是讀檔,我說,哎,我就愛讀檔。
再下一個裏程碑,就是轉譯了拿了傅雷獎的【男孩】,這本書大概是20萬字,是我翻到現在最長的一部小說。法國小說字數一般只有6、7萬,翻完這本的感覺就像,從一開始跑800米,到現在跑了一個半馬。所以【男孩】也是在長度上第一次讓我很有成就感。
我個人認為越是好的作家的作品,越是好轉譯。法語很講究語法用詞的精確性,越是好的作家,他的結構越是清晰,沒有多少讓你覺得看不懂的地方。用什麽詞更好,這個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但是基礎層面它不會讓你有什麽困擾,也不會有邏輯問題。所以總體上轉譯【男孩】對我來說不難,如果要說有什麽很崩潰的稿子,應該是那本【我為什麽自己的書一本沒寫】。
這本書大概只有5萬字,是一本很薄的書。但是它不是小說,小說相對好翻一點,因為有故事情節、有邏輯。那是一本很法國知識分子趣味的書,語言很高級,又有法國人那種哲學思維。每一個逗號都是一個轉折,看著篇幅很短,但要花的精力很多很多。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表達什麽。
翻這本書時,我第一次跟編輯說,我壓力太大了,睡不著覺了,要不換個人來轉譯。編輯開始鼓勵我,「沒事的,肯定行的,我跟你一起看」。我大概就等著人家這句話,最後也堅持下來了。
關於轉譯,我最近希望達到的一個狀態,是像原創作者一樣去寫下這些文字。在看原文的時候,譯者會不受控制地受到原文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你根本沒辦法。那麽怎麽可以不受控制?我現在的想法就是,用一種更符合中國人的語言,用一種更自然流暢的文字把它給表述出來。

黃雅琴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從選擇法語,到進出版社,再到成為譯者,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目標明確的人。無論做編輯還是轉譯,抑或是人生,都是一樣的,都要拒絕一些東西,才能目標明確地往前走。這跟我媽媽對我的影響有關,她是一個精神狀態非常穩定的女性,作為一個母親,她盡量給我一切。小時候她常跟我說,你想要什麽東西就說出來,不要跟我扭扭捏捏,不要作。從那時候開始,我心裏就清楚自己想要什麽,而且也明白,有一定可能性是可以獲得的。
維勒貝克說過,不要畏懼幸福,因為它根本不存在。我會覺得,幸福這個詞太大了,作為個人不配擁有,我更相信一些「小確幸」。現在回過頭看,其實從我入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積累,堅守在自己的崗位,「團結和孤獨」地重復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但這樣一種小小的確定狀態,就已經是我自己定義的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