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有海外博主在法國街頭表演科目三;不久前,芭蕾舞團在謝幕時也上演了一曲社會搖。「科目三」的勁頭持續升溫。
實際上,這一類的舞蹈並不是第一次引爆網絡,它們常常被統稱為社會搖——這種舞蹈沒有固定的動作,參與者只需跟隨節奏搖擺身體,常見的動作包括點頭、晃動肩膀、甩動雙手、扭腰和踢腿等。
社會搖何以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有人「深受其害」,認為它是精神汙染,標誌著大眾審美品位的下滑,體現了市場對審醜趨勢的迎合與放縱。同時也有不少人戲稱:「秦始皇也沒能料到,統一世界的竟是科目三。」這意味著它可能是一種積極的文化輸出,其風行可能暗示著,它不僅吻合了當下年輕人的生活態度,也帶來了一種精神動力。這種看似「發癲」的現象,或許是青年自主意識提升的體現。
科目三作為社會搖的一種,與其他舞蹈形式相比獨樹一幟。它與芭蕾的優雅或Kpop(韓流)的時尚都背道而馳,卻獲得了萬千受眾。當一群青年在街頭隨著古風喊麥的節奏搖擺時,這就不僅是一種舞蹈,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所展現的不僅僅是魔性的舞步和別扭的身體,而是青年們自信的自我表達,蘊藏著對性別規訓的反叛,乃至展現了一種倫理態度。但是,作為普通人,我們仍需進一步思考,當自我表達被市場收編時,我們能如何免於潮流的裹挾?
「科目三」:社會搖的優雅化?
「科目三」也稱「廣西科目三」。關於其由來,流傳著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這一舞蹈始於廣西梧州舉辦的一場婚禮,賓客用隨性而為的魔性舞步代替婚鬧的結果。另一種說法則提到,廣西人一生有三大必經之「科目」,一是山歌,二是嗦粉,三是魔性舞蹈。
起初,科目三舞蹈確是舞者任性為之。舞者不受場地、服裝和專業技術的局限,僅需隨音樂節奏扭動身體來表達情感。後來,這種舞蹈因幾段火爆網絡的影片而名聲大噪。影片中,幾名長相標致的海底撈服務生瀟灑自如地表演,它引發了一股模仿熱潮,為該舞蹈帶來了人氣和知名度,爭議也隨之而來。從路人視角拍攝的影片中,在「被迫營業」的服務生身上,很多人共情了普通人的辛酸:當流行文化與商品市場相結合,成為一種隱形的強制和挾持時,普通人為了生活往往不得不被迫迎合。
然而,隨著專業舞者的參與,科目三從小圈子躍升至更正統的舞台,正式步入主流文化領域,它在社交媒體上迅速風行,在各大舞台上博得陣陣掌聲,甚至走出國門,被拉丁舞世界冠軍和俄羅斯皇家芭蕾舞團所接受,得以展現於「大雅之堂」。總之,科目三成功擺脫了「低俗」標簽,獲得了全球影響力。如此,科目三正式參與了民族自豪敘事的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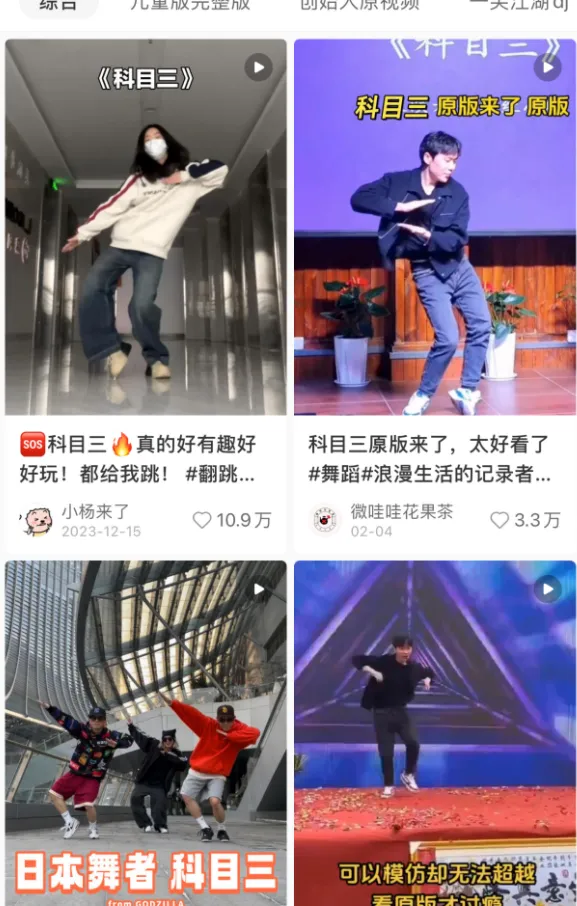
在社交媒體上,「科目三」的舞蹈傳播十分廣泛。
科目三實際上屬於「社會搖」的一種,它的爆火也並不新鮮。社會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盛行的「迪斯科」舞蹈。迪斯科舞蹈的經典元素是緊湊強烈的音樂節奏和簡單自由的舞步,還有室內晦暗閃爍的燈光,這三者共同營造出狂歡與釋放的氛圍。參與者主要是青中年,大部份人都將其視作一種在社會規則空間之外的刺激和釋放。社會搖既順承了迪斯科的以上特征,也傳承了它的受眾基礎。
然而,社會搖之所以成為一種文化現象,還得歸功於短影片平台的推廣。早在2014年,社會搖就透過美拍、快手等短影片軟件,逐漸成為潮流文化的一部份。快手平台上的網紅「牌牌琦」在互聯網上被譽為「正規軍」,他的團隊不僅統一了社會搖的表演風格,即結合社會語錄喊麥、西服裝扮與魔性舞步,而且對它進行了推廣。2018年,社會搖經歷了從「花團錦簇」到「過街老鼠」的墜落,一度被主串流媒體猛烈抨擊,甚至被形容為「晃散了人們的詩和遠方」。總之,社會搖在傳播方式和舞蹈設計兩方面都引人生厭。
從傳播角度看,社會搖被商業利益所驅動,透過「流量」無限制地推廣,造成了高強度、過飽和的傳播。在流量爭奪戰中,網紅們屢次劍走偏鋒,最終導致諸種怪異行為猖獗,直播對罵、線下約架等事件頻發。針對這些情況,主串流媒體將其正式標記為一種滋生亂象的有毒文化現象。
然而,與社會搖不同,「科目三」的流行不僅沒有被指控為「低俗」,反而成為主流文化的新寵,還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輸出走向了世界。然而,在舞蹈設計方面,「科目三」與社會搖一脈相承,因此同樣引發爭議。魔性的舞步伴隨著古風元素的喊麥,被一些人視作視覺和精神的汙染。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歸罪為「土味」,「醜陋」的舞步本身無傷大雅,但如果說欣賞它是一種「審醜」,那麽這種趨勢究竟反映出當代人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呢?
以「粗鄙」表達自我?
從舞蹈本身出發,「科目三」作為社會搖的一種,屬於「參與型」舞蹈,重要的是營造出一種狂歡的氛圍感。可能不適合從藝術的角度去評價科目三,或者可以說它展現出了對嚴肅之美的解構,並服務於人們對輕松快樂的自我表達的追求,這尤其體現在它對「空間」的利用上。
芭蕾等古典舞則被視作高雅舞蹈,它們追求藝術表達,追求極致的秩序、純粹、精確和和諧的古典美。高雅舞蹈需要舞者進行嚴格的長期訓練、精確的舞蹈編排,還需要精致的服裝、燈光和布景舞台。它的表演空間多是莊重典雅的劇院和音樂廳。觀眾或端坐於舞台之下,或在電視等傳統媒介之前。除此之外,交誼舞、蹦迪這類較為簡單的社交性舞蹈,雖然對場地要求較低,但通常也局限於歌舞廳、夜店等封閉室內。而與同樣不受地點限制的街舞相比,社會搖還不會受到有關專業度的隱形鄙視鏈的困擾,甚至它在排練時都不需要練習室。因此,自由靈活,不受地點限制,練習簡單成為社會搖的典型特征。

大連藝術學院某場音樂會現場的「科目三」舞蹈表演。圖/大連藝術學院影片號截圖。
相比於高雅舞蹈,社會搖的表演和觀賞空間都更加私人化和日常化,甚至可以說後者不受表演地點的限制,因此能夠隨意湧入各式生活空間中。這就打破了傳統舞蹈中舞者與舞台的固定結構。首先,舞者不再被舞台所界定,反而用何處跳舞界定何為舞台,社會搖也不需要觀眾,舞者首先就是自己的觀眾。個體的自主性得到了極大的肯定,這體現了它對高雅舞蹈中蘊藏的宏大敘事的解構。其次,社會搖的觀賞空間完全虛擬化,主要是透過短影片或直播等形式在網絡平台上傳播,這改變了傳統觀演模式。觀眾不再是鑒賞、評判或接受陶冶的角色,而是參與者或者湊熱鬧的人,看它是為了輕松找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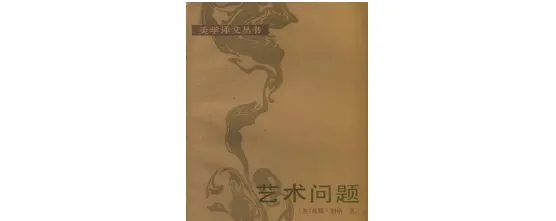
延伸閱讀:【藝術問題】,作者:蘇珊·朗格,譯者:滕守堯 朱疆源,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3月。
從舞蹈本身來看,社會搖在服裝和舞蹈動作設計上均呈現出一種「粗鄙美學」,其顯著特征在於不追求深層意義,反而流露出庸俗和審醜的趨勢,伴隨著一種虛假的自我陶醉和刻意的矯揉造作。從創作動機角度來看,社會搖諂媚流俗,其內容創作既缺乏深度也不追求寓意。在創作風格上,它追求視覺上的惡俗趣味,動作機械化重復,且缺乏協調性,引發觀看者的厭惡,但也營造出一種癲狂的氛圍。
表面上,舞者們似乎在刻意展現自我貶低的形象和姿態,透過矯揉造作和低俗化來迎合大眾對醜陋的審視。實際上,這種刻奇行為是一種「自媚」。舞者透過自我醜化的行為來挑戰所謂的高雅標準。他們在癲狂的體驗中,尋求挑戰世界的放逐感和控制世界的掌控感,從而獲得了一種虛假的自我感動,這一過程實作了審美上的自我崇高化。
這種「自媚」也並不罕見,從千禧年曾流行的「殺馬特」風潮,到社交媒體上流行的「汙」表情包,再到戲謔和解構經典的鬼畜影片,都展現了這種自我放棄式自媚。但在這種自媚中,這些群體又展現了一種極具強度的主體抗爭沖動。在伯明翰學派的視角下,文化是不同社會群體進行代表權鬥爭的戰場。邊緣群體的陣地是「亞文化」,他們需要由此出發,對抗主文化強加於身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說,社會搖代表了一種無法融入精英文化的小鎮青年們的叛逆。既然品位不被主文化認同而審美偏好被視作「低俗」,那麽亞文化群體便以低俗為驕傲,不屑於高雅舞蹈所推崇的規範之美,而是保持醜陋,自我賦權,進行抵抗。
社會搖如今已登「大雅之堂」,成為一種「正能量」,一方面由於表演它的人不再是不著調的精神小夥小妹,而是專職表演高雅藝術的舞者。由此可見,雅和俗,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文化話語權的「主流」所定義的,當我們評價一個東西 「low」(低俗)的時候,評價者就站在優雅的高處,是在俯視低處。主文化擁有俯視的特權,也即碾壓、無視、玩弄和收編亞文化的權力。
美麗與自信:
舞蹈中的性別意識
在當代流行文化中,流行舞蹈更加強調一種自主、自信、自娛。其中,社會搖似乎能對我們思考舞蹈動作的性異位建有所啟發,它采取了一種「先模糊邊界,再自我賦能」的策略。社會搖首先是在傳播的角度沖擊了美醜邊界,如果只有美麗的事物被認為值得傳播,那麽社會搖則選擇堅持並自信地展現所謂的「醜陋」。這種打破界限的做法,在性別系統中也有著相似的效果。傳統上,柔美和延伸的動作展現了女性氣質,而有棱角的框架和爆發力則展現了男性氣質。然而,社會搖的動作設計是去性別化的,它甚至利用「自我醜化」的手段,來模糊這些性別差異。
與其他藝術形態不同,舞蹈藝術獨特之處在於,它將審美主體、創造主題和藝術材料三者融合於舞者的身體之中。甚至可以說,舞蹈中的創作者、作品與觀眾可以是同一人。在某種程度上,社會搖恰切地展現了舞蹈的這一性質。
身體是舞蹈的「敘體」,不僅如此,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藝術問題】中還將舞蹈表演與意識本身相聯結,她認為「舞蹈表現的是語言無法表達的東西———意識本身的邏輯」。朗格的這一觀點啟示我們,舞蹈中的身體與意識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舞蹈表達中,身體不僅是生物學意義上性別化的肉體,同時也是社會性別的實體。舞蹈動作不但順應並表達人類社會中的性別角色,形成具有性別特征的敘述風格,同時也有能力挑戰和重新定義社會的性別規範。
芭蕾舞作為高雅藝術的代表,其追求的和諧、優雅、精準和純粹,展現了經典舞蹈藝術的精髓。在芭蕾中,和諧不僅是指身體與角色間的完美協調,也意味著即便在沖突和張力中,也要保持一種戲劇性和感染力的和諧統一。優雅是高貴與傳統美學的追求。精準關乎於對空間的把握,身體的每一個姿態都是舞者對空間的精確控制,也是情感在空間中的精確表達。至於純粹,它與舞者對舞蹈技術的極致追求相聯系,是嚴格規則和標準下所追求的藝術造詣,舞者向某一客觀標準追求卓越,並運用一種客體化的目光審視自己。按照這些標準,芭蕾舞難免深植於社會性別系統之中,透過服裝、動作等將對特定性別特質的展現推向極致。
另一方面,這並不是將高雅藝術等同於性別刻板。在傳統藝術中,「反串」的形式也並不少見。反串即演員扮演與自己生理性別不同的角色,比如京劇中的「旦角」,早期都是由男性扮演。這是由於歷史上對女性在公共場合中的暴露有著嚴格的限制。但是,反串保留至今形成了一種藝術傳統。它不僅提供了一種探索和表達不同性別身份的機會,還能引發觀眾對性別、社會規範和身份的反思。例如,越劇演員陳麗君在【新龍門客棧】中的表演,不僅因其男性化的英姿颯爽而備受贊譽,更是對傳統上「霸氣之美」的重新定義。這樣的藝術表現,展現了性別身份的流動性和多樣性,促使人們對性別角色有了更深層的思考。

越劇演員陳麗君在【新龍門客棧】中的表演。
同樣,Kpop女團舞作為流行文化中追求自主力量的另一種可能,則采取了強調女性美的策略來賦能自身。在賦能的過程中,不同代際的舞蹈風格差異巨大,但大部份都在強調舞者的表情與動作的配合,女性身姿的展現以及「享受美麗」的自信。這些舞蹈動作挖掘了女性特質的多元之美。然而,這種策略也可能會陷入對女性氣質的傳統處理方式,比如強調對舞者身材的嚴苛要求。盡管相比於芭蕾或古典舞,Kpop展示了更多元的女性形象,但如果僅限於迎合大眾對「美」的要求,那麽它的多元性很容易被收編。

Kpop風格女團舞曲影片畫面。
社會搖與以上舞蹈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它的「活力」與「別扭」。在社會搖發展之初,它更接近「原始舞蹈」。在原始舞蹈中,「實際活動」先於「審美活動」,舞動透過動作的律動性展現出生命的劇烈波動。舞者在高速的律動中體驗到生命的真實感,同時,觀眾也被這種真實活著的感覺所打動,獲得滿足。以現在的大眾審美標準來看,「生命的波動」並不美,甚至醜陋不堪,但不妨礙它展現了「活生生的強度」。然而,當「醜」開始被商業利用時,社會搖源於原始活力的抗爭性可能受到削弱。
對於當下全球範圍內流行的「科目三」舞蹈,很多國人的反應是「有些自豪但不願相認」。這種復雜的情緒可能源於社會搖與傳統審美標準的不符,但它又展現出了強烈的原始感染力。加上雅俗之間的界限伴隨著文化事件逐漸發生了改變,「科目三」成為一種積極向上的文化代表。然而,作為一種隨性和自由的舞蹈表達,社會搖卻被冠以了「考評」相關的名字,即「科目三」。這一命名或許與其本質相悖,原本透過舞蹈所要表達的隨心所欲的叛逆,卻被貼上了「考評機制」的標簽。這種命名或許也反映了主文化對亞文化的無意識的接納、收編和重新定義,指向了亞文化與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張力和互動。
本文參考資料:
[1]「從火爆全網到罵聲一片,社會搖是如何發展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L411v7jt/?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2] #新華銳評#【別讓社會搖等低俗影片晃散了你的「詩和遠方」】
[3]「從被封殺到火遍全網,科目三背後的社會搖,憑什麽能翻身?」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T4m1S7sN/?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4]李寧,非主流網絡文藝的審美文化探析——以「喊麥」與「社會搖」為中心的考察,藝術評論,2018(8),第35頁。
[5]唐滿城,唐滿城舞蹈文集[H],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 年,第126頁。
[6]劉湞,舞蹈性別意識之嬗變———胡塞爾話語符號理論建構中的舞蹈文化闡釋,廣西藝術學院學報【藝術探索】,第21卷 第5期,2007年,第130頁。
撰文/豬迅兒
編輯/走走
校對/楊許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