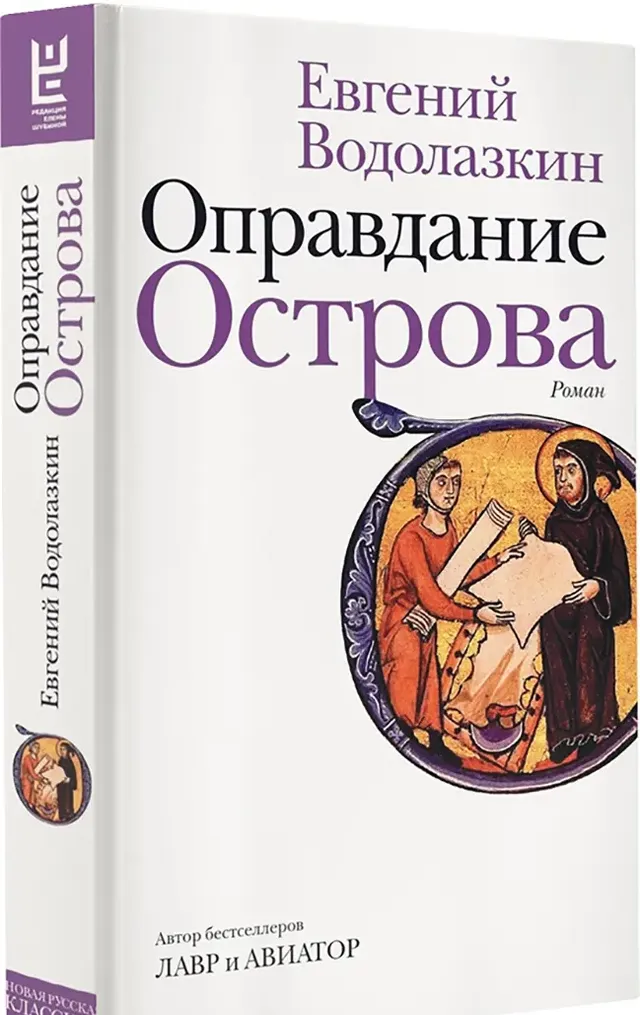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陳璧君 記者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這兩年,「發瘋文學」成為年輕人表達情感的一種形式,為什麽理性的人需要回歸非理性來宣泄情感?發瘋或癲狂意味著什麽?
在俄羅斯作家葉夫蓋尼·沃多拉茲金看來,言行癲狂的聖愚是根植於俄羅斯宗教信仰的特殊存在。他認為,這個僧人的癲狂只是外在狀態,聖愚以其佯狂揭示了世界本身的瘋狂,這是一種「超脫法律的壯舉」。
沃多拉茲金三度摘得俄羅斯文學最高獎「大書獎」,是一位對文學現狀高度敏銳的寫作者。他察覺到,現代的讀者越來越不相信虛構的力量,他們希望被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說服,這也是非虛構文學日益流行的原因。
獲得2013年「大書獎」第一名的【拉夫爾】今年出版了中譯本。書封上有一行小字——「非歷史小說」,這向讀者揭示了沃多拉茲金的寫作態度:本書所寫,既非史書上的歷史,也不是充滿虛構的歷史小說,【拉夫爾】追求的是高於歷史的真實性。在書寫主人公的結局時,沃多拉茲金甚至落下熱淚,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時說:「拉夫爾是一個真正存在著的人,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我是如此為他動容。」

在一個需要假裝癲狂才能直抒胸臆的時代,什麽樣的人是「真正存在著的人」?在文藝影視作品透過塑造惡人「大快人心」的當下,好人不再受歡迎了嗎?沃多拉茲金想用好人的故事為讀者帶來「含淚的微笑」——這也是他最愛的小說家、俄國作家果戈裏的喜劇風格。或許,對每一個為生活感到沮喪的讀者而言,【拉夫爾】的意義就在於此。
01 聖愚的行為是一種「超脫法律的壯舉」
界面文化:【拉夫爾】的封面有一行小字「非歷史小說」,你解釋稱,歷史只是作為人物發展的背景讓你感興趣。有學者據此認為,你的小說是「新現代主義」文學,是用不同時代的現實來說明人並不完全依賴歷史社會環境而存在,歷史也並不決定人的個性。你怎麽看待歷史和虛構的關系?
沃多拉茲金: 出版社希望我寫一部歷史小說,但我自己並不喜歡歷史小說,甚至不太喜歡型別文學,我想在這本書裏利用型別文學的形式來傳達其他的意義。我不想讓那些喜歡歷史小說的讀者失望。畢竟書的價格不低,如果他們花了錢卻買到不喜歡的書,何必呢?所以我告訴出版社的人,這並不是一部歷史小說。後來出版社便將這五個字印在了封面上,實際上不是我的主意。
【拉夫爾】是用中世紀詩學的手法寫成的,某種意義上後現代主義詩學與中世紀詩學確有相似之處。我簡單列舉兩個特征:首先,碎片化的文本結構在中世紀文學很常見,作品是由各種片段拼貼組成的。其次,中世紀文學往往是匿名的,這也可以與羅蘭·巴特所定義的「作者之死」相對應。中世紀文學追求更強的真實性,給讀者一種並非虛構、現實正是如此的閱讀體驗,這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非虛構文學也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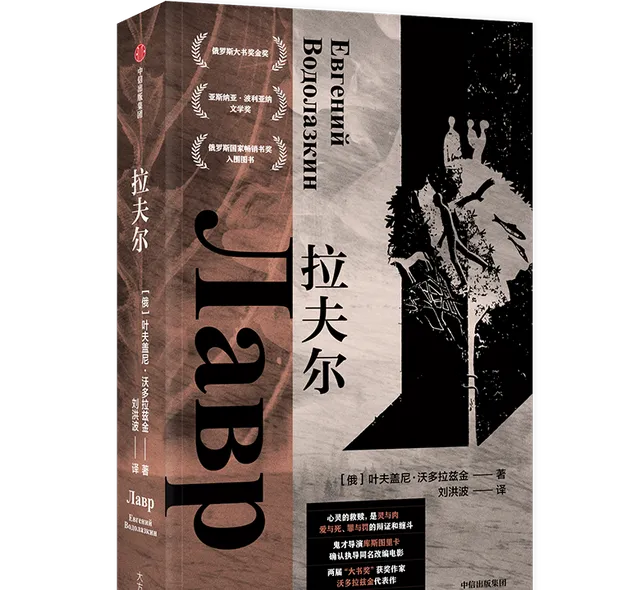
我還想就中世紀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區別做一點補充。與中世紀文學不同的是,現代文學具有一種遊戲性質,即我們約定俗成地假設事物的面貌,作者則負責編造那些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文學就好像作者和讀者一起玩一種叫做「虛構」的遊戲。但現在,讀者越來越不相信虛構,他們希望被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說服。現代文學開始羞於展現其虛構性,因此,「自傳式虛構」(autofiction,亦稱自虛構或自小說)應運而生,這是一種表現得像「非虛構」的虛構文學型別,這樣的虛構方式被認為是有效的,它在當前的文學界越來越流行。
界面文化:【拉夫爾】的開頭,你介紹了艾爾謝尼的職業「大夫」在中世紀的意思,它出自「開口說話」這個詞,這意味著話語的力量非常重要。在小說的對話裏,你還使用了大量雜糅的教會斯拉夫語、古俄語與現代俄語,詳細書寫了艾爾謝尼讀古書、教妻子念古書的過程,以及艾爾謝尼不斷對死者說話的情節。在中世紀俄羅斯,口語和文字的重要性是怎樣的?
沃多拉茲金: 在中世紀,書面語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艾爾謝尼的祖父凱瑞斯托弗,就總是在樺樹皮上記錄各種事物。他認為,口頭語言只有在空氣中振動發出聲音才有效,一旦振動消失,語言也就消失了。唯有書面的文字才能賦予語言以物質特性,使之具象地保存下來並流傳至後世。
尤其是在俄羅斯中世紀,人們對書面語言的態度非常鄭重。舊手稿中的字母和詞語,如「上帝」或「聖母」,都被認為具有某種神聖性。這些記錄了神聖詞語的書籍會被妥善保存,即使是老舊破損的手稿,也不會輕易燒毀,而是被放在木板上順水漂流,讓書籍進入永恒的旅程,它們依然是神聖的。我透過凱瑞斯托弗的形象,反映的是古羅斯對書面文字的敬重態度。

界面文化:在【拉夫爾】中你寫到了「瘋子」福馬和卡爾普。福馬總是被別人打,他卻說,「俄羅斯人是虔誠的。瘋子應該忍受苦難,便走向罪孽,為的是確保他能有這種苦難。」俄羅斯文學似乎有很多這樣的受苦者形象,比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白癡】的梅詩金公爵。
沃多拉茲金: 也許這裏存在某種語言文化的差異,把他們轉譯為「瘋子」並不準確。在英語中,「聖愚」(юродивый)被轉譯為holy fool,這也不是完全準確的。在我看來,聖愚的癲狂行為是一種「超脫法律的壯舉」:一個人不僅實踐禁欲的苦行,而且還透過奇怪的舉動掩蓋這一點,癲狂只是這種行為的外在狀態。俄羅斯的一首教堂聖歌提到,聖愚以佯狂揭示了世界本身的瘋狂。我寫到這樣的形象,是想體現人類心理的悖論:聖愚不能被冒犯,因此很多人都想冒犯他們。被禁止的東西有其特別的吸重力。

02 遺憾的是,如今的世界缺乏故事中的正義者
界面文化:你在多次訪談中都說,當代人的時間是快速發展的、橫向的時間,中世紀的時間則是一種縱向的時間觀。時間的橫向或縱向運動,它具體指的是什麽?
沃多拉茲金: 現今的時代是一個「水平」的時代,我的意思是,在人類的歷史中,時間總是從一個點向另一個點做橫向運動,從生到死,從開始走向終結,這是一種線性的時間觀。而在中世紀,還存在另一條「垂直」的時間座標,即縱向的運動,它指引人們向上抵達天堂、通往永恒。盡管中世紀的人們壽命較短,但他們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比現代人更豐富,他們的時間被向上的運動擴充套件了。可以說,追尋永恒就是中世紀人的思維特點,其核心是人的信仰,對於現代人而言,這種「垂直」的、以信仰為核心的時間意識幾乎不存在。
界面文化:【拉夫爾】也用到了類似的表述,故事中的長老告誡不遠萬裏來耶路撒冷朝聖的艾爾謝尼,不要過分熱衷於長途跋涉的水平運動,而要熱衷於垂直運動。這裏的水平胡垂直指的是你對空間運動的思考嗎?你怎麽看待時間和空間的關系呢?
沃多拉茲金: 是的。和剛剛討論的橫向和縱向的時間運動不同,這裏我也用了水平胡垂直的表述,指的卻是空間。
米哈伊爾·巴哈金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時空體」(chronotope),最初是由時間(khronos)和空間(topos)這兩個希臘語詞結合而來。這位偉大的文藝理論家認為,空間和時間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總是相互包含、互生共存。在【拉夫爾】中,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與之有所相似,主人公艾爾謝尼不僅在穿越空間,同時也在與時間抗爭。重要的是這個情節——艾爾謝尼到達了耶路撒冷,雖然他歷盡艱辛跨越了很長的距離,但聖墓邊的長老對他說:你完全可以在俄羅斯的修道院裏就提出你的問題,而不必來到這裏。他這麽說是要提醒艾爾謝尼,最重要的運動不是地理上的運動,而是精神的向上之旅。
界面文化:去年,你為中國讀者創作了一個短篇小說【水鏡的裂隙】。在給中譯者的電子信件中你寫道:「我努力選取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作家的勞動在所有國家的狀況或許都大致相同。」故事發生在一位已成名的作家和未成名的外賣員寫作者之間,將年輕一代與老一代創作者的不同心理展現給讀者。你覺得什麽樣的勞動對作家而言是真誠、有效、合理的,什麽樣的勞動又是作家應該避免的?
沃多拉茲金: 當一個作家推廣自己的作品,無論他要面對的是哪國讀者,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在我看來,作家首先應該關註如何表達出自己的核心思想或情感,而不是迎合讀者的意見。因為讀者其實無法得知作家的寫作能提供什麽,那麽這也是作家的主動性所在:敏銳地感知什麽對讀者有益,並把這些東西呈現給他們。
其次,為了某個特定的文學獎項而創作,想著如何取悅評審團,這是現實中很常見的情況,但我覺得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我曾經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拉夫爾】入圍俄羅斯最重要的文學獎「大書獎」短名單時,一位評論家告訴我,你是拿不到這個獎的,因為這個獎是頒給「主流」的,而【拉夫爾】不是一本主流的小說。結果,我還是得了「大書獎」。之後,當我再次遇到這位評論家,他對我說:「我知道你拿到了這個獎——這說明‘主流’已經改變了。」所以,不要想著獎項,也不要想著主流,作家應該依照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去寫作。
界面文化:那麽【拉夫爾】寫到的精神之旅,是你身為寫作者想傳達的理智和良心嗎?
沃多拉茲金: 可以這麽認為。到了某個年齡段之後,你就會開始思考一些事情,這些事情較為嚴肅,在年輕時可能很少觸及。你開始看見生命和生活的邊界,會對這條邊界以外的面貌感興趣。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應該變得沈悶無趣。嚴肅、深度和幽默之間並不相悖,我的小說不光書寫嚴肅的事情,它有不少幽默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想給人帶來「含淚的微笑」(這也是作家果戈裏講故事的風格)。

界面文化:你曾說過,創作【拉夫爾】是想講一個「能每天、每小時做出犧牲的人」,接續「好人」的文學傳統。「好人」又是怎樣的呢?
沃多拉茲金: 「好人」和「聖愚」不太一樣,我們不能將「聖愚」簡單定義為善良的人。他們太過與眾不同,但最終他們也是善良的,只是他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善良。他們羞於展示自己的善意,並盡力隱藏它。
界面文化:對於當下的俄羅斯來說,「好人」的概念還存在於年輕人的思想中嗎?你前面說到讀者的「主流」變了,是否意味著這個傳統得到了接續?
沃多拉茲金: 既然評審團決定把「主流」的獎項頒給我,也許確實帶有這樣的含義。有一個俄羅斯民諺:「沒有義人就沒有村莊,沒有聖人就沒有城市。」(俄文為「Без трех праведников не стоит земля」)它的意思是,世界的存在依賴於正義之人。如果沒有正義之人,生活是不可能的。這個短語曾出現在俄國作家尼古拉·謝苗諾威治·列斯科夫的作品中,還有其他作家也寫過。這句話在我的另一部小說【島的辯護】(Оправдание Острова)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遺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現在仍然很缺乏這樣的正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