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胡應麟講詩歌之演變,有一句很值得註意的話:「晉宋之交,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胡應麟是一位復古主義者,他在詩格上崇古,而貶斥後世的一切變革。但是他看出詩道的巨變是在晉宋之際,確可稱目光如炬。
晉宋之際的代表詩人是陶淵明和謝靈運,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雲:「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可見二人不但為中古時期興起的文人詩家的典範,也一直是後來文人詩文學創作的榜樣。
那麽陶、謝的「詩」與以前的作為歌詞的「詩」相較,究竟有什麽不同呢?我們說,其最外在的不同在於二者的物質形態:以前的「詩」是用嘴唱的,而陶、謝的詩則是寫在紙上的。陶、謝寫詩皆離不開紙:陶淵明寫詩的工具是「紙墨」;謝靈運之寫作也是「援紙握管」,且其流傳亦靠以紙來「競寫」。而紙對於陶、謝之詩來說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工具問題,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一種嶄新的語言藝術形態:將「詩」從過去的口唱的聲樂藝術變成了文本藝術,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詩文學作品。而詩相較於歌,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質的變革。
這種變革最明顯地表現在詩所敘寫的內容上。以前的「詩」亦即歌詞,歌詞之抒情,多為平鋪直敘的詠嘆和直抒胸臆式的情語;但陶、謝詩中之抒情,則仿佛有意轉了一個彎,他們都岔開筆去,著力營造一種由目中之景與身歷之事所組成的沁人心脾、豁人耳目的氛圍,以誘導讀者神遊於其中,去和他們一起感受,從而把自己特定的心情傳達給讀者。這種抒情機制,用我們過去經常說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借景言情」。也正因為陶淵明、謝靈運寫詩愛借景,多景語,故他們雖皆為抒情詩人,但我們每稱前者為田園詩人,稱後者為山水詩人。

陶淵明
我們讀陶淵明的【雜詩】【飲酒】【歸園田居】等名篇,仿佛走進「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的幽野農舍,徜徉於「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的恬靜田園,遊目於「木妍妍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的春山之景,聆聽著「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鄉村交響樂。我們仿佛與他一起和質樸的田父共語:「時復墟裏人,披草共來往。想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仿佛親身參加他們的酒會:「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於是,一種世外之人的盎然意趣和恬淡情愫在我們心中油然而生。
我們讀謝靈運的記遊詩,仿佛置身山水之間,與他一起「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嵚」,滿目是「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筿媚清漣」的美景,於是,在切實體驗回溪石瀨茂林修竹之美的同時,我們也領略了詩人的閑適與豪邁,深深地感受到他「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的襟懷。
有人說,陶、謝詩的寫景狀物,是對漢賦中手法的繼承。但漢賦狀物,旨在景物之本身;而陶、謝詩中之狀物,卻都是作為一種情境來寫的。景物在漢賦中是實的,但在陶、謝詩中是虛的;前者是擺在讀者面前的一些「物件」,後者是引導讀者神遊其中的「道路」。賦中之物作為物件,其本身就是作者要給你的東西;而詩中之物作為道路,目的則是讓讀者走進其中而體驗出詩人的情感。這也就是文人詩中的寫景與漢賦中寫景的根本差異。
正如陸機在【文賦】中所說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賦中寫物,在於鋪寫物之本身;而詩中寫物,乃由情之所系也。其實,我們在這裏所說的陶、謝詩中作為傳情之契機的景物描寫,也就是後世的詩論家所經常提到的「意境」。是的,陶、謝的詩與過去口唱的歌相比,最大的特點正在於意境的營造。古典詩歌研究者多去追索意境之論的誕生,而很少想到意境本身在中國詩史上也有個誕生期,這個誕生期就是晉宋之際。我們認為,陶、謝是中古以後首先有意在詩中營造意境者。陶、謝之後,意境遂成文人詩之詩骨、甚至詩魂。而意境在詩中之誕生,正是中古時期的詩歌所用以傳達情感的媒介發生了巨變的結果。
前文說過,過去的歌是口唱的,它傳情的物質媒介是直接的聲音,特定的情感可以透過直接入耳的音調、節奏和旋律得以體現。故口唱的歌雖然也有歌詞,但它以聲傳情的方式就決定了它必須以樂調和旋律為主軸。「歌」字之本義,即是純粹聲音上的詠嘆。【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雲:「在聲為歌。」註雲:「歌,嘆聲也。」【說文解字】雲:「歌,詠也,從欠哥聲。」「欠」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個人張口嘆氣之狀,而「哥」為二「可」相疊,「可」就是古代的「啊」,啊啊相連,狀嘆聲之長也。【毛詩序】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永歌之。」【毛詩·鄭風·子衿】傳雲:「歌者,謂引聲長詠之。」都說的是這個意思。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歌,不過是將事情直白地嘆出來而已,【呂氏春秋·音初】講「南音」之始,是大禹的妻子塗山女在苦等丈夫的時候所唱的【候人歌】:「候人兮猗。」「兮猗」等於「啊」「呀」,故所謂「候人歌」,不過就是直白地將「候人」一事曼聲嘆出來罷了。在這個詠嘆句中,「候人」作為歌詞之所以極其簡單而直白,就是因為歌人所要傳達的,並不是「等候人」這件事,而是她在等候人時的心情;而她的心情,主要是透過她直接發出來的如泣似訴、充滿哀怨的詠嘆之聲表現出來的。這就是歌之抒情以聲為用的情況。
後來的歌中,「兮猗」一類的詠嘆演變成樂曲,其歌詞也要比原始的「候人」要繁復些,但因為歌主要以聲音樂曲為用,故其歌詞總不脫直白淺露的特點。例如項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中只是簡單地告白他過去的勇猛和現在的絕望,而歌者的巨大傷痛,是在反復而發的「奈何」「奈若何」的悲嘆之中直接傳達給聽者的。又如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詞所述,也只不過是得了天下衣錦還鄉的簡單事實和加強國防的簡單想法,而作歌者的豪情壯誌,主要透過豪橫而高亢的旋律和韻調表現出來。這一點,不但漢魏以前口唱的歌是如此,就連現代的歌也是這樣。有的歌,歌詞可以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單憑其旋律就可以感人。過去有個佳話,一位朗誦大家在酒席間為座客用波蘭語朗誦詩篇,其抑揚頓挫的節奏和優美的韻律使滿座為之動容。人們問他所朗誦的究竟為何詩,他說,桌上之選單耳。這話雖誇張些,但不是沒有可能。因為人們直接聽唱誦之聲,在聽覺之中就能獲得情感。
詩歌從實際的歌唱一變為紙上的文字,它的節奏韻律與文字意義之主從關系就發生了倒轉。因為人們看紙上的文字,不能不首先領會文字的意義,而閱讀文本、領會意義的過程是一個想象過程。我們先須透過想象,把文字中所寫的東西在我們的心中締構出來,讓它們化為觀念形象。而在觀念形象中,那原先歌中直接入耳的節奏和旋律雖不能說完全消失,卻會從主軸變為意義的從屬,只起間接的輔助作用了。故文字的詩為了傳情,也就必須適應讀者閱讀行為中的想象機制,把引發自己特定情感的情境寫出來,讓讀者在想象中進入這一情境,從而把詩人在此情境之中的特定感受傳達給讀者。所以,意境之營造,實在是文字的詩在審美機制上的需要。唐人皎然【詩式】總結詩的規律,在創作上特別強調「取境」,他說【古詩十九首】「初見作用」,說謝靈運「尚於作用」,其所謂「作用」者,實指意境締構而言。他說「詩情緣境發」,又說「緣境不盡曰情」,總之是強調境為傳情的重要渠道,應該說這是極其深刻地把握了詩文學的藝術特質的。

謝靈運
另外,文字的詩與口唱的歌在結構上也有本質的不同。口唱之歌的直接物質形態是時間性的,因為作為它的主要支柱的樂曲,是音符與樂句的前後承續。而寫在紙上的詩文本,其形態就帶有很大的空間性。故唱歌可以肆口而發,想到哪兒就唱到哪兒,甚至有些樂府歌詞出於樂調的需要,其發端之詞可以隨意截移,如「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之類,在意義上不一定與全篇相連,不少樂府在整篇詞意上還有缺頭短尾的情況。而作詩卻需要預先結撰,像構建一座建築物,不但要註意平面的均衡,而且要使前後左右鉤心鬥角,相應相連。所以陶、謝以後的文人詩中,不但在語言上越來越註重句法,使對句增多、藻飾加強;也在詩意上越來越重視結構,使綴慮鋪言、首尾圓成。故煉句镕篇,是晉宋以後詩人寫詩的要務,而未聞漢魏歌人唱歌之前先作冥思苦想。後世的詩論家對文人詩與歌的這方面不同屢有論述,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雲:「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胡應麟【詩藪】亦雲:「東西二京,神奇渾樸;六朝排偶,靡曼精工。」皆為此論。
晉以後詩人對詩篇的镕煉,既包括意蘊上的,也包括韻律上的。詩文學雖主要供案上閱讀,但韻律作為抒情的輔助手段畢竟不可缺少。過去口唱的歌,因為有樂譜的勒制,故唱出的歌詞必有聲韻;而文字的詩擺脫了歌的原始形式,取得了自己的文學地位,這無形中就給詩的韻律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以前透過樂譜的勒制才能表現出來的韻律,現在要讓文字來承擔。這也就迫使詩人們去尋找語言本身固有的音樂素質,並透過調解組織來形成以前透過配樂才能有的音樂效果。這種要求在詩論上的反映,就是劉宋以後沈約等人的聲律論的誕生以及永明體的出現。後來,唐人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創造了律詩,標誌著中國古典的詩文學在聲律上的成熟與定格。其實,在沈約以前,謝靈運就在佛經的啟發下作過【十四音訓敘】,已開始探索漢語文字本身的聲韻問題,而這與他作為文人詩的代表是密切聯系的。
總而言之,晉宋之後詩之變革,不但涉及審美內質,也涉及形式聲韻,而這一系列的變化,都是紙的套用改變了詩歌傳情的物質媒介的結果。過去人們雖註意到晉宋詩道之變,而未悟變革之因,其一是因為歷代稱「詩」與「歌」時,往往兩個詞打通了來使用,故人們既忽略了二字的原義,也忽略了它們在漢魏前後的不同的形態,從而也就混淆了聲樂與文學的區別;其二是因為紙作為一種書寫的媒材,從出現到普及經歷了五六個世紀的漫長時間,故人們也就忽略了隱在其中的詩格的漸變;還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人們出於習慣,在考察文化時往往只從精神本身來著眼,而很難註意到物質因素的影響,雖然我們都知道物質生產對精神生產起著決定作用。
本文摘自【中國文藝思想通史】叢書之【魏晉南北朝文藝思想史】,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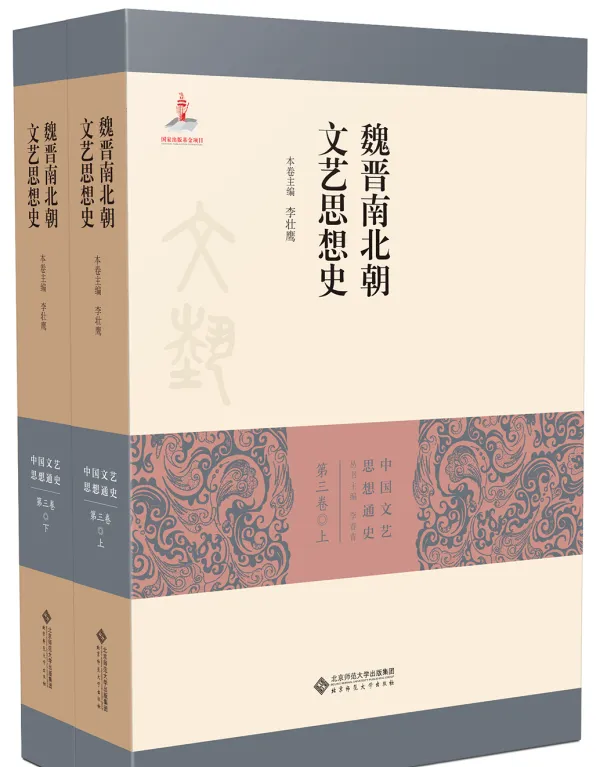
【魏晉南北朝文藝思想史】,李壯鷹/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