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影迷圈最熱鬧的事莫過於這件了:
北大放映於去年斬獲坎城金棕櫚大獎的影片【墜落的審判】。
映後交流陣容相當豪華——該片導演茹斯汀·泰瑞耶,北大的戴錦華教授、董強教授,主持人是【奇葩說】第五季的BBking陳銘,轉譯則是曾留學法國的北大博雅博士後繳蕊。
在想象中,這將會是一場關於電影創作和學術思想的深度交流。
但交流現場的幺蛾子簡直不要太多。
董強教授一上來就強調導演比他想象中年輕漂亮,然後翹著二郎腿,在場上用手機偷拍導演。
在戴錦華教授的發言獲得現場觀眾的掌聲後,他十分疑惑: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麽給出這麽熱烈的掌聲?」
聽到不同的觀點,他的態度是:
「如果你們都是這樣看電影我很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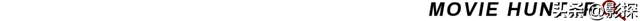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接著是陳銘。
身為主持人,發言比導演都多。
在性別等議題上顧左右而言他,還扯到了佛學,被現場觀眾噓了好幾次。
映後交流結束時,陳銘向大家道歉,但話裏話外的意思是:
我和董強教授是男性,所以才被現場的北大學生和媒體人針對。
網友們為這場映後交流精心制作了海報和詞條:
有的突出大師之爭;有的強調導演被主持人「審判」;還有的借「芭」諷今,戳穿董強和陳銘身上的「肯」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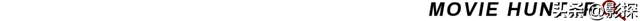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相關討論網上已經很多。
所以,我更想提及的點是,就在全網狂歡的當下,該片悄無聲息地上映了。
首日票房不到300萬,貓眼專業版預測總票房不超過3000萬。
這一票房成績,對於一部很可能是「今年院線最佳」的電影來說,實在太低。
讓我們將視角,放回到電影本身——
「墜落的審判」

Anatomie d'une chute
2024.3.29法國


性別互換,評論過萬
古今中外的故事裏,有一類出場率很高的角色。
她們既無法與社會建立正常連線,也為社會所不恥。
這兩種情態,往往很難說清楚誰先誰後。
她們可以有名字,比如【雷雨】中的繁漪。
但在口口相傳的故事中,在大街小巷的議論裏,比起名字,人們還是更喜歡叫她們的外號——閣樓上的瘋女人。
它聽起來很長,足足有七個字,遠沒有臥龍、鳳雛、及時雨、黑旋風等外號精簡,但在精準程度上,絲毫不差。
它涵蓋了地點、空間、狀態與性別,對同一類女性在社會處境、精神狀態等方面進行了一場血淋淋的審判。
【墜落的審判】要做的,是將其進行性別互換。
對,該片描繪了一位
「閣樓上的瘋男人」
。
電影開場,遠郊的獨棟閣樓裏,妻子和丈夫身處不同區域。
樓下,是身為著名作家的妻子珊卓,她正在接受年輕貌美女研究生柔伊的深度采訪。
談笑風生間,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曖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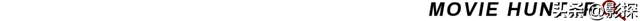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樓上,是突然開始播放爵士樂的丈夫薩穆埃爾,且音量越來越大。
很明顯,他在用這種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樓下的采訪不得不中斷。
珊卓說過幾天去出差時會給柔伊打電話,繼續兩人的采訪,並在樓上目送柔伊離開。
同時,剛給狗狗史努比洗完澡的兒子丹尼爾,準備出門遛狗。

但當丹尼爾遛完狗回家,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
再確切點說,是聽,是摸。
丹尼爾患有後天的視力障礙,史努比既是他的玩伴,也相當於他的導盲犬。
史努比快速撲上前去,不停嚎叫。
幾秒鐘後,丹尼爾在前方的雪地裏摸到了自己的爸爸,他腦後溢位的血已經多到形成血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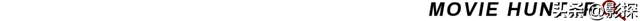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經法醫鑒定,死者是頭部受撞擊後滑動了一到兩米,才到最終的仰臥位置。
即是說,薩穆埃爾的頭部曾經碰到過鈍器,很可能遭受過他人的猛烈擊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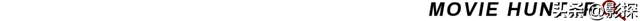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房屋的布局相當清晰。
一樓是連線積雪的地面,無人居住的儲物室;
二樓是放著椅子的餐廳,也是珊卓被采訪的會客廳;
三樓是閣樓,正在改裝的區域,有三角形的屋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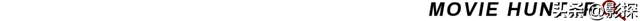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珊卓說,閣樓的三角玻璃窗戶,在救護車到來時是開著的。
丈夫當時正在改裝閣樓做民宿,平常他會不時開啟窗戶通風散味。
而樓下,丈夫墜樓點的正下方,有一個堆滿積雪的矮小屋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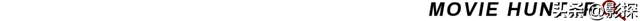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問題來了。
窗台的位置很高,薩穆埃爾意外墜樓的可能性很低。
外來的兇手?也不太可能。
第一,薩穆埃爾沒有仇人。
第二,有人闖進屋把一個健壯的成年男人從三樓扔下來殺死,且不驚動在家的珊卓,可能性幾乎為零。
與此同時,珊卓身上還出現了扭打傷最容易出現的淤青。
但她自稱是在廚房桌角磕磕碰碰,並且有兒子作證。
說到底就一句話:
我沒有殺害我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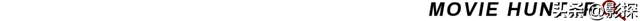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在她身陷囹圄時,作為大學同學的案件律師樊尚給出了另一種解法:
薩穆埃爾很可能是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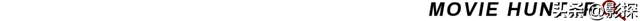
雖然丈夫在兒子還在的時候自殺的可能性很低,低到珊卓自己都不相信。
但稱薩穆埃爾是跳樓自殺,是珊卓現在最好的辯護策略。
問題也就隨之而來:
薩穆埃爾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
當真相揭曉,迎來的痛感,遠比死亡更加強烈。
!!!以下內容包含劇透!!!

死亡的「真相」
取證,實驗,尋找證人……
真正的庭審非常復雜,開庭已經在一年後。
由於沒有找到目擊證人,也沒有人認罪,警方的態度是「我們必須進行解讀」。
借由公檢法等方面的詰問,不難發現導演在引導我們去猜測薩穆埃爾死亡的真相。
這種引導,歷經多個回合,愈久彌深,直到我們認為自己猜到了真相。
Round1:質疑珊卓的人品,從而推論夫妻矛盾程度大小。
檢察官首先詢問了案發當天采訪珊卓的女研究生柔伊。
根據她們親密的聊天(喝酒,大笑),
以及珊卓曾經與女性出軌的前科,來判斷珊卓的意圖。
檢察官讓柔伊對珊卓是否「勾引」她做出準確的判斷。
Round2 :質疑丹尼爾的證詞,從而證明他想保護母親。
在情景再現前後,丹尼爾曾變更過一次證詞。
他曾認為自己聽到了父母的對話而非爭吵,因為他摸到了棚屋上的記號點膠帶,判斷自己當時正站在窗戶下面。
但事實上,無論在屋內還是屋外,丹尼爾都聽不到父母的對話。
丹尼爾撒謊了嗎?
Round3:用血跡分析,證明薩穆埃爾是在三樓遭到擊打後才墜樓的。
無論是死者的體重,還是護欄高度,都證明了珊卓擊打並推搡丈夫下樓的困難。
更何況,既沒搜到兇器,也沒有搜到DNA痕跡。
但是,也並非沒有可能性。
萬一,真相就藏在那0.01%的可能性裏,只是我們還沒發現呢?
Round4 :透過詢問心理分析師,判斷薩穆埃爾是否有自殺可能性。
珊卓表示,薩穆埃爾當初也有成為作家的機會,但他自己放棄了寫作。
丹尼爾四歲時,由於薩穆埃爾的疏忽,導致丹尼爾出了車禍,雙目失明。
當時他們一年都在醫院度過,財務也出現危機,薩穆埃爾開始服用抗抑郁的藥物。
珊卓認為,丈夫有復用抗抑郁藥物的可能,因為寫作失敗讓他痛苦萬分。
而在薩穆埃爾的心理分析師看來,這都是胡扯。
珊卓在指責薩穆埃爾,不僅如此,她還在怨恨他,PUA他……
總之,對於薩穆埃爾的死,出軌的珊卓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珊卓在和律師對談時明確表示,她就兩個想法。
第一,保護薩穆埃爾的形象。
別說薩穆埃爾曾經費盡心機,逼迫珊卓進入不理智的狀態,並錄下那些帶有攻擊性的話語。
第二,別把丹尼爾牽扯進來。
在跟兒子丹尼爾聊天時,她十分貼心:我不要你篡改記憶,我要你原原本本地說出你記住的事。
但當庭審尚未完全結束的某個夜晚,珊卓向兒子表示自己不是怪物,她和丈夫是真正的靈魂伴侶。
所以,庭審表面上是各方依據線索與細節來還原真相。
但本質上是各方站在不同角度,憑借非黑即白的「可能性」去重塑真相。
由於珊卓有重大作案嫌疑,在薩穆埃爾是否有自殺傾向等問題上,丹尼爾的證詞尤為重要。
為了驗證母親的話,丹尼爾給史努比餵了阿司匹林做實驗。
他看著史努比——這位玩伴、戰友、家人、導盲犬,從直接昏厥到眼神清明,再到一度嘔吐,最後好不容易緩過勁。
丹尼爾表示,自己對父親心理狀態是否正常、是否服用藥物等問題一無所知。
但他說起史努比曾經的一次嘔吐,與今天的狀態很像。
丹尼爾認為,那是史努比吃了父親的嘔吐物所導致。
而這,成為珊卓被宣判無罪的重要證言,成為「我們必須進行解讀」的最後結果。
但我們無從判斷丹尼爾是否是為了救下母親而撒謊。
因為情感上的巨大沖擊,會讓記憶發生混亂。
即使人在主觀上不想說謊,記憶也會在客觀上說出謊言。
一如父親的血跡,打破了丹尼爾安靜祥和的生活,成為他童年天空中的陰霾。
也一如在公開庭審中,擁有視力障礙的丹尼爾,在他人一次次的言語操控中,感官被一步步放大。
我們也無從判斷,這種解讀的結果是否真實可信。
我們只能確定,在庭審現場上,丹尼爾的解讀壓過了其他人的解讀。
我們更能確定,「我們必須進行解讀」的想法是危險的。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生活,經得起抽絲剝繭的追問與解讀。
婚姻、權力與性別
【墜樓的審判】曾經的片名,是【墜樓死亡的剖析】。
受審判的不止珊卓,需要剖析的也不止一樁命案的真相。
愛、權力、家庭、婚姻、性別,都是導演想要借由型別片的框架,去做的現實主義表達。
而這些關系中的復雜糾葛,就在法庭內外的剖析裏清晰顯現。
先是愛與權力。
越是精神碰撞越多的人相愛,越是會伴隨著越激烈的權力沖突。
它涉及的不只是權力鬥爭,還有核心的「自我」。
其中既有控制和馴服,也有退讓與和解,直到一方徹底受不了,選擇結束。
再是家庭與婚姻。
一個家庭是否和諧,一段婚姻關系是否良好,不是依靠所謂的「證據拼圖」就能拼湊出真相。
汪小菲&大S、傅首爾&老劉,這兩種曾經被網友艷羨的感情樣版,在短短數年時間裏,先後成為了負面教材。
因為人是動態變化的情感動物。
倘若不活在當下,而只是去翻過往生活裏的「舊賬」,去尋找有罪的論證,再美好的感情也會被消磨殆盡。
於是,在一個個負面教材的教導下,現在最流行的觀念是「智者不入愛河」。
最後,是性別。
在北大那場映後交流裏,戴錦華教授不得不詢問了一個自己都覺得過於基礎的問題:
「您認為性別議題是不是電影創作的核心?」
導演則給了一個相當直截了當的回答:
「是。」
如果把片中夫妻的處境進行對調,會發現丈夫的處境,其實是現實中不少女性正在經歷的困境。
她們全心全意為家庭付出,隨著時間流逝,換來的是身材的走樣和丈夫的背叛。
但凡抱怨,就是「歇斯底裏」的「瘋女人」。
然而現實社會早已習慣這種對女性的無形壓迫,並把它當成自然而然的事。
一旦性別互換,一旦受到這種壓迫的是一個男性,一旦他受不了這種壓迫去自殺,電影裏就出現了相當戲劇性的結果——
他不可能因為「這點小事」自殺,一定是他的妻子殺害了他。
而在口口相傳的故事中,在大街小巷的議論裏,如果自殺的人是一個「閣樓上的瘋女人」,即使大家都跟她不熟,現實裏也都有一個相當統一的答案——
人好好嘞,突然就喝藥死了。
如果非要說答案有什麽區別,也只是來自「瘋女人們」選擇離開的方式有所不同。
為什麽大家會認為薩穆埃爾沒有自殺傾向?
又為什麽會認為「瘋女人」在自殺之前每天「好好嘞」?
答案,藏在丹尼爾身上。
他有著多重內容。
從年齡上來說,他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
從身體狀態上來說,他是一位後天失明的視障人士;
而從體感來說,他覺得母親「是個怪物」,無法在玩耍時聽到父親放的爵士樂。
於是,一個絕妙的隱喻就此形成——
從童年起,我們便無法看清對方,無法傾聽對方。
而這樣的「視障」與「聽障」,又並非先天,是經由一次次生活的「意外」才被塑造。
薩穆埃爾曾對丹尼爾說過這樣一句話:
「(死亡)總有一天會發生,史努比的年齡已經不小了,你能想象他的生活嗎?他是一條優秀的,了不起的狗。」
在這個獨棟小屋組成的溫暖之家,薩穆埃爾或許就是那條總是被她忽視,卻一直溫厚、陪伴在丹尼爾身邊的史努比。
薩穆埃爾的死,或許也只是渴望「被尊重」和「被看見」。
珊卓在回家後親吻了兒子,躺在床上抱住了史努比。
暗流湧動的真相下,是還要繼續的生活。
而在現實生活裏,在一段段婚姻裏,在一個個家庭裏,在一則則親密關系裏,又有多少被遮蔽的真相?
看見了嗎?一直陪伴你的史努比在落淚。
聽到了嗎?別讓你喜歡的音樂(發出的噪音),掩蓋了TA落淚的聲音。
這關於性別,也不止性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