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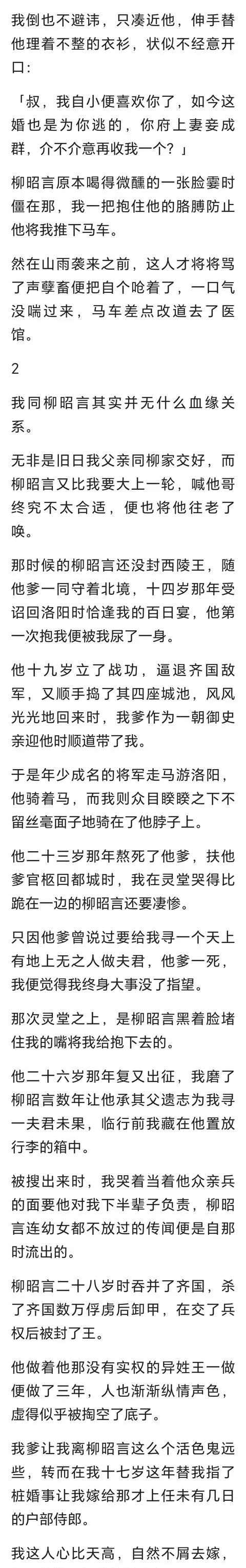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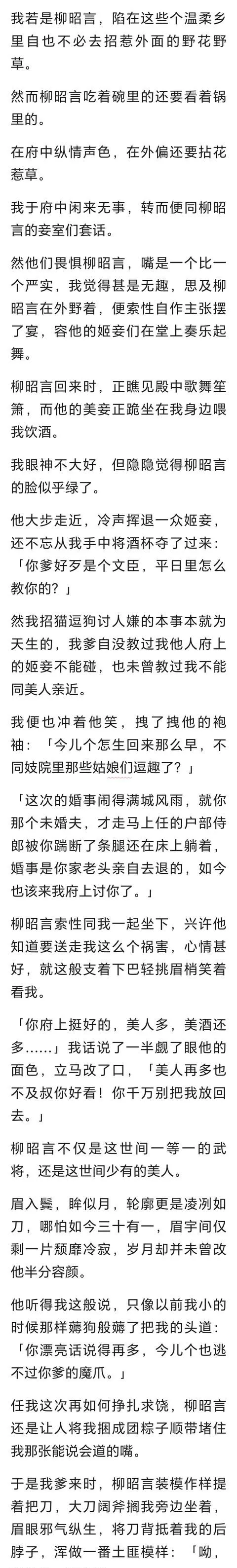
「小女大婚之时西陵王将其掳走,如今这般又是想做什么?」
我爹在朝中待了半辈子,什么场面都见过,自是一番人精模样,全将我逃婚这过错全都赖在了柳昭言头上。
然柳昭言却也认得干脆:「今儿个很简单,给本王筹十万两,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然本王就将她给剁了。」
世人都传柳昭言嫖妓养女人早就将打仗得来的赏赐与家底亏空个干净,如今将我拐回去却打着这么个如意算盘。
我和柳昭言都以为我爹会拿钱来换我,我呜呜咽咽地同柳昭言摇头,不妨我爹却是出了声:「剁吧,我看着。」
柳昭言愣住:「你女儿不要了么?」
我爹则气定神闲地摸着胡子,径自朝主位一坐:
「小女顽劣,如今婚礼上这番一闹,自也无人敢娶她,泼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由不得我管,西陵王既掳走小女,应当负责。」
他顿了顿,复又加了句:「可小女毕竟是老夫独女,西陵王又未娶正妻,这正妃之位理应由小女来做。」
柳昭言本想坑我爹,不妨却反过来被我爹坑了一把。
当场拽着我爹的领子将人拽进后屋。
我被冷落在一边自是郁闷,手在椅子上磨了半天,到底将绳子磨断了,不声不响地绕到后屋靠在窗边旁听。
那会儿他们谈得应当差不多了,我也再听不得什么,我只知柳昭言做了这么个接盘之人甚是不悦。
而我爹临走时拍了拍他的肩,只留了一句话:
「阿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如今落得这般下场终归是朝廷对不住你,莫要因此生了恨心,绝了自己往后的生路。
我本不想让思潼与你有所牵扯,然她偏生欢喜你,我这几日想了想,将思潼放你身边,她未必不能救你。」
「你真觉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能让我回头?」柳昭言却蓦地冷笑出声。
那时正逼近黄昏,我立于窗边,透过窗前薄纱看不清柳昭言说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只觉得他身影萧条得过分,总容我生出那么一二不该有的怜悯来。
4
不出三日,我同柳昭言便草草办了场婚礼。
毕竟这事儿算不上光彩,那差点娶我的侍郎头上还是一片青绿。
柳昭言初时并不愿,但在我拿着绳子深更半夜要挂老槐树上吊时,柳昭言黑着脸把我抱下来,吩咐将树砍了后,便也答应了我。
于是我叫他叔一叫叫了十七年,洞房花烛夜喝合卺酒时我改口唤了声夫君,柳昭言吓得手一抖径自将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这酒泼花了我的妆也就算了,当事人偏还笑出了声,我正待发怒他却是拿出一方帕子替我擦了脸。
「柳昭言,你喜欢我吗?」我气势汹汹地问。
他则戳了戳我额头,还不忘笑话我:「小孩子说什么喜欢?你可还小。」
柳昭言惯会敷衍我,然而他那夜却甚是温柔,细致地将我头上的钗环摘下,又褪去一身繁重婚服挂在一边,在我以为他要同我睡一处时,他却道:
「你先睡吧,我去院外透透气。」
「我们今儿个大婚,你第一天就想出去找女人,小心我告诉我爹。」我拽着他衣袍不让他走。
柳昭言无奈:「虽然你总不让我省心,可好歹是我看着长大的,怎么可能让你落人笑柄?我就在院外守着,过会便进来。」
我心知柳昭言一时半会也接受不了便宜侄女成他娘子的事实,今夜自也不急着同他圆房,便也随了他。
那夜直至我熄灯睡下,半夜复又梦醒之时,床榻边依然是空的。
我遂披衣起身走至院中,月光溶溶而下,映着光下竹影随风而动,蝉声于耳边凄切鸣叫。
我四处寻他不见,正觉得柳昭言又哄骗我,却不妨回身时看见屋顶上坐着的人。
此时他微曲着一条腿,另一条腿垂在檐下晃荡,手中还拿着壶酒,正垂眸笑看着我:「深更半夜起来作甚,还怕我跑了?」
「那你深更半夜坐屋顶上又想作甚?」我当即反问。
他兀自喝了口酒,眼神幽远地看着天边零落的星星,声音也空辽得很:「我在想让你嫁给我究竟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
以前的柳昭言并不是这样的,他不会去顾虑什么,更不会在决定了什么事后依旧难以抉择,大半夜爬屋顶吹冷风。
我总觉得我是遭嫌弃了,索性在檐下同他张开了手:「抱我上去。」
柳昭言今夜甚是好说话,从屋顶跃下,一把抱过我的腰,旋身便带我上了屋顶。
在沉沉晚风中我闭眼抱着柳昭言,哪怕已然坐在屋顶上偏还不肯放开他。
他大概觉得是夜里太冷,怕我冻着,还将我往怀里带了带。
「我知道你那些妾室都是幌子,每日花街柳巷乱窜也是为了做戏。」我在他怀里轻声开口。
柳昭言并未否认。
而我则又道:「既然如此我便是你唯一的娘子了,我同你成婚哪还有什么对的错的。」
「可嫁给我,定然不会有什么好归处的。」他闷声说。
我觉得他想得太多,索性趁他不备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柳昭言在娶我这方面已经够想不开了,总觉得是他老牛吃了嫩草,今夜我偏又在老虎头上拔毛亲了他。
霎时间,柳昭言方才的愁绪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拎着我的后领将我提了起来:「韩思潼,你胆儿肥了,连你叔都敢亲?」
5
其实柳昭言是个可怜人。
他娘死得早,自幼便在北境长大,从北境第一次回洛阳那年他年仅七岁,那会我还没出生。
听我爹说啊,他当时年纪小,总还想不通,为何北境风沙袭人,尸体遍野,齐人为何总在北境挑起纷争。
他人生初始,见到的却尽是烽烟刀鸣。
因而他初回洛阳,见着满目纸醉金迷,安逸自在,最初觉得不忿,不忿以后便也不愿离开了。
临别前,柳老将军想将他给拖走,他当时硬是抱着我爹的腿不放,说要给我爹当儿子,哭得直哆嗦,非要赖在这不走。
这洛阳繁华安乐与他往日认知差距甚大,他才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日子过得都如他所知那般凄惨。
一个小孩子这般想其实并没什么错。
可柳老将军是个粗人,自顾不得当时柳昭言心中那些千回百转的心思,只一句话就灭了他往后的所有念想。
他提着柳昭言的领子将他提溜上了马,告诉柳昭言,这里并不属于他,他天生就该吹尽北地风沙,天生该杀人拜将,如今贪图一时安逸,往后便只能死在敌人的刀下。
小孩子哪能接受这些?
我爹只知道他离开的时候一直在哭,哭得甚是撕心裂肺,直至马行远了都没有停歇的意思。
于是十四岁的柳昭言再回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当时传闻柳昭言十三岁时便带兵立了战功,取了敌军副将的首级。
我不知道他是几岁开始上战场杀人的,只听说他第二次回洛阳时性子沉寂了不少,也失了本该属于他的一身少年气。
他看花看月,看洛阳繁华似乎都已入不了他的眼,整个人反倒透出一股死气来。
我一直觉得,柳昭言不适合当将军,他幼年时既贪妄富贵平安,畏惧战争与鲜血,那么他便不该去杀人。
他合该当一个文臣,哪怕当讨人嫌的纨绔公子哥也好,这般逼迫他只会将他重塑成边界感甚强之人,直到成为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异类。
他面上第一次透露出那么一二鲜活时,便是在我百日宴上抱我之时,哪怕我那时尚在襁褓,还尿了他一身,他还是抱着我笑出声来。
我不知他当时是如何笑的,大概便如冬日雪融,秋霜初化那般,定然恍眼得很,胜过旁的千万般颜色。
那会北境平安了三年之久,他便在洛阳待了三年,每日严于克己,从未曾懈怠半分,而我亦从襁褓中的娃娃成了牙牙学语的幼童。
他后来不练武时便总爱抱着我,他本少言,自也不会哄孩子,我极爱抓他垂落腰际的发,而后放嘴里含糊不清地咬。
他便也将自己的发从我嘴里拽出来,反倒伸手戳我的面颊,我同他笑他便也跟着笑,我哭他便手足无措地杵在那。
我爹见他甚喜欢我,因而两府往来时,见他抱我,便也极为放心的在他回去时让他把我带走养上几天。
柳昭言哪会养娃娃呀。
我总是干干净净的被他抱走,灰头土脸的被他送回来。
他十七岁那年又奔赴北境,临走时并未有诸多留恋,唯一求的一桩事就是想把我带走。
后来似乎也觉得自己这要求挺过分,说出的下一秒便反了悔,临走时未曾再求什么,走得比谁都要干脆。
那时我其实尚未记事,一切只是从我爹那得知的,我隐隐知道自己也算被少年时的柳昭言喜欢过的。
他在后来的两年里立了战功,亦逼退了齐国之人,再回来时,少年将军已然成名。
我年纪尚小对他总还有些模糊印象,再见时便也生了亲近之心。
不知是不是重逢那天我非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骑在他脖子上让他丢脸的缘故,在我记事后,他似乎并不喜欢我,待我冷漠得很。
我虽黏他,他却并不爱搭理我,总让我滚到一边别杵他面前碍眼。
只不过啊他府上总有吃不完的糖以及各种玩意儿,他自己定然用不着,唯一的可能便是为我留的。
而我在他面前哭上一哭,他便蹲下来面无表情地给我擦眼泪,开口语气也很冰冷:「不许哭。」
我因此哭得更凶,而他只会僵硬着身子同我对视,眼神偶露无措。
直到我抱着他将眼泪蹭他衣服上,他才会将手搭我背上轻轻拍着我的背缓缓抱住我安抚。
他在洛阳与他在北境的时间应当是对半而分的,我记得他陪过我一些年,又分别过一些年,如此循环往复。
他后来虽不喜我,可柳老将军却甚喜我,我曾在将军府吃糖吃坏过几颗乳牙,最后牙疼难忍的时候还将一切错推给柳昭言,柳老将军训他时我便总躲在老将军背后同他做鬼脸。
老将军还不止一次说将来要给我寻一个天下至好的夫君,我总背着柳昭言偷偷告诉柳老将军说我将来要当柳昭言的媳妇。
他便也眯眼笑着应下来还同我拉了钩,承诺我长大后定然会逼迫柳昭言来我家提亲。
只可惜,柳老将军死在我九岁那年,因而所有的一切便也都不作数了。
那一年柳昭言扶柳老将军的棺椁回到洛阳,我在灵堂上又一次见着柳昭言,他当时在棺前跪得笔直,面色却惨白得吓人。
听说柳老将军当时身陷敌阵,而齐军已然逼近边境小城,柳昭言在救他父亲与救一城百姓之间选择了后者。
听说柳老将军死无全尸,是柳昭言亲自拼凑的尸骨。
还听说啊,柳昭言在那一战中也负了伤,差些便也死了。
我第一次接触生死,除了畏惧与恐慌,却也还被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占据。
柳昭言没有哭,我却在柳老将军的棺前哭得甚是凄惨,柳昭言见不得我哭,他踉跄着站起走到我身边,将我抱在怀里轻声问:「哭什么?」
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难过,却说不出旁的理由,到嘴边只能哭着答:
「柳老将军不守诺,答应给我的夫君还没兑现便死了。」
柳昭言听了却是空落落地笑,继而指着灵堂便骂:
「恬不知耻的老东西,说死便死了,留下一堆烂摊子别想我帮你收拾。」
他将我抱出灵堂后,却出奇的没有将我放下,就只是抱着我,直至我闻着了血腥味,低头瞧见我被血浸湿的衣裙以及淋漓滴落于地的鲜血。
柳昭言似乎也才反应过来,在我惊慌失措的哭喊声里,他却是捂住我的眼睛,他说:
「思潼,别哭,只是伤处裂开了而已,没事的。」
他说没事我也信了,不让我哭我便真不哭了,只死死搂着他脖子不愿松开。
他抱着我走得很慢,直至走进一处屋子,他便也就势靠坐在角落,抱着我将头埋在我的颈边,手捂着我的眼始终没有放下。
我问他疼不疼,他说我抱着他便不疼了,我又问他难不难过,他说我哄哄他就不会难过了。
我依稀同他说了许多话,他也极有耐心地答我,直到他声音渐缓,我如何唤他他都不再应,而他一直捂着我眼睛的手也垂落下来,我才看清身下氤氲了一地的血泊。
我终究还是在他怀里哭嚎出了声。
及至后来的许多年,柳昭言不仅一次借此事怨怼过我。
他说我若听他的不去哭,无人听得我的哭声去救他,他早就可以死了,也省得日后继续被我祸害。
我则不理他胡言,反而逼他发誓,他是因为我才活下来的,往后我若不允,他定不能轻易去死。
然而毕竟我年纪小,柳昭言也始终把我当成个孩子,我说的话柳昭言一向不当回事。
我很早便明白了,柳昭言这人是世间少有的混蛋。
6
柳昭言一直笃定我脑子有病,然而有病的其实并不是我。
回门时我爹说有病的是柳昭言,他分明有心病,轻易治不好,也轻易想不开。
我觉得这话并不错,却不敢当着柳昭言的面同他说。
其实他姑且算是个合格的夫君。
只因娶的人是我,他便也收敛了不少,整日盘算着遣散一众姬妾,也再未找过他近年在那些烟花柳巷里认识的相好。
他说我还小,自不想宠妾灭妻让我被世人笑话。
柳昭言事事其实都替我考虑到了,可我却依旧不想同他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
他每夜甚是自觉地打着地铺,从未对我生出旁的半分心思。
直到那夜下雨,雷声入耳总还搅得人难以入眠,我思及旁的姑娘都是害怕打雷的,便索性起身顺带踹了一脚正睡在地上的柳昭言,用平静到没什么起伏的声音同柳昭言道:「叔,我怕。」
「你这像怕的样子么?」柳昭言笑道,而后自顾自翻身继续睡。
我索性下了床,死命晃着柳昭言,偏不让他再睡。
柳昭言彻底被我磨烦了,猛地起身吼我:「韩思潼,今儿个有完没完了?」
我向来是没完的,只不过演技不甚好,轻易哭不出来,柳昭言每每凶我,委屈劲儿上来,自然也落了泪。
因着柳昭言这一吼,我倒真溢出几滴泪,抹着眼睛道:「可我还是怕。」
自小到大,我哭上一哭,柳昭言定然是拿我没办法的。
直到我如愿让柳昭言上了榻,我初时只是让他抱着我,在他呼吸渐缓之时,低唤了几声他的名字,见他不应,索性便也将手伸进他里衣中。
柳昭言旧日征战,身上落了不少伤,我触及他身上那些疤痕之时早已忘了再去撩火,反倒将他里衣又扒开些想看清他身上的伤。
然而我身边之人如蛰伏已久的野兽般,在我并不设防时翻身将我整个人压制在床上。
暗夜里那双眼睛带着森然寒意,继而伸手捏住我的下巴,声音也冷得吓人:「你到底想怎样?」
我被他这般模样给吓到了,故作镇定地亲了亲他的面颊,他却蓦然俯身吻了下来,动作甚是粗暴,箍着我不让我有丝毫喘息的机会。
那眼神也像要将我抽筋扒骨般,甚是吓人。
我踢他踹他,他反倒一把扯过我的发,嘴上犹自道:「你想要那我便给你,你现在在抗拒什么?」
直到这次我当真呜咽出声,他才停下动作,身上的戾气渐收,轻轻揉着方才我被他捏疼的下巴:「别哭了。」
其实我知道,柳昭言只是想吓唬我,让我厌恶他,继而远离他,不再与他纠缠。
可真把我惹哭后他却又反悔了,只能收起方才故作凶恶的神情安慰我。
可那会我也当真受了惊吓,心里颇觉委屈,被他抱怀里哄时心中依旧揪成了一团,什么囫囵话都说出了口:
「柳昭言,要是我不在你风光回城的时候骑你的脖子,不在牙坏的时候跟你爹告状,不对你胡搅蛮缠撒泼耍赖,你是不是就不会这般讨厌我?」
我在他怀里抽抽噎噎语无伦次地说,他到底也慌了,给我擦着眼泪不经思考就道:「我没讨厌你。」
「那你喜欢我吗?」我兀自抹了抹脸,又问。
柳昭言苦笑,在我以为他又要糊弄过去时,他却道:
「思潼,你是我这辈子最珍视的人了,你该有光明如锦的前程,而不是跟我这么个烂人待在一处。」
说来的确可笑,他分明是一国之功臣,人人都该敬慕仰望,可他却偏生同我说他是个烂人。
7
柳昭言的姬妾据传闻都是他于国中各地寻访来的美人。
可柳昭言却并不让我同她们接触。
直到她们被遣散离府那日,有个姑娘递话想要我送送她。
我本不欲去,然那个姑娘是在柳昭言身边待得最久的,我不想让柳昭言总把我当个小孩,他这些年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旁人我还是想寻她问问。
初到约定之地却并无人赴约,我浑浑噩噩尚未探出究竟,反倒在打算离开时被那位姑娘用利器抵住了脖子。
好巧不巧柳昭言便在此时赶来了。
平日我在柳昭言面前寻死觅活也就罢了,单纯就是气上他一气,自也不可能真的去死。
然而真当如今生死悬命之时我却还是怕的。
倒也不是怕自己就这么死了,单纯只是怕柳昭言。
柳昭言少时沉默寡言,中年又放浪形骸,在谁看来都是个没什么脾气的,自也没几人知道他疯起来是个什么样子,毕竟看过他发疯的大多都已经死了。
「在我府上待了这些年,总该知道规矩,让你做什么便莫要违背我的意愿,你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先把她放了。」
柳昭言在数步之外站定,声线却没什么起伏。
我身后那姑娘只是冷笑,手里的剑又往我脖子处送了送,我生怕她一个不稳直接划了我的脖子。
她故作镇定地开了口:
「西陵王,你当年覆灭齐国,世人都说你功高盖主,你遭帝王猜忌,被冤枉有谋反之心,还被逼迫上交兵权,整日只能装作欢场浪子,来借此抵消帝王疑虑。
你心中不忿,又想助齐国复国,借齐国之手霍乱整个楚国都城,便私自在府里藏了齐国暗探,又暗中豢养死士无数,本该大业将成。
可你现在为了这么个女人将我们所有人尽数送走,是为了自此收手么?」
一个国家可被覆灭吞并,但这个国家的人是没办法杀尽的。
齐国那个无能的君主在国破时连同他们齐国数位重臣一同失踪,朝中亦有人言齐国残军早就已经乔装成普通百姓,暗藏于各城之中一直在寻机反扑。
可又有谁会想到,暗中相助他们的会是当年亲手覆灭了齐国的柳昭言。
柳昭言此时的声音偏生冷静得吓人,他一字一顿开口:
「我不会收手,谁都不会让我收手的,如今送你们离开,只是因为你们使命已尽,我不用你们再为我收集情报,也不必留你们在我府上做齐国国君的眼线。」
他方说完,后方有暗器蓦地射出,那姑娘身子微僵,似被射中。
而她似乎知道自己入了死局,临死还想要再拉个垫背的,利器将将要划破我脖子之时柳昭言却一刀斩断她执剑的手,而后将我整个人托拽进他怀里。
柳昭言捂住我的眼睛,便又挥了刀,我面上溅了一片黏腻,有什么东西滚落于地,我闻到浓重血腥味,而抱着我的那人始终捂着我的眼。
我听得他同旁人冷声吩咐:
「离府的那二十三个暗探一并杀了,将她们的头颅送还给她们齐国的君主,顺便替我警告他,不日起事,没有我的吩咐,还请他的人莫要妄动。」
柳昭言一直都是人人畏惧的杀神,亦漠视人命到了极处。
当年他覆灭齐国,万名俘虏被他尽数坑杀,如今更不会在乎这二十多位曾假扮成她姬妾的齐国暗探。
他不让我看面前的血腥场景,只将我带离了此地,一路无话,直至回到屋中,他到底放开我,而后竟是一个不稳扶住身侧桌沿,捂着自己的心口急促喘息。
在我不知所措上前想扶他时,他却蓦地抬眼看我,那眼神里的悲伤太过浓烈,开口时就连声音也带了颤,他说:
「我这辈子受的最重的伤便是送我父亲棺椁回洛阳前的那一战,长刀自我胸骨划至小腹,齐军羽箭亦擦过我的后心将我穿透。
我带伤奔赴洛阳送我父亲尸骨还乡,并不觉得疼,可那天太冷了,只有你这小家伙身上还有些热乎劲儿,我想抱着你等死,好歹不至于死得太过难受。
可你偏生连死的机会都不给我,让你不要出声,你还哭着将人给引来,非要从地狱里将我捞上来,你既让我活,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若出了事,我会如何?」
我想过的,我也知道,但我却不敢说。
我只紧紧搂住他的腰,像他以往安抚我般轻拍着他的背,可他身子却颤得厉害,我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战栗,他说:
「我弃过你一次,始终是我对不住你,你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想报复我,所以故意入了她设的陷阱?你恨我当年弃了你,恨我当年不要你。」
「思潼,可我觉得疼啊,疼得喘不过气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疼。」
听他这般说,我却也难过起来,小声哭喊道:
「叔,我错了,我以后都好好保护自己,再也不去轻信他人,我不会死,你不要再疼了。」
虽说做人不能太自视甚高,可我就是知道,柳昭言将我的性命看得比他自己的还要重。
我犹记得十二岁那年在他出征前夜给自己备了一袋干粮,躲进他置放衣物的箱中。
那会我年纪甚小,胆子却甚大。
怕自己被闷死,每夜无人时偷偷从箱子里钻出来透风,这般过了七八日才被发现,被人拎至了柳昭言面前。
柳昭言自他爹死后,整个人便颓了,因我没让他死成,他记仇得很,在我面前话变得挺多,却多数是来挖苦我的。
他见我第一眼就毫不客气地凶我,我心中悲愤无以复加,便当着他身边十数位兵卫的面哭着让柳昭言对我负责。
我至今都记得他当时的脸色甚是五颜六色。
那会已行军半路,他想让旁人送我回去,终归放不下心,便将我留在他身边。
他这次复回北境,本是为了寻仇,然我当时在军营中被护得很好,以至于并不知他当年的打法有多不要命,刹鬼修罗之称便是从那时起传出的。
他扒了齐兵的皮做战旗,将他们的头颅剔骨做夜灯,甚至一把火生生烧死百余名战败俘虏,将他们焦黑的尸体堆砌于边关闹市。
手段太过狠辣,不留余地,终究会遭到反噬。
于是老天又一次让他做了选择。
齐兵欲行险道过雁门关,一旦被他们踏入,雁门关后的那几座城池必遭屠戮。
那一战中,齐人为报复柳昭言,亦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分道去屠了他的兵营。
为将者,身上担着诸多责任,又有诸多不由己,柳昭言选择什么本就不言而喻。
他为了守住雁门关弃了我和营中的一众伤兵。
于是兵营中留下驻守的伤兵尽数死了,有数人濒死之际将我压在了身下,阻隔了齐兵的视线,也让我保住了性命。
可柳昭言并不知道。
旧年他在平了雁门关外一战后立刻折返营中,遍处寻不见我的尸骨。
他以为我死了,同柳老将军一样被齐人砍成一堆碎尸烂肉。
他后来说,他跪在那心疼得似炸裂一般,直到四肢百骸渐冷,看这满目尸骨都已然麻木。
他觉得他爹走了以后,若还有什么是他没办法失去又没办法割舍的,便只剩我了。
后面的他没说,但我知道。
那时我被压在重重尸骨之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爬了出来,第一眼便看见跪在不远处的将军手中持着刀朝着自己的脖子利落地划了下去。
他以为我死了,所以他要将他自己的命偿给我。
我蓦地在他身后哭嚎出声,他手一颤刀也落了地,只是颈侧却留下一道极深的伤口,还在汩汩冒着血。
本就是一刀削去半边脖子的力道,他连自刎也向来够狠。
就差那么一点,我同他便是一辈子的天人永隔。
他是因我自刎,又因我收了手中的刀。
他既答应我去活,便也当真只为了我一人去活,我若哪天死了,他也决然不会多活一日。
从那一天开始,我便也知道,我的命同他的是连在一处的。
因而后来我逼迫他娶我,我分明知道他有多怕我死,可总还用死威胁他,可劲地戳他的心窝子。
现在想想,终归是我的不是。
8
其实柳昭言自从灭了齐国回到洛阳,在庆功宴上被当今圣上摆了一道后,放权放得甚是干脆。
我自是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而他则满心满眼都是那些个秦楼楚馆的花花姑娘。
然我爹始终是个清醒之人,他不让我同柳昭言一处,甚至直言柳昭言这男人心思已经歪了,我如何都要不得,还不惜给我安排了一桩不甚靠谱的婚事。
如今我同柳昭言虽还未生米煮成熟饭,但毕竟阴差阳错之下成了婚,也算一根绳上的蚂蚱。
我最近总在纠结该怎么让柳昭言收手。
毕竟他干的这事儿如何都说不通,真干成了他同样也里外不是人。
齐人杀他父亲,亦毁了他一辈子,他反手灭了齐国,一个一心为家国的将军,如今又为何要相助齐人复国?
七日后是皇帝的生辰宴,柳昭言自也不避讳我,他说他打算在当日动手。
我去寻他那会,他为了将我撇干净,休书都写好了。
他虽是武夫,却写得一手漂亮字,然而他第一次为我动笔送的不是情书,而是休书。
他气定神闲地在院里掷飞镖玩,而我则气急败坏地将休书给撕了个粉碎。
我甚少同柳昭言发怒,只因我年纪小,同他发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只认他捏扁搓圆的纸老虎。
然那次我先是待柳昭言一阵拳打脚踢,还嫌不够般死命咬他脖子。
他旧年颈部那处伤极深,因此落了疤,我咬起来觉得硌牙,便也无理取闹地埋怨起他来。
柳昭言果然看着我笑,我自也笑不出,索性便同他说了狠话:
「柳昭言,你要是死了,我也会疼,我不仅疼,我还要殉情跟你死一处!」
柳昭言果真在我又欲说什么时死死捂住了我的嘴,瞪我道:
「年纪小什么浑话都说得出口,赶紧给我把话收回去,我自不要你下来陪我。」
柳昭言话一说完我同他自己都愣住了,他说漏了嘴,而我亦得知了他这次本就没打算活。
他遂也叹了口气,似被我搅扰得头疼,坐在一边木桌上兀自按着自己的额头,良久才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他说:
「思潼,我爹自幼便教我忠君忠国,我总在被迫做着我无法理解的事,被迫杀人,被迫在家国与私情之中来回撕扯徘徊。
我一直不认同这些道理,可依旧不知缘由地去奉行,老天总让我在家国与至亲中做选择,我其实畏惧杀人,厌恶战争,甚至并不想将所谓的家国百姓放在第一位。
我很早就累了,在我第一次做出抉择的时候,我便觉得这般无休止的战争于我来说本就是酷刑,他人言我大义,我却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尽是错的。
我分明厌恶杀戮,可到头来却只有借着杀戮才能得到快慰与解脱。」
他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看我,只看着桌上那把陪了他大半辈子的长刀,刀上的血迹永远抹不去,挥刀时的刀鸣便如万千怨魂悲鸣。
我心中所有愤懑终究渐消,我知我喜欢他,在窥得他那些难言的心思后却只剩悲悯与心疼,我缓缓走近他坐在他身边,头顺势枕在了他肩上。
「我为国征战半辈子,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想留住的也没能留住。
我覆灭齐国,居功后被帝王畏惧猜忌,为了保住性命还要双手奉上自己的兵权,我不忿自然也不平,我甚至觉得这般的家国挺可笑的。
都城之中为争权夺利,人人醉生梦死,边境之上为护一方国土,人人命不保夕。
归根究底,人的命终究是不同的,我总要去恨些什么才能让自己接着去活。」
他将他的恨说得如此轻易,反倒让我愈发无措起来。
我轻声问:「所以你要助齐国复国与自己的故国抗衡?」
「不会的,我还不至于这般胡来。」
他笑着看我,眼睛微弯,继而轻轻拨开我扫至眼尾的碎发,极平静地说出了比我的猜测更胡来的预想,「齐国不会复国,我只是想借他们杀尽朝中武将文臣,让偌大朝野形同虚设,然后我啊,顺势将所有齐国余孽一网打尽,在报复了所有人之后再好好的去死。」
柳昭言所计划的一切太过疯狂,他不仅要自毁,连带着还想让所有人都陪葬。
他哪是想要造反?分明就是已经在战场杀疯了。
他如今是世间至恶之人,也难怪我爹说他连带着将自己的生路都绝了。
「那你可舍得下我?」我恨声问他。
他显然被我这话问愣住了,思考良久才道:「自是舍不得的。」
我在他说舍不下我的时候,欺身搂住他的脖颈吻了他。
他这次没有推拒,反揽过我的腰身回应了我的吻。
彼时秋日红色枫叶落了满院,在一吻终了后,我倚在他怀里,声音不由自主带了无措与委屈:「柳昭言,你真想走也可以,你得把我一起带走。」
「小孩子莫要说气话。」
「你死了,没人愿意娶我这么个寡妇。」
「我活着时是杀神,死了自然也能成厉鬼,你往后瞧上谁,那人若不敢娶你,我做鬼都不放过他。」
「别人求死都是心如死灰,无可留恋,可你哪怕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我,黄泉路上哪轮着你掺上一脚?」
「那我到时候尽量靠边站站,再走慢一点,不碍着旁人去死。」
柳昭言早该死了,或死在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深秋,抑或死在五年前自己的刀下。
是我一次又一次留住了他。
他对人世无甚留恋,生死皆无畏,可我却偏要强求。
9
柳昭言赴宴前一晚大抵知道同我讲理讲不清,索性也狠了心肠骂了我一通。
他嫌我烦他,说我缠人,还言我从小到大都是个讨厌鬼。
彼时齐人的残兵已然乔装入了洛阳,将会于第二日月升之时集于宫外。
而柳昭言手上有百名死士,亦有他爹旧年的残部,在齐人带兵攻入时,他们也同样会将整个皇宫包围。
不过是一招螳螂黄雀的把戏,偏柳昭言玩得极欢。
然他偏也不贪权势,他恨齐人,同样也恨皇城中君谋权斗的把戏,他索性玩了场大的,临末两方俱损他解了心间之恨顺带再把自己搭进去。
我是如何都拦不下柳昭言的。
他离开前留了几个死士护住我,任我如何哭喊眼睛都不曾眨一下,就只捂着自己的耳朵皱眉看我:「近些年怎么愈发能嚎了?」
生死攸关处,偏他还在闲话家常。
他知道甲胄硌人,穿之前似也纠结了一番,然后同我张开了手:「最后再让你抱一次,你过不过来?」
我哭着跑过去挂在了他身上。
他揉着我的发,在我耳边骤然笑道:「思潼,你既不愿同我和离,我自也舍不得你因我而被牵连的,所以你……不要怕。」
他这话甚是含糊,偏在我欲问个分明时,他却不想再开口解释什么。
后来直到他走,我试图细细理出一些头绪来,也大抵猜到了一些。
我从始至终于他来说都只是一场难以设防的意外,若我当初嫁了人,安安心心当着侍郎夫人,那么所有的一切便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他借齐国之兵谋反自毁,我同他毫无干系,自也不会被他牵扯半分。
然而我嫁给了他,他是不是会为了我,给自己留有半分余地?
我猜得其实并不错,柳昭言到底收了手,在后世落了一副他最讨厌的愚忠之名。
当日宫变,齐兵攻入皇宫,宫内却空无一人。
柳昭言临末良心发现,也到底不欲让自己落一个罪臣贼子的称号,老老实实地装作一个同齐人为伍,忍辱多年只为将齐国余孽尽数杀尽的忠臣。
宫中之人早早撤离,皇帝亦让柳昭言带着他的残部与死士将所有齐国余孽包围。
彼时齐国国君被杀,剩下的士兵无主,再加上柳昭言不要命的打法,也已然成了强弩之末。
可柳昭言千算万算,都未曾想到,在一切已成定局之时却有一个杀手藏于他的死士之中。
那夜宫中火光彻夜未熄,我在晨光初现时见着了柳昭言的尸体,安安静静躺在那,已然没了任何生息。
跟着他的副将说,当时齐人已降,可柳昭言杀红了眼,不欲将其收押,非要赶尽杀绝。
然而柳昭言旧年战场上负了不少伤,哪怕好了仍然是多年的隐疾伤痛,如今身手早已不如年少气盛之时。
柳昭言在天明时终究力有不殆,被伪装成死士的齐国杀手看准时机趁他不备一剑贯穿了心口。
旧年战场之上刀剑无眼,他数次涉险,九死一生,都安然活到现在,又怎可能会死在这么个小小的宫变之中?
到头来啊,他愿意为我让步,没有去做那遗臭万年的恶人,却不愿为了我去活。
我想,到了如今,他一生被命运玩弄,一生命不由主,也算彻底解脱了。
10
尾声。
柳昭言这一死,自然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他受了追封,而我亦无须同他撇清关系,安安静静在西陵王府做着我的寡妇。
我不愿再改嫁,转而在府里养起了小白脸。
这小白脸模样甚俊俏风流,观面相也不过才二十出头,年轻貌美在我爹看来自比某个老家伙要好上许多。
我自不顾旁的,偏爱拉着他在柳昭言牌位前调情。
小白脸甚是胆大,在同我上了几次床后,不仅将柳昭言旧日的刀沉了塘,还将柳昭言的牌位给砸了。
不过是仗着我的宠爱任性胡来。
柳昭言死得干脆,临死前留给我的也不过是王妃的无用身份,以及他多年谋划起事被彻底掏空的家底。
我恨他恼他无处发泄便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拿小白脸撒气。
小白脸别看他长得好看,衣冠之下一身的疤,我胆子小自不敢去碰,只可劲咬他的脸拽他头发。
他也不是没脾气的,在我一口又咬坏了他花大价钱做的人皮面具时,他也彻底怒了,一把将脸上那缺了一块的面具撕了下来,恨声道:
「韩思潼,家底都空了,你两三天就咬坏一个,日子还过不过了?」
「以前嫖姑娘花钱如流水,如今没了钱你不得可劲在床上讨好我求我养你?」
我嬉笑着看他,手细细描摹着他甚是深邃的眉眼,如何都舍不得撒手了。
这小白脸正是柳昭言。
他总觉得自己老,也为了防止被旁人窥得自己的身份,整日顶着张二十岁的面皮在我面前扮嫩装年轻。
世人都以为柳昭言死了。
他虽在最后收手,可他同齐人相谋是真,豢养死士亦是真,皇帝自然忌惮他,就算他没假死,皇帝自然也不会让他活。
柳昭言索性便自导自演了一场戏,死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所有人尽数骗过去。
然而他到底待自己甚狠,心口那处利器伤与旧年所受箭伤本就在同一处,堪堪擦过心脏,但凡偏上一分,抑或是伤处过重他没挨得过来,他便只能是埋在地底的一具尸骨。
他怕自己当真死了,因而之前从未给我希望,他将话说得甚绝,亦让我知道了他的必死之心。
他将自己死后之事全都安排好了,却一直未让我知情。
直到我深更半夜路过灵堂看到从棺椁里爬出来,面色苍白,正同我笑着的柳昭言时,我以为他诈尸了,浑浑噩噩地让他带我一起走时,他才说出了一切的谋划。
他本就起了反心,也从来不把天命皇权当回事,他想不留余地地毁了一切后去死,可我说喜欢他,还硬迫着嫁给了他。
他旧年疼我珍视我,在我长大后又因我的纠缠复又生出那么一丝不可为外人所道的情意。
柳昭言纠结了一番后,便也不想去死了,他想试试为我活上一次。
于是他假死后改换了身份,收敛了所有弑杀之心,亦戴上了人皮面具彻底成了另一个人,就为了年年岁岁伴着我。
如今我好好养着他,掏空我爹的家底给他买上百八十副人皮面具自也不是什么难事。
柳昭言啊,一向好养活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