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大師班「國族史詩與心靈奇跡」在京舉行。本屆北影節「天壇獎」評委會主席、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裏卡作為主講嘉賓,同中國導演黃建新、作家余華展開對談。
1954年出生在南斯拉夫薩拉熱窩的庫斯圖裏卡,今年就將年滿70歲。作為前南地區的演員、編劇和導演,他在中國觀眾熟知的電影【華瑟保衛薩拉熱窩】中曾客串過遊擊隊員而初登大銀幕。上世紀80年代後,他正式拿起導筒,先後拍出了【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爸爸出差時】【格拉斯哥流浪之歌】【亞利桑那之夢】【地下】等多部膾炙人口的影壇佳作,令他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斬獲頗豐,成就了「全世界最會得獎的電影導演」之名。
「人是如何感受歷史中那些巨大災難的呢?又是怎樣度過那些災難的呢?無論是在災難前還是在災難後,遺忘始終居於統治地位。」恰如庫斯圖裏卡在個人自傳【我身在歷史何處】中所說,他總是用影像講述著一個失去的國度,一段無法重溫的鄉愁,以及那個在歷史長河中被迫止步不前的南斯拉夫。對談開始前,一段混剪的影片為現場觀眾撿拾起過往他在電影創作中「絕不向遺忘屈服」的努力與掙紮,初心和抗爭。

庫斯圖裏卡
「電影一定能夠引來一群誌同道合的人走進影院」
「【地下】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庫斯圖裏卡導演的作品。」黃建新導演在發言時回憶說,「當時是一位朋友向我推薦的,說電影的風格太獨特了。那時找不到資源,不知是從誰那裏借到了錄像帶,我連夜看完,呆坐在沙發上長久沒動地方,帶給我的沖擊太大了。」
「電影講述了在大時代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從被占領到解體、分裂,把民族心靈史同一對兄弟間的故事結合在一起。庫斯圖裏卡導演用一種自由的暢想,塑造了一眾狂放不羈的藝術形象。現在我們說他的手法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恰在那段時期,我的一些影片也采用了非寫實主義、表現主義的方法。而且由於歷史原因,導演看待他的國家的歷史,同中國的歷史間也有一些關系,在意識形態上存在一些關聯和反思。所以看【地下】,包括之後看【爸爸出差時】都會讓我作為中國觀眾產生很多聯想,可以說他的電影超越了文學、超越了藝術,帶給我們更多在人類意義上廣泛的想象。」黃建新說。

余華
余華在介紹自己對導演片單的閱片史時,親切地將庫斯圖裏卡稱為「老庫」。「我看老庫的第一部電影是【爸爸出差時】,是在一位中國導演的家裏,他從國外帶回的英文字幕錄像帶。我聽不懂裏面的台詞,卻看懂了。因為我和黃建新一樣,都經歷過那個特殊時代,所以不需要轉譯也能看懂電影的故事。【地下】我是用VCD碟片看的,【格拉斯哥流浪之歌】在從網上下載的,只要能找到片源,老庫的電影我基本上都看過。」
「今天大師班的題目‘國族史詩與心靈奇跡’,起得特別好。老庫的電影中呈現的南斯拉夫,劇情中人物的經歷,那種國族創痛感並不是當下中國人可以體會到的。其次他的電影可以說展現的就是心靈奇跡,那種天馬行空、不拘一格著實令人震撼。」余華說。
庫斯圖裏卡表示自己的電影創作,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1981年,我拍了個人第一部劇情長片【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當時南斯拉夫還是一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整體。電影展現了我們在特殊經歷下的一段傷痛的回憶,也反映出當時社會出現的新的情態。」

【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劇照
「對於南斯拉夫來說,在戰亂之前它還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非常不幸的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它的內外沖突都特別尖銳。作為電影工作者,我是幸運的,那段經歷給了我創作的靈感,但我們的人民則大多沒有這份幸運。」庫斯圖裏卡表示直到上個世紀末,歷史的創痛也不曾在自己的心靈中減輕。「但與此同時,人們在苦中作樂產生出的幽默感也影響了我的創作。我也希望可以借由這樣時代背景的展現,更好地把個人的家國情懷放入電影,比如我從小怎麽長大,我的求學經驗,我的價值觀等等一路成長的過程和經歷。」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怎樣用電影更好地參與到這樣的世界當中,把我們的故事放到大銀幕上,讓其他國家的觀眾也能夠產生情感上的共鳴。電影帶給我們的經驗就是如此,它一定能夠引來一群誌同道合的人走進電影院,並且去相信電影中呈現的東西並不過時。我不過是用藝術的形式,把更多的魔幻現實主義和超現實的東西融入進去,讓大家理解人們遭受到的苦難,無論是身體上還是心靈上的。」庫斯圖裏卡說。
「我特別同意庫斯圖裏卡導演的觀點,你所經歷的一切事情一定會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跡。當你真誠地去反映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的想象力、你的表達方式自然而然也就產生了。對藝術家而言,這是非常寶貴的經歷。總的來說,誰也逃不掉歷史對他的影響。每個導演會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偏好,但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關註的不是一個單一的靈魂,我們看到的、表現的其實是一個真實的、多級的、豐富的靈魂,來自那樣的人,那樣的群體。如此,我們的影片也好,小說也罷才會有比較長時間的價值,才有它的生命力。」黃建新說。

對話現場
「1994年,陳凱歌拍了【霸王別姬】,張藝謀拍了【活著】,我拍了【背靠背,臉對臉】,三部電影都來源自小說。其實我的前六部電影,五部都是源於小說。我一直認為在中國,作家比電影人在觀察人性、塑造人物方面要強,他們在寫作時可以進入一種冥想狀態,而電影則是現場集體創作,作家更能觸摸到社會的脈動和本質。」黃建新表示,電影人的創作一定會同他的人生經歷有關,「當我可以拍戲的時候,我就特別關註普通人的遭遇。評論界曾把我的電影視作先鋒,後來我去澳洲做存取學者,看了很多紀錄片,回國後我的電影開始向寫實主義轉向,想記錄下中國改革初期的變化。【紅燈停,綠燈行】(又名【打左燈,向右轉】)中的主場景就是我小時候成長的院子,拍完後一個月那個院子就拆掉了,我把它保留在了電影中。」
「老庫心裏住著兩個靈魂」
相較於黃建新導演的條分縷析,作家余華的發言則顯得隨意家常。「我和老庫小時候都是‘壞孩子’,小時候想幹什麽幹什麽,我讀書時的教室就像個菜市場。老庫在【我身在歷史何處】中也寫到,當年的玩伴都進了監獄,他要是不拍電影,肯定也進去了。所以是藝術和電影救了庫斯圖裏卡,把他變成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老庫現在住在貝爾格萊德,但他成長、上學都是在薩拉熱窩,我去過薩拉熱窩,專門去看了他從小長大的街區。站在路邊,我就想,這哥們小時候幹過的壞事一定跟街上來來往往的車輛一樣多,所以我特別推薦大家去看看他的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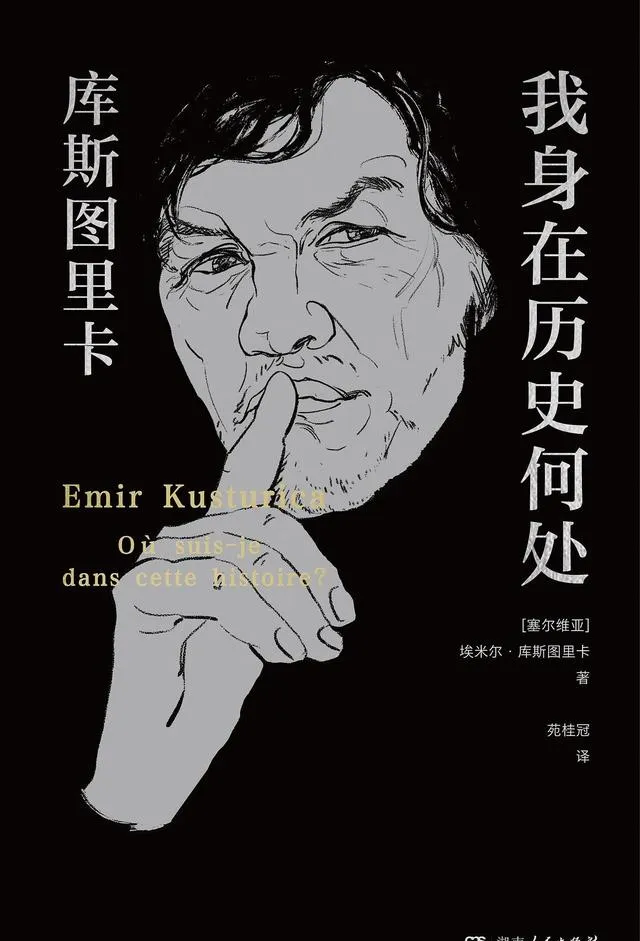
【我身在歷史何處】書影
余華還饒有興趣地回憶了他和「老庫」的第一次見面,是在貝爾格萊德薩瓦河畔的一個公園。「我們在那吃了晚飯後,他就告訴我說,走,帶你去看看我拍【地下】的靈感是從哪來的。我註意到他的鞋帶沒系好,還提醒他,他嗯了一句,然後繼續走路,後來我發現不系好鞋帶是他的一個習慣。他把我領到了一處下沈的遺址,裏面有一個小門。當時燈光是照在下面的,周遭一片黑咕隆咚。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為什麽那麽多人有過他類似的經歷,卻只有他可以拍出【地下】,是歷史選擇了庫斯圖裏卡看中了那個小門。」
【爸爸出差時】劇照
「在我看來,老庫心裏住著兩個靈魂,一個是莎士比亞靈魂,一個是契訶夫的靈魂,這兩個靈魂有時候是分開的,有時候又合在一起。比如說他拍【爸爸出差時】時,是契訶夫式的靈魂(在主導);但是你看【地下】的時候,會感覺到他那莎士比亞式的靈魂蹦出來了,那種放肆、那種開放、那種為所欲為、天馬行空,所有這些都出來了。到了【格拉斯哥流浪之歌】,你又感覺他那兩個靈魂又合在了一起。所以他是這樣的導演,他的作品是他的靈魂碰到了什麽,然後他就去創作什麽,反而跟時間的關系不是那麽緊密,包括他後來風格的轉變其實也跟時間的關系不大。」余華說。

【格拉斯哥流浪之歌】劇照
余華的發言讓庫斯圖裏卡莞爾一笑,「大家現在看我的鞋子,鞋帶就沒有系上,為什麽沒系?因為我現在心情特別平糊,如果我在街頭受到威脅,有人要打我,我就會系緊鞋帶,隨時準備逃跑。」
「說到小時候的頑劣,其實我出生在一個家境不錯的家庭,但我周圍的人家有單親家庭,有的家庭比較貧困,有的家庭裏還有罪犯。在我的記憶裏,我一直想尋找他們那種家庭的存在感,而且我也一直在尋找這種力量。在我的電影中有不少街上的人、格拉斯哥流浪,他們也見證了社會的變遷。作為一名導演,你要能夠看到社會上到底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並且能夠把現實剝離出來。」
「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也有一些關鍵元素,就是他到底要展現什麽,要隱藏什麽,這在一部好的電影裏面也是一樣。同時,人性也是復雜的,並不是像陰陽兩極的對立一樣,不是非黑即白。作為電影人,我們要透過藝術的形式找到人性的脆弱,去探究人性深層次的內涵到底是什麽。」
「我的電影創作開啟於半個世紀前,這期間我活了下來,成了藝術家。我來自南斯拉夫,也見證了柏林墻的倒塌,我希望能夠用電影鏡頭,來展現時代和家國的變遷。同時,我也看到了社會的很多變化,在我看來,未來並不是暗淡的,我們必須要適應社會的變化,才可能去預見未來、暢想未來。」庫斯圖裏卡還特別提及,自己想在中國創作一部電影,「片名叫做【成吉思汗的白雲】。」
【成吉思汗的白雲】書影
「這個劇本老庫已經準備好多年了,改編自艾特瑪托夫(吉爾吉斯作家)的同名小說。我讀了劇本後覺得寫得好極了。」余華補充道,「在成吉思汗那麽強悍一個大人物身上,老庫卻想從他人性的某一種脆弱的角度切入進去,這有點像當年他帶我去看創作電影【地下】時靈感的出處,那個小門一樣。我覺得越是強悍的人物,他最脆弱的一面才是他人性中最打動人的地方。期待這部電影能早日在中國開拍。」

【地下】劇照
大師班上,庫斯圖裏卡還介紹了自己拍攝電影的經驗。「對於挑選演員,還是要找到他人性或者是性格的一面。有時候作為導演也可以從演員的性格中進行想象,觀眾已經記住了某位演員的臉孔,但我卻覺得是不是可以為他塑造其他的形象讓你記不住他的臉呢?我在選角的時候往往會做一些視覺上的創意工作。」
「在拍攝的時候,比如拍河邊、草地上的場景,我會坐在那,拿一杯咖啡靜靜地看他們的表演。如果演員有些緊張,我會試圖同他一起放松下來,他要是還放松不下來,我就會建議,幹脆我們一起跳到河裏怎麽樣。拍攝【爸爸出差時】時,裏面飾演爸爸和爺爺的演員都是群眾演員,並沒有什麽表演經驗,我就讓他們更多地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呈現。」
「作為導演,我們其實也是轉譯,把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轉譯成荒誕和懷疑的電影語言和電影故事。電影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現在還有一個趨勢是人人都可以拍電影,但我認為電影制作依然是要有一顆匠心。電影是一個非常具象的存在,我們透過在大銀幕上講電影的手段,來跟時代產生共鳴或者產生連線。」庫斯圖裏卡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