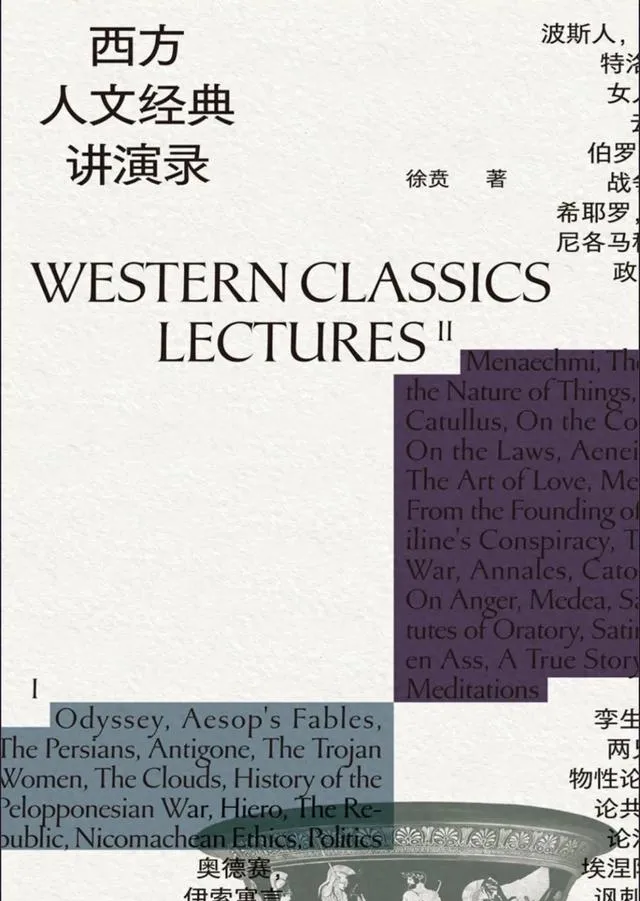
1、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創作的一部重要歷史著作,記錄了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間雅典與斯巴達及其各自盟友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與希路多德的【歷史】不同,修昔底德采用了更加嚴謹和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因此被視為現代歷史學的奠基人之一。

2、修昔底德出生於富有的貴族家庭,35歲就擔任希臘軍隊的將軍,由於一次征戰失敗,被雅典的公民議會判處流放,直到戰爭結束。流放期間他四處旅行,收集材料,從事他的歷史寫作。修昔底德去世是在戰爭結束後第四年,此前他似乎一直在寫這部著作。他去世後,遺稿被編輯為八卷,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3、修昔底德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目的是講述這場戰爭,而不是寫一部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關於這場戰爭的「歷史」。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歷史」是歷史學的產物,「歷史學」是一種對人類自身史料進行篩選和組合的知識形式,不僅是史實本身,而且註重對史實事件的起因與後果的分析、評價。這樣的歷史學在古希臘時代是不存在的。
4、戰前的斯巴達內部辯論,辯論雙方都訴諸「愛國」這個基本價值,盡管斯巴達國王發言較長,主張和分析都顯得相當理性,以勸說斯巴達人從長計議,謹慎行事;但還是不如主戰的監察官,幾句口號式的、不到國王的七分之一的簡短發言更能打動聽眾。
5、這樣的辯論場景在今天能夠給我們很大的聯想空間,讓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象,這似乎是一場顯示愛國主義的辯論。反抗雅典,這是斯巴達人最容易表現也最容易接受的愛國主義情感。在這種公開表決的場合,就算有普通人同意國王暫不宣戰的說法,他們也不太可能像國王那樣公開說出來。
6、修昔底德讓我們看到,這種和說話的人的身份有關的「愛國情感」或脅迫性「愛國」,其實古代就已經有了。國王勸斯巴達人三思而後行,沒有人會懷疑他「懦怯」或「不愛國」,但一個普通民眾就不同了。因此,普通人會更傾向於在公開表態時做出「勇敢」和「愛國」的表示。而且由於是公開表態,「愛國」會變成「超級愛國」。
7、在修昔底德那裏,斯巴達不是一個傲慢或窮兵黷武的城邦,而是一個因為雅典的崛起而感受到威脅的正常城邦。修昔底德更多的是從雅典和斯巴達人的不同性格來解釋他們之間的沖突:這兩個民族的性格截然相反,一個敏捷、好冒險,另一個膽小、遲緩。所以他認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8、今天,大多數現代歷史學家都這樣解釋修昔底德本人對此事的觀點:第一,斯巴達人懼怕雅典日益增長的勢力;第二,戰爭是強加到斯巴達人身上的,不是因為雅典人首先攻擊斯巴達人,而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就有了現實的戰爭危險。這就是人們今天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
9、「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說法是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創造的,但事實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本身無法支撐艾利森的說法。因為仔細閱讀第一卷可以發現,修昔底德並沒有把伯羅奔尼撒戰爭描述為不可避免的。他認為,相對能力的變化充其量只是戰爭的間接原因,絕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10、在斯巴達內部確實有「戰爭派」和「和平派」的分歧,然而,「戰爭派」並不害怕雅典,他們有信心發動一場速戰速勝的行動;而「和平派」則尋求通融,因為他們對雅典的實力有準確的評估,並擔心他們發動的任何戰爭有可能被他們的兒輩繼承下來。斯巴達人參戰主要是為了維護他們在希臘的榮譽和地位,而這一地位受到雅典帶頭進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革的威脅。
11、換句話說,斯巴達對雅典開戰,不是為了權力或意識形態的爭霸權,而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戰爭並不是必然的,斯巴達人可以選擇要戰爭,也可以選擇不要戰爭,而「與其他事情一樣,戰爭是他們在危急的關鍵時刻做出誤判的結果」。他們沒有在戰爭的火星剛閃爍的時候撲滅它,而是「允許一個遙遠而無足輕重的定居點的內亂升級為雅典和斯巴達及其各自的盟友之間的全面沖突」。
12、修昔底德在書裏的觀點是相當清晰的:盡管有利益沖突和國民性格的不同,但戰爭並不是必然的,雙方領袖人物都有多次可以選擇不發起戰爭的機會,卻沒有把握好這樣的機會。如果說真的有什麽「陷阱」的話,那對於真正有智慧的政治領袖而言,也還是有不往陷阱裏跳的選擇,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13、科西拉內戰其實是雅典和斯巴達的代理人戰爭,革命的一方開始時力量較弱,因此尋求外來勢力的幫助,而另一方在外來勢力的幹預時失去力量的優勢,所以就求助於另一個外來勢力。如果說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中還有英雄,那麽屠殺自己人的內戰中是沒有英雄的。在修昔底德的描述中,我們看到,如果內戰有英雄,那麽連同室操戈或者匪徒內訌也會有英雄了。
14、修昔底德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革命暴力敗壞公共語言的思想家。他指出,由於辭句的意義被扭曲和改變,以前的好事現在變成了壞事,而以前的壞事現在成了好事,諸如:「瞻前顧後」變成了「畏縮不前」;「不擇手段」變成了「足智多謀」;「殘忍」變成了「勇敢」;「同情」變成了「懦弱」;「權術」變成了「智慧」。
15、這樣一來,事情便不再有本質的對錯或是非分別,任何事情,我去做就是對的,別人去做就是錯的。凡事都必須有敵對觀念,有敵我之分。凡是敵人贊成的,我都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就要擁護。任何壞事,任何陰謀詭計,只要是我去做,就是正當的對敵鬥爭手段。敵方的任何行為都必須朝最壞處去設想,都是陰謀詭計。這種敵對思維制造了各種各樣的陰謀論。
16、在黨派和敵我鬥爭思維的驅使下,殘忍、仇恨、暴力、不守信用、背信棄義都成為一個人在敵對鬥爭中必須具備的素質和能力。在這樣的敵對鬥爭中,越是善於運用欺詐手段,越是不遵守常規的道德習俗,就越能獲得成功和勝利。修昔底德指出,一個國家裏這種政治行為的敗壞,會變成國民品格的敗壞。
17、瘟疫是捕捉到人性本身最深處黑暗的一個時刻。因為瘟疫讓人們普遍感受到生命的短暫和無意義,因而陷入一種道德危機。人們有理由在輕松的快樂中尋求快速的滿足,以至於沒有人願意去做被認為是高尚的事情,因為他們認為在實作這個高尚目標之前,他們是否會死死是不確定的。無論是對神靈的敬畏還是對法律的敬畏,都沒有人退縮,因為人們認為無論他們是否崇拜神,都是一樣的滅亡。在瘟疫之前,人們的這些傾向一直處於休眠狀態,被對眾神的恐懼和人類的法律所壓制。
18、關於「強權即正義」。「強權」的普遍原則是,你不做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你對我不是絕對服從,就是絕對不服從。強權邏輯是,打你是因為你弱,只要你弱,沒有反抗的力量或手段,我就可以打擊你、壓迫你。強權邏輯是,希望要有希望的本錢,弱者連希望都不配。強權邏輯是,誰都是利字當頭,誰都不會做違背自己利益的事。所以,分化對手,各個擊破是最好的戰略。既然神和人一樣把實力看得比道義重要,那麽強權就是天經地義、就是理所當然的正義。
19、有兩種不同的雙重道德標準:第一種是,對外國似乎非常友善和平等,甚至慷慨解囊、無私地援助;但對自己的老百姓卻蠻不講理、百般盤剝;第二種是,對自己人很講道理也很有羞恥感,但卻能對外國人做出非正義之事而不感到羞恥。對自己的事情,他們互相之間要求基於正義的權威,但對外人,他們卻不在乎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