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本名周耀平,是一位傳奇人物,亦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他早年的職業生涯,曾與新華銀行有過一段難解之緣。他於1943年3月加入該行後,擔任過總行稽核處稽核等職務。1946年底至1948年初,周有光擔任新華銀行駐紐約的代表,並負責該行附屬企業新原公司在美國的營運。在晚年回憶錄中,他對此段經歷的記述非常簡略,個別地方還作了隱晦處理。筆者近日在查閱上海檔案館藏新華銀行檔案時,偶然發現了與此相關的一段塵封往事。

周有光
禍起蕭墻
新華銀行附屬企業新原公司於1944年初設立於成都,抗戰勝利後遷往上海,並於1946年10月完成增資改組,這期間該公司由周有光兼負其責,投資專案包括木材、食糧、 柴炭、駱駝牌香煙、布匹、電石等,自營部份則包括西北毛呢、食糖、紗布,以及汽車等。如果不計借款利息,新原公司總體效益還算不錯。
1946年底,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美國考察,接洽拓展業務,並籌設紐約新原公司。1947年4月間,周有光在紐約登記成立「新原公司」( Newland products Corp.),與僑商所辦的紐約原有貿易公司「中國貿易公司」(China Trade Inc.)合地辦公,辦事地點就設在紐約百老匯路。他在晚年回憶錄【逝年如水】中寫道:
新華銀行在紐約百老匯路原來就有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一直有人在照管。這個人是國民黨教育部次長的兒子。以前有個著名的數學家叫秦汾。秦汾的兒子在美國讀書,抗日戰爭期間他待在美國,沒有回國,所以新華銀行一直委托他照顧這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一直租著,沒有退約,新華銀行有事情,也托他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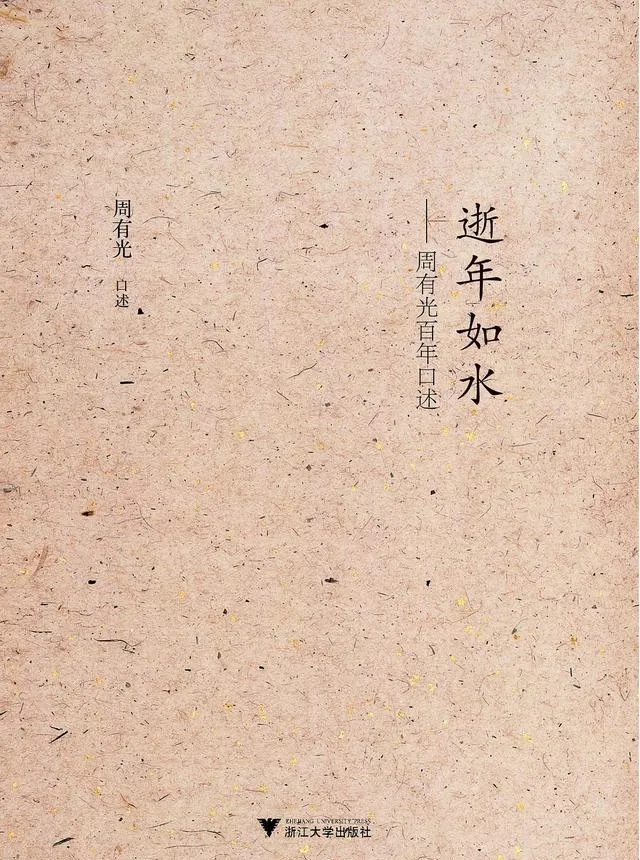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他的這段話非常拗口,「教育部次長」與「數學家秦汾」,實際是同一人,即秦汾,字景陽,上海嘉定人,北宋著名詞人秦觀(少遊)第十八世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曾任上海南洋公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後任教育部代次長、財政部常務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公路委員會主任等,抗戰勝利後任最高經濟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賠償委員會副主任;文中所提到的秦汾之子,系其長子秦寶同。值得註意的是,周有光在回憶錄中始終沒有點明秦寶同的真實姓名。時隔多年後,周有光依然如此隱晦,實際是與紐約新原公司涉及的一樁公案有關。
當年紐約新原公司成立後,周有光征得總行同意,邀請了他的中學老同學、中國貿易公司負責人章午雲,以及中國發動機公司負責人秦寶同擔任副經理。
秦寶同,1914年出生,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時兼任中國發動機公司協理兼業務部主任。
章午雲,名章植,字午雲,江蘇無錫人,1907年出生,常州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因學潮轉入復旦大學經濟系。1928年畢業時獲全校第一名金質獎章,留校任教。1931年著有【中國土地經濟學】,後加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任調查部主任。1939年作為陳光甫秘書,隨同赴美洽談「桐油借款」,後留美創辦中國貿易公司。

章午雲
當時,周有光因不擬在美久留,實際委托章、秦二人辦理該公司具體業務,並規定一切支付款項,由三人中二人會簽支領,如三人中有二人離去,則由中國貿易公司的會計主任Burke經律師證明後會簽款項。公司成立後在代收款中撥出美元貳萬五千元作為實收資本,「其後以上海經濟情形變化過速,實際無法聯系進出口事業,故僅辦若幹調查及計劃而已」。
紐約新原公司的資金來源比較特殊。早在抗戰時期,新華銀行曾委托新原總公司,在重慶向美國慎昌洋行訂購過一批卡車。抗戰勝利後,因慎昌洋行無法迅速交貨,周有光抵美後,上海新原公司與慎昌洋行議妥,分四次在美退還了一部份車款,交周有光代為收入紐約新原公司賬內,計美金124,609.24元。另有上海新原公司出售的一部份已到申之卡車款項,其中一部份亦陸續撥去紐約,並有上海客戶托代收之款項等,收付相抵後,結收美金14,950元。兩項共收美金139,559.42元,均存於紐約伊文銀行。
紐約新原公司「以各事委托他人代辦,約明不另支薪,須待以後業務開展,由業務中扣傭為酬」,從1947年初創辦,至1948年3月12日周有光離開美國時,共計一年三個月,該公司的最大一筆開支,就是周有光考察銀行所支之旅費,包括其這段時間旅費美金5000元,及赴歐考察旅費美金2000元。此外為公司器材、家具開支美金1,310.99元,零星開支如房租、水電等美金1,075.77元,以及歸還中國貿易公司墊付開支之美金2000元,共計美金11,386.76元,平均每月不足800元,「此為在美任何機構費用之最省者」。周有光離美赴歐考察時,以業務一時不易開展,又與中國貿易公司商量,此後一切開支除郵費外,均由該公司負擔,「是以開支幾等於無矣」。
周有光於1948年3月12日離美赴歐考察,至當年6月初返滬。當時上海新原總公司以國民黨政府管制外匯「嚴格而不合理」,遂通知紐約分公司將銀行結單暫勿寄滬,以免檢查麻煩。周有光返滬後,章午雲為欲使周有光明了紐約新原公司賬戶余額情況,寄來一份結單,周有光乃送交該行稽核處。稽核處根據周有光離美赴英時所寄抄賬表查核,發覺數目不符,短缺竟然達87500元美金,遂詢問周有光原因(按:事發時,1948年上半年,1美元大約可購買一克黃金,照目前1克550元人民幣推算,新原公司被挪用的87500美元,現在大約值人民幣五千萬)。周有光起初以為是章午雲或為業務必要而動支,乃即托人帶信及電稿至香港,請香港分行函電詢問。「其所以轉折詢問者,以當時滬美之間,格於禁令,已無法直接通訊談及外匯也。」後得港行轉來章午雲復電,「驚悉彼並未支款,經彼向銀行調查結果,獲悉系四月廿三日秦君所支」。也就是說,這筆款項是秦寶同動用的。
此外,周有光離美前,曾因留美僑商發起組織一個食品加工運銷組織,初步在美試辦食品加工,「以後將辦有經驗之加工方法,回國辦理推廣出口」。周有光頗為贊成,並經陳準總公司,參加合營資金兩萬元,交由秦寶同經辦,但這筆款項也被秦寶同挪用了。
以上兩筆,計共十萬七千五百元,均為秦寶同挪用。周有光說,「秦君在美頗為僑界推重,今竟如此,實非初料所及。」

周有光
先索後訴
周有光於1948年6月初返滬後不久,即被派往該行香港分行處理相關業務工作。不久,他接到老朋友一份秘密電報,告知辦完事情不要回上海。他後來才知道,因曾幫助一些共產黨朋友辦理香港上海之間的匯款,自己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他因此只能繼續待在香港,等待上海的解放。期間,就如何收回被秦寶同挪用的款項,周有光與章午雲始終保持著密切的溝通,往來信函亦均轉呈新華銀行總經理王誌莘閱洽。
1948年10月6日,章午雲約見秦寶同。秦承認,當年4月23日,其向伊文銀行支領了美金87500元,此支票系付與中國發動機公司,再由中國發動機公司存於另一家銀行的中國石油公司戶內。秦解釋說,當時以中國發動機公司急於歸還中國石油公司欠款,「遂出此下策」,原擬稍隔數日,即行設法歸還,不意中國發動機公司資金為銀行凍結,遂造成如此結果,當盡力設法歸還;「對於挪用之另兩萬元,則先由其個人歸償。」
對此,章午雲明確要求秦寶同直接向周有光說清事實原委。秦遂於10月7日、11月6日兩度親筆致函周有光。
10月7日,秦寶同致函周有光稱:「關於動用新原款八萬七千五百元事,同(即秦寶同)因一時糊塗,出此下策,同無以對先生及誌莘老伯對同之信任,更無顏對家中老父。此事發生以來,無日不在恐慌中。」並陳述了中國發動機廠正進行改組招股,但也有可能陷入被迫清算的境地等情形。
10月29日,周有光復函秦寶同指出:
公司之款並非弟(即周有光)或同事之私有,均為外界寄存於公司者,弟對之有法律上及道德上之責任,兄(即秦寶同)之所為,不僅損害吾兄之信譽,且將損及弟之信譽。現外界索款甚急,外界對弟逼緊,弟對吾兄不得不逼緊,此亦吾兄必能了解,望吾兄妥自籌劃補救之道,於最短期間彌補此事,以自全信譽,是為至要。
在這封信的結尾,周有光再次婉言相勸:
弟及吾兄之友好,均對吾兄期望頗深,此種可貴之友誼,系吾兄能加以珍視,吾兄事業現正肇啟初基,盼能自重自愛,勿自毀前途。逆耳忠言,幸采納焉。
11月6日,秦寶同再次致函周有光: 「自此事發生以來,無時無刻不在恐懼中」;如此事被揭發,「此後將信譽破產,無顏見人,不能再立足社會,只好聊此一生」。他也提出,「如能假以時日,當盡力設法,圖謀解決之道」。他稱正參與組織一家油輪公司,「如該公司日後賺錢,必須盡先提出一部份盈利,用於幫助中國發動機廠」。秦承諾,原計劃投資食品廠的資金兩萬元, 11月10日先償還一萬元,其余一萬在年底前償還。
秦寶同的這兩封信均由章午雲攝影後留存,以作重要證據。
1948年11月1日,王誌莘致函周有光:此事完全應由秦寶同負責,新原公司與中國發動機廠並無直接債權關系,「法律上即無從科以歸償責任,故只有盯住寶同,要其清理」;不過,但照目前情形,盯住他或訴諸法律,於實際恐亦無補救,只可勸以利害,「責成其從速設法清理,否則於其個人以後一生大有不利」。王誌莘的這一指示非常明確,即首先要設法向秦寶同本人曉之利害,盡力索追。
11月6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稱:
據弟觀察,彼目前無余力還出款項,大致系事實,故即送彼坐牢,亦未必能收回款項,其原因在中國發動機廠辦理之糟,幾成為一無底之洞;外人在美辦廠,本非易事,彼等初出學校,又無經驗,所接到之生意,本系苦事,因工作不慎,第一批退貨即吃虧十余萬元,向銀行借款竟出六厘錢,又欲虛張場面,不知節省開支,故外表講得怪好聽,內部一天到晚移花接木,糟而又糟,希望天外能飛來一筆好生意,渡過難關,跡近一個騙局,如此辦廠,等於買跑馬票,如何得了。
在這封信中,章午雲提出,經與律師詳細討論,「秦君所為犯二個罪名,一為盜用公款,一為冒簽支票」;秦既答允在11月10日前歸還一萬元,當然看其能否履約,尚無法律解決之必要;法律解決系最後之辦法,可不訴諸法律,總以不用法律為妥,「法網開一面,與人以自新之途,亦為中國固有之精神,惟如不願自新,則只得以法律從事耳」。
從現存檔案史料看,章午雲的每封信函均篇幅不短,敘述周詳,並常常提出應對策略。對此,周有光給與了極高的評價:「吾兄代弟費神,實已超過一般友人之可能性,弟之感歆,決非言辭所能表達也」。
11月17日,周有光致章午雲:「寶同兄事件,不擬輕意提出訴訟,但須早日將訴訟手續準備妥帖」。並提出第一步應催促秦寶同將食品廠兩萬元歸還,「此事愈速愈妙」;第二步應要求秦寶同提出八萬余元分期歸還之保證,「如無確實辦法及保證,即考慮提訟」。周有光認為:「關於提出訴訟,最好不訴寶同,先訟銀行,支付冒簽支票,銀行有責任賠償。」他還特別強調:「寶同來信希望油輪公司幫助者,誠癡人說夢;油輪公司因包政府運油而得利,現政局有急轉之可能,油輪公司之業務頗有隨時終了危險。」
時間轉眼到了1949年,但追索工作的成效並不明顯。
1949年4月12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報告了中國發動機公司清理工作的相關情況,認為「此事夜長夢多,希望不佳」;同時 他認為,「以秦君少讀中國書,缺乏辦事上之道德觀念」,因此「費了許多口舌,只有一些效果」。
1949年6月初,上海解放後不久,周有光從香港回到上海。6月22日,周有光向新華銀行管理層送出了「秦寶同案報告書」,其要點為:(1)在艱苦不懈努力下,挪用的食品公司款項美金二萬元已還清;(2)最近中國發動機公司因周轉不靈而宣告清理,但「有無余款歸還新原,大成問題」;(3)建議不再繼續追索,而考慮改用訴訟辦法,「訴訟辦法之優點,在對於秦君有名譽關系,及今後能否繼續留美經營事業問題」。
周有光回到上海後,與章午雲之間的函電往來,均經過香港分行經理徐湛星中轉。
1949年8月12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提出:
據弟淺見,非用法律解決,難有較佳之效果,如訴之法律,不一定有較佳之效果,但至少有較佳效果之希望;因秦君等少讀中國書,既無中國舊道德觀念,亦無西方之宗教訓練,其平昔行為好利用他人錢財以圖自利,而不顧他人利益,累已成習,料想其必有若幹私蓄,但欲令其吐出,除用法律解決,實無其他途徑。
9月12日,章午雲再次致函周有光:「現在最要之點在秦君事應否法律解決,尚望早日決定。」
9月15日,公私合營新華銀行新董事會成立,周有光在其中擔任了董事,他同時還是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私人業務處副處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這種轉換,對周有光而言,不僅僅是職位的變化,同時也意味著責任的加重。秦寶同挪用的這筆款項,實際已成為人民的財產,必須要堅決追回。
9月21日,周有光在致本行各位同仁的信函中,將秦寶同私自挪用事件作了通報,並坦承:「此為本行一極不幸之事件,亦耀平(即周有光)所遭遇之一極不幸事件。」
9月25日上午,新華銀行假座上海麗都大戲院召開員工大會,歡迎新董事,慶祝新董事會成立。這次會議上,對於新華銀行解放前情況的審查結果作了報告,在報告人提到秦寶同拖欠新華銀行美金事件時,周有光董事起立講話,對於這一事件作了說明,並表示將繼續負責到底,一直到有了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他才卸責。「周董事誠懇負責的態度,得到了全體同人充分的同情與了解。」
10月10日,經新華銀行董事會研究後同意,王誌莘、周有光聯名致電香港分行經理徐湛星,請其即通知章午雲,向秦寶同及中國石油公司提起訴訟。

章劍慧、章午雲、章絳唐(後排)、章映芬、章央芬、章周芬(前排)兄妹六人1930年代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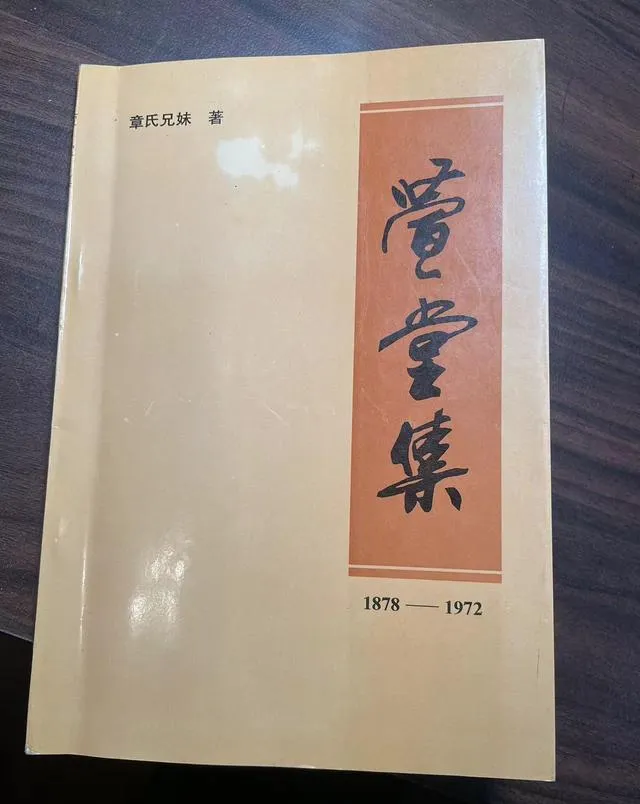
章氏六兄妹於1992年為紀念其母親秦萱逝世二十周年合編的【萱堂集】
「一鳥在手」
進入訴訟階段後,章午雲很快就有了新的重要發現。
1949年10月27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對中國發動機廠的清理情形,經專門托人查閱相關案卷,發現中國石油公司仍然為中國發動機廠之大債權人,數額為87500元。他認為,按秦寶同親筆函上的說明,此前已歸還同額欠款;中國石油公司既已收了新原公司87500元,則欠款業已取消,不應再參加清理。因此,「其串通舞弊之情節,甚為顯明」,此案非但為一民事案件,且為刑事案件;秦之盜用公款,固然不成問題,而中國石油公司負責人夏某亦犯有偽證罪。並告知已依法請求法庭,先行扣押了中國石油公司在化學銀行、大通銀行等處的存款10余萬美元。
法庭扣款後,控訴雙方曾有協商,但未達成共識,隨即進入訴訟程式,爭論焦點在於中國石油公司是否有免訴權問題。章午雲判斷,此問題最後決定之機構為美國外交部,而美外交部對這一問題極為審慎,不肯輕易給與,故中國石油公司欲請求免訴權,實際並不容易。「如對方不享受此項權利,彼之資產無法啟封,只有在法庭上打官司,我方理由充分,對方斷難勝訴。」
章午雲認為,此事開始訴訟以後,極易拖延時日,甚至可能需要五、六個月,「好在我方已扣到現金,將來可照算利息」。而且,此案一旦開庭,「中國石油公司之一切買賣,必須因我方之詰問,盡量宣布,其中難免有不可告人之處,對其聲譽極為不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解或許成為中國石油公司比較明智的選擇。
果不其然。1949年12月初,章午雲致電周有光稱:「秦寶同及中國石油公司現提議以立即付出三萬五千元,外加已付之五千元,以解決新原公司之訴訟;我方律師意見認為,免訴權問題須視政治因素而定,訴訟結果難於確定,故擬於和解為妥雲;上述條件能否接受,行方之最低希望如何,以便遵照進行接洽。」
12月15日,王誌莘、周有光聯名致電章午雲:「經商主管部門,以關公有財產,不便貿然和解,擬續追訴,倘機關獲免訴,擬再訴二人串騙罪。」此電的態度很明確,即不同意和解。
此後,章午雲數次來函來電,反復陳述了和解的必要性,其核心內容為:(1)如堅持進行訴訟,其風險在於中國石油公司是否能獲得免訴權,而此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關;(2)我方律師認為,如能在未請求免訴權以前,試行「和解」,在我方最為有利,如能收回五萬元,應可作一結束。章午雲認為,西諺之「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確系經驗之談;「且萬一美府改變政策,我方有完全失去優勢之可能,故以和解為上策」。
章午雲力爭「和解」的這些相關函電,王誌莘、周有光陸續轉送給了新華銀行各位董事、經理閱洽,並提到「港行經理徐湛星對美國法律情形熟悉亦建議和解」,建議「慎重應付」。可以看出,王周二人,實際傾向於章午雲的「和解」意見。
超乎常規的是, 12月30日,章午雲未經香港分行中轉,而直接致電新華銀行總行:「速將和解條件電復,我個人意見認為以五萬現款和解,余額由寶同出立五年至十年期票,但此僅供參考,請自決定條件電示。」
12月31日,王誌莘、周有光致電章午雲:「經董事會考慮認為,如能扣款,徐圖合理解決最佳,否則盼在六、七萬之間和解;可否另再要求對方在發動機廠歸還對方款項中,盡先補足我方余數?」此電表明,管理層已同意進行和解,不過對金額的判斷上有所差距。
1950年1月11日,王誌莘、周有光致電章午雲:「如處理上有實際困難,請斟酌當時當地情況,代為決定,十二月卅日直接來電不另復。」 此電表明,新華銀行管理層給了章午雲更大的授權。
2月1日,章午雲致電王誌莘:「關於新原事,此間資委會代表又來調解,擬共付四萬五千元了結,包括已付五千元在內,有關各方面之責任,連對中國發動機廠之主張,一並解除。我方律師仔細研究後,因前電所述明之免訴權一點無把握,雖覺如此解決,損失過巨,仍勸接受此項辦法;除非冒對我不利之危險,深以不能得更好解決辦法為憾。」顯然,這已經是章午雲認為的最佳結果了。
2月25日、26日,正在香港出差的周有光,先後致電在北京公幹的王誌莘總經理,以及留守上海的孫瑞璜副總經理:「覺目下國際情況下,以請雲兄全權酌決為要。」
2月27日,孫瑞璜急電王誌莘:「經商謝董事長,正在考慮,希征總經理意見,並盼就近商陳穆處長,請速復,俾商謝後電港」。電文中的謝董事長,即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副行長兼新華銀行董事長謝壽天,此時在上海;陳穆,即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處長兼人民銀行華東區行行長,此時也在北京公幹。
3月1日,王誌莘復電孫瑞璜:「新原事,陳穆處長同意照章電辦理。」
3月4日,孫瑞璜急電在港的徐湛星、周有光:「新原事董(事)會同意請雲兄全權酌決。」
此案最終於當年4月底了結,合計收回45000元,扣除律師費、扣押費後,「實收為四萬元之譜」;調解合約中尚有一附帶條文,規定中國發動機廠債權方面如收到款項在美金四萬五千元以上,仍應歸還我方。
3月6日,周有光致函新華銀行謝壽天等各位董事認為,此事的解決,采取了現實主義之辦法,「一鳥在手,勝過二鳥在林」;「如欲繩寶同以法,可待中美復交後,引渡寶同回國,在中國法庭前再加審判。」
此案前後經歷了三個年頭,實際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從中,或可觀察到周有光的擔當與睿智,章午雲的執著與細致,更可感受到的是他們身後人民政府新政權的強大力量。

周有光與夫人張允和

周有光與夫人張允和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