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5日,晚上十一時許,一輪明月高掛在天空,一個神秘的男子悄悄出現在位於蘇州市東橋鎮境內的西塔庵門口。
他並沒有到庵裏去,而是來到庵西邊的一棵老松樹下面停住腳步,把肩膀靠在樹上,眼睛向庵後面的小路不停地張望,好像在等什麽人到來。
停了幾分鐘之後,這名神秘男子又悄悄走入尼姑庵,在門後蹲了下來。
此人名叫湯文伯,當年34歲,是蘇西區武工隊東橋武工小組成員。

看到此,你一定會提出一個疑問,是不是搞錯了,武工隊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產物,1946年已經進入解放戰爭,怎麽還會有武工隊?
解放戰爭時期武工隊員真實照片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解放戰爭時期也有武工隊,不過跟抗日戰爭時期的武工隊使命不同。
抗戰時期的武工隊,活動在敵後抗日根據地,主要任務是抓漢奸,殺日軍;解放戰爭時期的武裝工作隊,主要活動在即將解放的國民黨統治區,或者剛剛解放的地方,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清匪反霸,以及建立人民政權,實行民主改革等。
無論什麽時期的武工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成員都是百裏挑一的精英,對黨無比忠誠,還身懷絕技,腦子反應要快,精明幹練,綜合素質高。
沒有兩下子,是當不了武工隊員的。
這天晚上,湯文伯是奉武工隊長周誌敏的命令,來這裏和交通員接頭的。
周誌敏原名許培貴,是吳縣光福人,1921年出生,他在哥哥許培榮的進步思想影響下立誌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事業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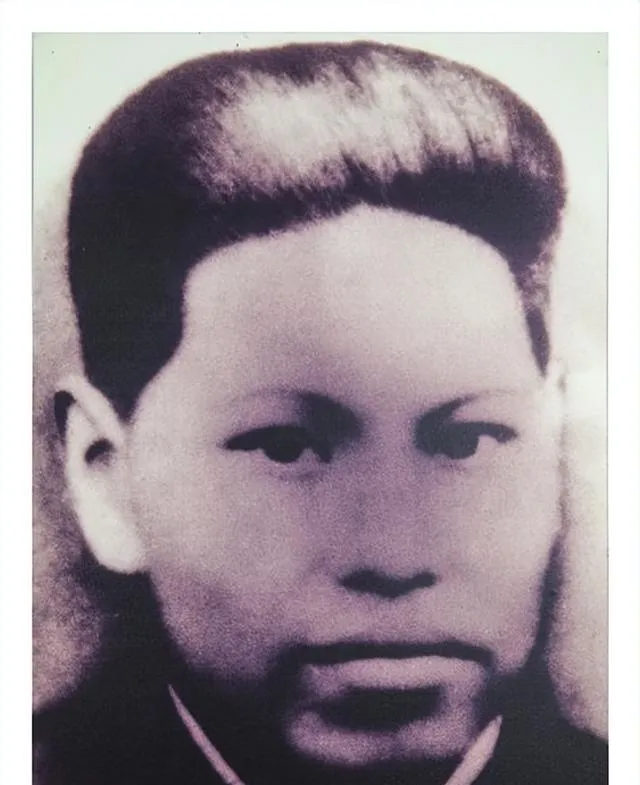
1941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
兩年之後,他公開了身份,正式參加了新四軍,堅持太湖敵後的抗日遊擊戰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新四軍全部北撤,周誌敏則留了下來,擔任中共蘇西區武工隊隊長戰鬥在太湖一帶,帶領武工隊機智勇敢地打擊蔣軍和一切反動派。
湯文伯原名許培文,跟周誌敏是老鄉,二人還是堂兄弟,他出生於1923年,家境優越,高中文化程度。
在學校的時候,許培文就接觸了不少進步書刊,參加學生運動。
抗戰爆發後,許培文也跟著堂兄許培貴參加地下工作,化名湯文伯。
現在的湯文伯,在半夜三更來到這裏,是要等待一個人此人名叫陸阿夯。
陸阿夯家住東橋湯埂村,出生於1904年,他1938年就入黨了,也算是一名老黨員。
但是因為他沒有上過學,是個文盲,而且還有七十歲老娘,組織上就讓他一直在本地堅持工作,主要任務就是傳送情報。

陸阿夯的哥哥,也是一名黨員,在土地革命時期死於國民黨反動派之手。
他的父親,則在抗戰時期,被國民黨頑軍士兵殺害。
可以說,陸阿夯跟國民黨反動派有不共戴天之仇,革命立場堅定。
而且,他辦事非常細心,送情報幾年了,沒有出過一次差錯。
每月一號、十五號和月底,陸阿夯都會準時在晚上十一時左右,出現在土山灣處和武工隊小組聯系、傳遞情報。
如今又到了傳遞情報的日子,武工隊員湯文伯早早就來到尼姑庵,在門後耐心等待。
可是左等右等,等了好一會,也不見他到來。
湯文伯有點著急,他走出尼姑庵,來到空曠地帶,拿出懷表借著月光湊近眼前察看,時針已經指向了11時24分。

過了約定時間快半個小時了,還是不見陸阿夯的身影,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西塔庵原來拄著幾個尼姑,抗日戰爭爆發後,這裏的尼姑因為掩護新四軍傷員全部被日本鬼子扒光了衣服,吊在院裏大樹上拷打。
最後,她們全部被殺害,投進院裏的枯井之中。
從那之後,尼姑庵就成為一座荒廢的空庵,沒有人再到這裏來,因為傳說尼姑被害之後,這裏半夜三更總有人哭,說是在鬧鬼。
別說是晚上,就是白天,也沒有人敢上這裏來,唯恐沾上晦氣。
按照原來的約定,接頭人應該提前到庵子內去,故意把後門關上(其實平時這扇門是開著的)。
而送信人陸阿夯到來後,會走到庵子的後門,輕輕敲門。
敲門的聲音必須是有規律的,是「當——當當」一長兩短,一共敲擊兩遍。
聽到暗號無誤後,湯文伯才會開門與對方相見,開始接收情報。
今晚,湯文伯按照約定,提前來到,但是卻始終沒有等到陸阿夯。陸阿夯做事踏踏實實,嚴謹守時,今天的遲到罕見,這讓湯文伯很自然警覺起來,心跳也加快了,腦子裏開始胡思亂想。

他在想,陸阿夯為何遲到?
是老娘健康出了問題,還是他本人身體欠佳?是半路上崴腳了?還是遇到了敵人,暴露了?
總之,他希望不是最後一種情況;如果是這樣,他在這裏就不安全了,危險已經迫在眉睫。
想到這裏,湯文伯的心提了起來,他趕緊起身,悄悄結束了西塔庵,躲在了庵子外面的一棵大松樹後,屏住呼吸,暗中觀察著周圍的情況。
秋夜寒涼,四周一片寂靜,除了蟲兒的低鳴,沒有別的聲響。
偶爾會傳來一兩聲貓頭鷹的叫聲,為寂靜的夜增添了幾分恐怖,讓人毛骨悚然。
湯文伯在樹下觀察了十幾分鐘,一切如常,沒有什麽動靜。
這時候,天空變得陰沈,一朵烏雲不知道什麽時候飄過了,將一輪明月遮擋得嚴嚴實實,大地更加昏暗,不遠處的庵子被黑暗吞沒,連輪廓也變得模糊起來。
突然,一陣敲門聲傳來:「當——當當,當——當當」。
這聲音在寂靜的夜裏,顯得非常清晰。

敲門聲是那麽的熟悉,跟往常約定的暗號分毫不差,湯文伯驚喜交加,他站直了身子,向發出響聲的後門觀察。
可是由於光線太差,什麽也看不清。
湯文伯用右手摸了一下胸口,然後長長地舒了口氣,隨後邁著堅定的步伐,摸索著緩緩地向著庵子後門走去。
可是,就在他剛走了五六米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黑暗之中,忽然響起了「刺啦」一聲,那是劃火柴的聲音。
聲音響過之後,前面亮起了暗紅色的火光,這光點很小,就像指甲蓋一樣。
但是,在這無邊的黑暗中,顯得分外刺眼。
這讓湯文伯的心又懸了起來,覺得有點不對勁。
大家是在做地下工作,處處都要小心,之前街頭的時候,是不允許劃火柴的,陸阿夯是輕車熟路,也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

今天,他突然劃火柴,出於什麽目的,就不怕暴露?
盡管這樣想,湯文伯也沒有停住腳步,繼續摸索著向前走。
又走了幾步,火滅了。
可是停了一會,又是「刺啦」一聲,火柴再次劃響,那裏又閃起亮光。
這時候,空中飄來一股淡淡的氣味,味道很熟悉,「似曾相識」,湯文伯努力辨別了一下,終於想起了,那是煙葉燃燒的味道。
他隨即得出結論:來接頭的陸阿夯因為是沒有找到人,只好蹲在門口抽煙。
無論怎麽說,終於等到了,湯文伯興奮不已,他不由得邁開腳步,加快速度,打算上前跟陸阿夯說話。
可是剛走了沒有幾步,他突然感到了不對頭,在他的記憶中,陸阿夯是不抽煙的。
記得一個月前,我軍剛跟蔣軍打了一仗,繳獲了不少戰利品,其中就有香煙。

湯文伯專門拿了兩包香煙,在接頭的時候,他拿了出來,遞給陸阿夯:「老陸啊,我專門給你帶了點小禮物。」
他滿以為,對方會高高興興接住。
誰知道,陸阿夯看到之後連連擺手。
「你不抽煙?」湯文伯有點好奇,在當地,男的大多都抽煙。
「我不是不抽煙,我不敢抽,老婆不能聞煙味,我要是抽煙就不讓我上床。」陸阿夯有點難為情地說。
「你還怕老婆?」
「不怕你笑話,因為我長得醜,30歲上才娶媳婦,對方比我小14歲,長得還很好看,我把她看得比命都重。」陸阿夯撓撓頭,不好意思地說。
一想到這一幕,湯文伯當即停下了腳步,眼前這個人肯定不是陸阿夯。
而情報站都是單線聯系,不許找人替代;這就是說,陸阿夯出事了,來人很可能是敵人。

如果是敵人,肯定不是一個,很可能敵人已經設下埋伏。
一想到這,湯文布頓時緊張起來,脊背一陣陣發冷。
他決定快速離開,以免落入敵手。
但是他沒走兩步,又猶豫起來:萬一陸阿夯不舒服,臨時找人來替代,如果離開,那不就錯過接收情報的良機了?
可萬一要是敵人呢,自己不就完了?
這樣一想,湯文伯猶豫起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陷入兩難境地。就在這時候,那人有人說話了:「劉班長,裏面怎麽沒人,該不是對方發覺了吧?」
顯然,來者不是一個人。
「別急嘛,周副班長;那個姓陸的老婆孩子在我們手裏,諒他不敢耍我們。」這時候,那個被稱為劉哥的人說話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再等一會,那家夥肯定會來的!」

聽了這話,湯文布頓時猛醒,陸阿夯八成是叛變了。
此人對黨忠心不二,但是他說過很在乎自己的女人,很可能他暴露之後,敵人抓住這個軟肋,逼他招供了。
湯文伯不敢怠慢,立即掉頭向西走去,一邊走一邊暗自慶幸:幸虧我反應快,否則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正這樣想著,湯文伯突然一腳踩空,滑了一跤,倒下的時候身體碰到了樹枝,發出聲響。
聲音驚動了敵人,姓周的敵人突然喊道:「劉哥,前面好像有人,快去追!」
聽到喊聲,湯文伯不敢猶豫,他一個鯉魚打挺站了起來,邁開雙腿大步流星往前走。
有人說,怎麽不跑啊。
黑燈瞎火的,不能跑,碰到障礙物可就糟了。
而敵人卻敢跑,因為他們帶有手電。

這一來,雙方的距離很快縮短,不到一百米,甚至都能聽到對方的喘氣聲,眼看湯文伯就要被敵人追上。
他想, 我不能再順著道路走了,不然被抓住是板上釘釘的事,必須下路。
這樣想著,湯文伯來一個急轉彎,鉆到路邊的樹叢中。
身後的敵人隨即趕到,但是卻失去了目標。
「劉班長,人怎麽不見了?」
「周老弟,可能是鉆樹叢裏了吧。」
「我們也進去吧,劉班長?」
「笨蛋,對方很可能帶槍了,我們進去不是成活靶了?」
「我怎麽把這給忘了?」姓周的拍著腦袋說,「那就讓他跑了,回去如何交差?」
「我說你咋就這麽笨呢,我們就說那家夥根本就沒來,姓陳的是在撒謊。」姓劉的班長到底是個老兵油子,腦殼靈活,他回頭對士兵們說,「你們聽好了,回去就說沒看到共產黨接頭,誰要亂講老子斃了他!」

聽他一說,士兵們齊聲答應。
「劉哥,我還是想立功,要不我們就在前面路口潛伏下來,等他到了來個猛虎撲食……」周副班長說。
「那好,正抓不住,我們回去就說沒見,不能亂說啊。」劉班長說。
「知道了,劉哥。」姓周的答應道。
二人的對話,湯文伯聽得一清二楚,他心裏罵道:「老子聽見了,還會上當嗎?真是蠢豬。」
他趴在樹叢中一動不動,等了足有一個時辰。
「如果被敵人發現了的話,今天就跟他們拼了,反正不能當俘虜!」湯文伯趴在那裏大氣不敢出,心裏暗自思忖。

敵人在那裏等了半天,也沒有聽到什麽動靜。
「撤了吧,看來那接頭的早就跑了,說不定已經在床上呼呼睡覺了。」
「好!」姓周的班長說著,又對手下說,「弟兄們,記住了,接頭的根本就沒來。」
「知道了,班長!」
很快,大路上響起了一陣齊刷刷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又等了一刻鐘,周圍沒有任何動靜,湯文伯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這才從樹叢中爬了出來,大踏步向我軍駐地走去。
事過三十年之後,湯文伯回憶起當年那驚怵一幕,依舊有點後怕:
「那天晚上,如果我反應慢的話,恐怕早當烈士了。」
來源:【蘇州新聞網】2023年——【周誌敏烈士的「戰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