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馬拉·哈裏斯的外交政策會與拜登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嗎?從她的國家安全顧問菲利普·哥頓的工作中可以找到線索。

卡馬拉·哈裏斯在2022年第九屆美洲峰會期間與國家安全顧問菲利普·H·哥頓交談。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拜登總統很喜歡說一句話,那就是美國正處於世界歷史的「拐點」,無論是在應對氣候變遷和種族不平等、保護烏克蘭和全球民主、引領中美關系新時代,還是恢復惠及中產階級的經濟方面。如果卡瑪拉·哈裏斯在11月擊敗當勞·特朗普,她將繼承這些轉折點,以及日益不合時宜且未經證實的外交政策。
哈裏斯主義是否只是拜登主義的延續?
哈裏斯現任國家安全顧問菲利普·H·哥頓有望在哈裏斯當選總統後繼續擔任這一職務。他的搭檔傑克·沙利文(在拜登擔任副總統時也曾擔任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改變了這一職位,其變革程度自亨利·基辛格以來無人能及。在沙利文任職期間,國家安全委員會進一步成為美國外交決策中最不具民主色彩但不可或缺的機構。據報道,他是烏克蘭政策、中美政策和美國工業政策的主要設計師。
哈裏斯對外交政策問題有著,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這是民主黨人爭論的焦點。但哥頓對哈裏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並可能在塑造她的政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就像蘇利文在拜登政府中一樣。已故美國前駐以色列大使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於2023年12月評論道:「鑒於哥頓對各方角色的深刻經驗和了解,哈裏斯非常依賴他的建議。」
哥頓的職業生涯以及他豐富的學術成就表明,他雖然身處華盛頓,卻深知其弊端:群體思維和缺乏自我反思。他最近出版的新書【輸掉長期博弈:中東政權更叠的虛假承諾】(2020) 記錄了美國在中東地區推翻領導人的努力。 這本書也是給決策者的一個寓言。 哥頓記錄了美國在推翻專制領導人時,長期誤判自身能力,肆意妄為,以良好的意願取代深思熟慮的戰略。 他寫道:「 美國關於中東的政策辯論存在一個謬誤,即美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即使數十年的痛苦經歷表明事實並非如此。而政權更叠是最糟糕的」解決方案"。」
鑒於哈裏斯的提名,【輸掉長期遊戲】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失敗政策的優秀歷史著作,它還揭示了哥頓如何影響哈裏斯的外交政策,特別是中東政策。一些人認為有理由保持謹慎樂觀,認為情況可能會好轉。美國外交政策本身是否正處於潛在的轉折點?
哥頓的職業生涯是獨特的,但並非異常,在許多方面反映了華盛頓早期外交政策制定的歷史。冷戰時期,學術界與政府之間形成了一條紐帶,對所謂的「國防知識分子」的需求應運而生。政策制定者希望專家能夠控制潛在的核戰爭並提供合理的分析。持續的冷戰困境——如何贏得核戰爭,如何獲得對敵人的技術優勢——鼓勵了學術界的投入。
在此期間,社會科學家在白宮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正如大衛·哈爾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記錄的那樣,約翰·堅尼地總統曾咨詢過哈佛大學的「精英和才俊」,並向基辛格和麥克喬治·邦迪等年輕學者尋求如何應對蘇聯的建議。後來的總統們效仿堅尼地的做法,招募前國防部長羅拔·蓋茨(Robert Gates)所說的「書呆子」進入國家安全機構。

2016年12月11日,布熱津斯基(左)和基辛格(右)同時出現在挪威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論壇
像基辛格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後者是林登·詹森的顧問,後來成為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樣的人,他們的職業生涯都是從常春藤盟校開始的。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模式。近年來,像康多莉紮·賴斯和蘇珊·賴斯(沒有親屬關系)這樣的人物也是如此,她們都是博士,分別成為候選人喬治·W·布殊和巴拉克·奧巴馬的顧問。
哥頓也經歷了類似的軌跡。他於1991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和國際經濟學博士學位,撰寫了一篇關於法國總統戴高樂堅定外交政策的論文,並將其修改為他的第一本書【法國的某種理念:法國安全政策和戴高樂主義遺產】(1993年)。20世紀90年代末,哥頓憑借在歐洲事務方面的專長,在克林頓政府擔任歐洲事務主任一職。在奧巴馬總統任期內,他擔任過類似職務,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擔任歐洲和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之後於2013年至2015年擔任總統特別助理兼中東、北非和海灣地區事務協調員。
在克林頓和奧巴馬執政期間,哥頓是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定期為【外交事務】撰寫評論,並撰寫了幾本關於國際關系的書。2015年,他重返外交關系委員會,並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內一直任職。隨後,他在哈裏斯2020年競選期間擔任其外交政策顧問,之後擔任了目前的職位。
喬治·W·布殊總統任期是哥頓思想轉變的轉折點。直到21世紀初,他發表的作品幾乎都是針對其他學者的;伊拉克戰爭使他更多地擔任公共評論員和評論家。雖然民主黨內部許多人毫不猶豫地支持了布殊的戰爭,但哥頓卻更加謹慎。在入侵前兩個月,他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對布殊不顧一切地入侵提出了間接批評,希望總統能夠更多地招募歐洲人。
入侵後,哥頓以更強烈的措辭譴責了布殊的外交政策。占領伊拉克一年後,他寫道:如果布殊的目標是應對「全球恐怖主義帶來的直接威脅」,那麽「伊拉克戰爭嚴重分散了反恐戰爭的關註」。哥頓認為,只有「中東轉型」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但這一結果不太可能實作,而且需要投入大量國際資源。
哥頓在2004年與傑里米·夏皮羅合著的【盟國在戰爭】一書中重申了這一觀點。哥頓和夏皮羅認為,美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特殊方式疏遠了歐洲盟友,損害了全球安全。美國和歐洲在如何發動「反恐戰爭」以及什麽構成對全球安全的威脅方面存在分歧,這損害了聯盟體系,但「2001年至2003年期間執政的領導人所秉持的哲學、個性、決策和錯誤導致了伊拉克問題上的跨大西洋沖突」。美國和歐洲大國都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從而在未來導致跨大西洋聯盟破裂,但分歧並非不可調和,和諧相處並非「單邊主義和好戰美國與和平主義歐洲」的漫畫所描繪的那樣。

在2006年的一篇,隨著伊拉克陷入宗派暴力,哥頓慶祝了美國外交政策中「布殊革命」的終結——以「先發制人」理論作為美國戰略的基礎。在伊拉克建立一個繁榮、民主國家的目標不僅未能實作,而且可能根本無法實作。這場戰爭還掩蓋了國內外的其他問題。哥頓寫道: 「由於在伊拉克的過度擴張、疏遠重要盟友以及讓反恐戰爭掩蓋了所有其他國家優先事項,布殊讓美國陷入了一場失敗的戰爭,使軍隊捉襟見肘,並耗盡了國內資源。即使布殊面臨新的恐怖主義威脅,或對國內可能發生的恐怖襲擊感到焦慮。」 專制政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的情景,以及美國感到富有、強大和正確的情景,是非常可取的,但不太可能很快出現。
哥頓在【贏得正義之戰:美國與世界的安全之路】(2007)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指責布殊浪費了美國作為全球保護者的「聲譽」和「合法性」。美國在全球南部的歷史無疑誇大了這一點,但哥頓的觀點是正確的,即911襲擊事件幾乎引起了全世界對美國的一致同情和善意,美國需要采取「維持美國實力、凝聚力和吸重力」的政策,而不是使用武力。書中總結道。 與中東國家開展外交活動、減少美國對外國石油的依賴以及避免威脅升級是更安全的替代方案。 哥頓總結道,美國無法贏得反恐戰爭,但可以制定「應對恐怖主義挑戰的新戰略」,包括以兩國方案解決以巴危機,透過外交手段「遏制」伊朗,確保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加強與土耳其的聯系,使其成為該地區的穩定力量,並改變軍事化、臃腫的國土安全機構。
在所有這些方面,哥頓都預示了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奧巴馬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伊拉克失去了重點,其不幸遭遇是過度擴張的征兆——簡而言之,美國沒有很好地處理其沖突。總統公開表示,他的外交政策以限制為核心,即「以世界現狀」為出發點。在第一任期的四個月裏,奧巴馬說:「我確信我們可以並且一定會擊敗基地組織。」但他避免使用「反恐戰爭」一詞,而是描述為「一系列持續、有針對性的努力,以摧毀威脅美國的特定暴力極端分子網絡」。【輸掉長期戰爭】表明,奧巴馬並不總是能夠實作美國在中東政策限制方面的願景。在哥頓的敘述中,奧巴馬是問題的一部份,而且幾乎沒有什麽例外。
這本書向讀者展示了他們已經知道的結果:
美國的中東戰略已經失敗。
這本書並非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外交政策進行整體敘述,而是講述「政權更叠」的歷史——即努力建設國家並引導歷史朝著美國希望的方向發展——以及為什麽它未能符合美國的利益。哥頓按時間順序講述了七個案例研究,從1953年伊朗政變到阿富汗(蘇聯先發動入侵,然後是美國發動入侵)、伊拉克、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雖然名稱和背景發生了變化,但正如哥頓所言,起源和結果都是一樣的。他總結道,政權更叠應該繼續作為美國決策者的選項之一,但絕不應該被縱容,因為這種做法往往沒有考慮到「固有的高昂成本、意想不到的後果和難以克服的障礙」。
這是對政權更叠的有力批判,但歸根結底,這本書是對決策者性格的控訴,而非對美國外交政策本身的歷史或結構的控訴。在哥頓看來, 美國之所以入侵其他國家,並非因為龐大的軍事力量帶來的物質壓力,也並非因為它擁有無與倫比的實力,而是因為推翻一個政權的「誘惑」變得太大,以至於決策者忽視了其他選擇。
事實上, 哥頓將政權更叠歸咎於外交政策領導人的傲慢自大,在他看來,這些人過於沈迷於美國的例外論和一廂情願的想法,對被入侵或幹涉地區的歷史和文化一無所知。 在這方面,他對伊拉克政策的描述是淪陷性的;他表明,監督2003年入侵和占領的大多數人物不會說阿拉伯語,不了解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緊張關系和歷史,或者他們過於相信民主政府可以從政治抗議中產生。即使美國沒有像在伊朗和利比亞那樣入侵其他國家以推翻領導人,也沒有像在敘利亞那樣未能推翻獨裁者,哥頓認為,這些行動的結果還是造成了「意想不到且不受歡迎的後果」。美國領導人缺乏必要的遠見和必要的資訊,無法意識到這種做法行不通,因為「專業知識非常匱乏」。

在哥頓看來,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具有人類固有的弱點: 利己主義、過度自信和好奇心不足。 美國人傾向於樂觀主義,傾向於制定烏托邦式的計劃,但如果沒有嚴厲、嚴格和戰略現實主義的約束,這將成為災難性外交政策的幫兇。在哥頓看來,美國權力機構本身並沒有錯,只是管理這些機構的人辜負了他們的承諾。如果給他們配備更好的領導人,那些傾向於做出更謙遜、謹慎決策的人,那麽我們的政策就會更好。
閱讀【失去長期遊戲】一書,可以了解哈裏斯政府可能與布殊和奧巴馬時代有何不同,但該書對重塑外交政策有何看法?畢竟,拜登避免了政權更叠,使美國擺脫了阿富汗——911後時代的最後一場「永久戰爭」,並宣稱「美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戰爭」。
哥頓的世界觀很難歸類,與傳統的外交政策「Blob(小集團)」背道而馳。 他不像拜登那樣認為美國的力量總是有益的,也不像沙利文所說的那樣,美國總是「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並試圖成為這樣的國家。 相反,哥頓認為「有益」必須得到證明。他還認為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著歷史性的角色,並希望美國成為民主的催化劑,但問題在於細節。如果美國必須采取行動幫助他人——哥頓認為美國應該這樣做——那麽美國必須謹慎行事,警惕意外後果。最重要的是,他擔心美國即使想控制也無法控制事件,他試圖避免「任務蠕變」或不必要的升級。
他對沖突升級的厭惡,或許能讓我們洞悉哈裏斯政府將如何應對加沙戰爭。哥頓在2015年寫道,
如果以色列試圖統治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數百萬巴勒斯坦人,那麽它就不可能「繼續作為一個安全的猶太民主國家與鄰國和平相處」。
但以色列對10月7日襲擊事件的回應已經過去近一年了——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平民被殺害,加沙完全被摧毀,一些以色列領導人宣布打算永久占領加沙——以色列現在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如果哥頓堅持他在【失去長期遊戲】中的結論,哈裏斯政府將努力避免中東地區發生更大規模的戰爭。這意味著拒絕任何一方(無論是以色列、哈馬斯還是真主黨)采取的戰爭升級行動,優先考慮政治解決方案。這意味著不僅要告訴以色列人贏得反恐戰爭是徒勞的,還要積極勸阻以色列發動其自稱為反恐的戰爭。所有這一切都需要美國改變其目前準備地區沖突並無條件為以色列的戰爭計劃提供物質和意識形態支持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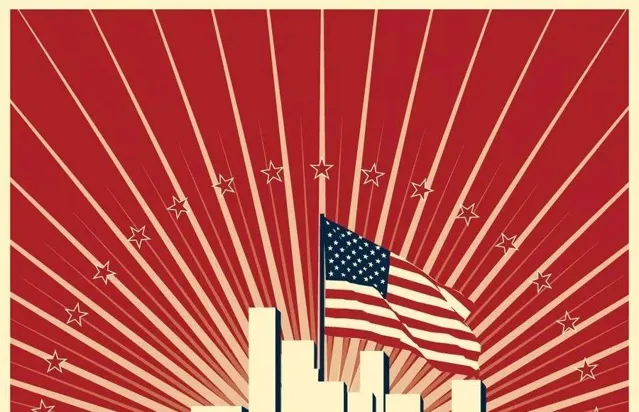
這種變化是否可能尚不確定,但似乎有可能發生一些變化。哈裏斯公開反對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並拒絕否認拜登的以色列政策,但她私下批評該政策。她在競選活動中反駁了抗議者的言論,但也將加沙的破壞和死亡稱為「災難」。哥頓也使用了類似的語言,他認為兩國解決方案必須仍然是「最終目標」,正如他在6月以色列安全問題的赫茲利亞會議上發表的演講中所言——他也不避諱地指出,「定居點擴張、定居者暴力和其他破壞西岸穩定的活動……不利於和平」。
哥頓的發言主旨是,以色列目前的戰爭與其自身的「長期安全」和中東的穩定背道而馳。他說:"現實情況是,如果沒有可信的治理和安全替代方案,哈馬斯就不會被永久擊敗——正如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經歷所證明的那樣。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政府並不這麽認為。在赫茲利亞會議一個月後,就在內塔尼亞胡前往美國之前,以色列議會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透過了一項決議,稱巴勒斯坦建國將對以色列構成「生存威脅」。面對這種頑固態度,哈裏斯政府在哥頓的建議下可能會采取什麽行動,還有待觀察。
哥頓的觀點為他贏得了一些人眼中的「進步派」稱號。拒絕接受美國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世界這一觀點——即美國並非能解決所有問題,短期解決方案也會帶來長期問題——在華盛頓的國家安全圈子裏會讓人被視為進步人士,但這種定性並不十分準確。大多數外交政策進步人士都支持以某種形式限制或削減美國實力。但正如哥頓和華盛頓大多數人的看法,美國可以參與全球事務,也可以結束全球事務;只有國際主義或孤立主義,盡管美國在政權更叠等政策上犯過錯誤,但它必須繼續作為世界全球領袖行使權力。
哥頓的著作中明顯表現出一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傾向,即傾向於全球停滯,希望透過更好、更理性的領導來重塑世界。 他反對約翰·米爾斯海默和史帝芬·禾特等實力均衡論者宣揚的冷酷現實主義,也反對左派的反帝國主義。哥頓在【輸掉長期遊戲】的序言中寫道:「我不認同特朗普本人及其左翼批評者經常表達的觀點,即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微乎其微。」
更準確地說,哥頓是一位務實的國際主義者,他認為必須以克制和理智的態度制定外交政策,並確保手段與目的相匹配。哥頓敏銳地察覺到美國外交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即「長期博弈」——那些不可預見但可預測的突發事件可能會損害美國的利益。他贊同美國國家安全方面一些陳舊的前提,但對國家安全的設計師卻始終表示失望。
簡而言之,他是一位對局外人充滿同理心的內部人士。最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和政策記錄表明了他對自由國際主義和強大美國前景的信念——這種信念雖然因糟糕的結果而受到挫折,但他並不願意否認取得更好結果的可能性。
在這種受挫的信念中,哥頓並不是國家安全機構的典型代表,但他確實有同僚。他的觀點與奧巴馬外交政策顧問賓·羅茲(Ben Rhodes)的觀點相似,後者在2017年遲到了接受了哥頓自2003年以來一直主張的觀點:美國不能以穩定的名義建設民主,也不能將民主強加於人。與此同時,哥頓認為我們不能放棄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也就是說, 「美國能夠且應該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減少沖突、減輕痛苦、促進繁榮、遏制暴行並推進政治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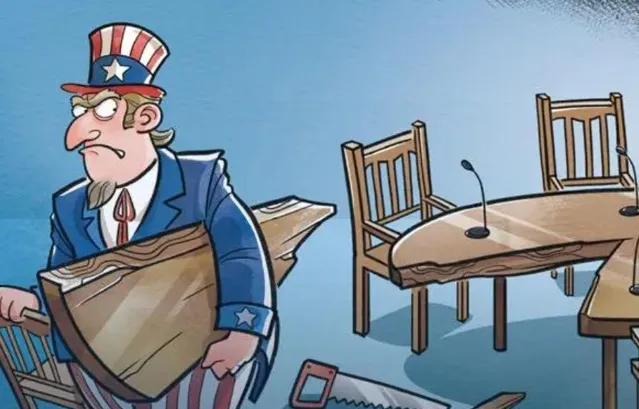
但正如哥頓和其他理性派自由普世主義者所承認的那樣,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切實可行的工作」是一項更為棘手的工作。事實證明,美國在使霸權更仁慈或更有效方面表現不佳。問題不在於監督美國外交政策的人,而在於美國權力的結構本身——其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國家安全預算和慷慨解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懈軍事化。認為無需訴諸國際法或多邊機構即可改善霸權地位的想法是歷史性的盲目行為。
在這方面,值得註意的是,羅茲現在已經邁過了哥頓沒有邁過的那座橋。在【外交事務】雜誌最近的一篇,羅茲認為,在一個不再需要美國主導的世界(包括全球大部份南方國家)中,美國無法繼續維持其主導地位。拜登在推行其外交政策時, 「 一只腳踩在過往,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充滿懷舊之情;另一只腳踩在當下,適應正在崛起的世界。」
哈裏斯政府拒絕與中國進行競爭(在拜登政府領導下,這種競爭愈演愈烈),放棄追求霸權,將正義置於無節制的軍事力量之上,這將是真正的前所未有之舉。包括全球南方大部份地區在內的世界正在尋求緩解地球變暖、猖獗的不平等和剝削以及大國無視不幸者未來的問題。美國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指望美國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保持其主導地位是不現實的。
作者簡介:邁克爾·布雷斯(Michael Brenes)在耶魯大學任教歷史。他與範·積遜(Van Jackson)合著的下一本書是【競爭危險:大國競爭如何威脅和平並削弱民主】。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日新說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