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學術平台「全球研究論壇」(globalstudiesforum.com)展開了一場圍繞「城市研究」和「微觀史」問題的圓桌談。主講人是澳門大學講座教授王笛,與談人則是香港樹仁大學教授、歷史學系主任何其亮。圓桌由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陳丹丹教授(也是「全球研究論壇」創始人和本場活動召集人)主持,參與討論的還有河南大學博士生何元博。以下為本次圓桌談之匯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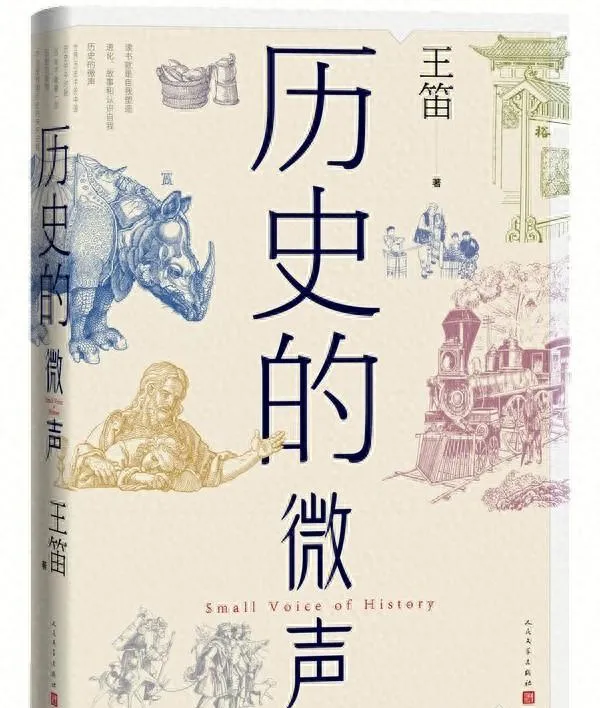
【歷史的消音】,王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一、為什麽選擇做城市研究
陳丹丹: 我們在去年6月份有過「全球城市·長安與洛陽」系列講座的第一季第一場,當時很受大家歡迎,所以很高興半年之後能繼續我們的「全球城市」系列講座。今天有幸邀請到王笛教授和何其亮教授。王笛教授是城市研究的大家,研究包括有成都、長江上遊地區以及城市空間諸如茶館等。何其亮教授研究的是上海及其城市文化、杭州及城市空間比如西湖。我個人也是研究城市的,研究的是民國初年上海的清遺民,還有張愛玲和王安憶的城市文學。
今天的圓桌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我們先談城市研究,中間加入我們三人對各自的家鄉、各自當下所在地域的討論;第二部份我們就切入到微觀史,會談到王笛教授的作品【歷史的消音】【街頭文化】【茶館】,還有【袍哥】等。現在先開始城市研究部份,請問二位專家為什麽要選擇做城市研究?
王笛: 我真正開始城市研究是1991年在美國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的博士論文有三個題目,其中兩個和城市史有關,分別是成都街頭文化、茶館,以及和城市研究關系不大的袍哥。最後我選定了成都的街頭文化。我選擇城市史主要是基於我當時對中國學術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研究生期間我閱讀了大量的城市史研究成果,發現關於中國的研究有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上海的研究特別多,但是對內地的研究相對薄弱。第二個問題是重鄉村輕城市,我看到很多關於區域的研究,幾乎都是以農村為主要的研究物件,而當時城市史的研究,上海之外的如羅威廉的【漢口】這樣的著作並不多。國內的城市研究幾乎也是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由此,我感到整個西方對中國城市的研究是一個不平衡的狀態。而且我認為上海其實不能代表中國的城市,上海是一個西化的港口城市,是在近代貿易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它是中國,但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甚至不是典型的中國。像成都這樣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傳統城市,其實更能代表我們稱之為的中國城市。所以我提出要研究一個全面的中國、另外的中國,只知道上海是遠遠不夠的。同時我並不是研究整個成都,而是研究成都的某一個方面——街頭文化。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內地城市的現代化過程中,去發現一些我們透過上海或北京所看不到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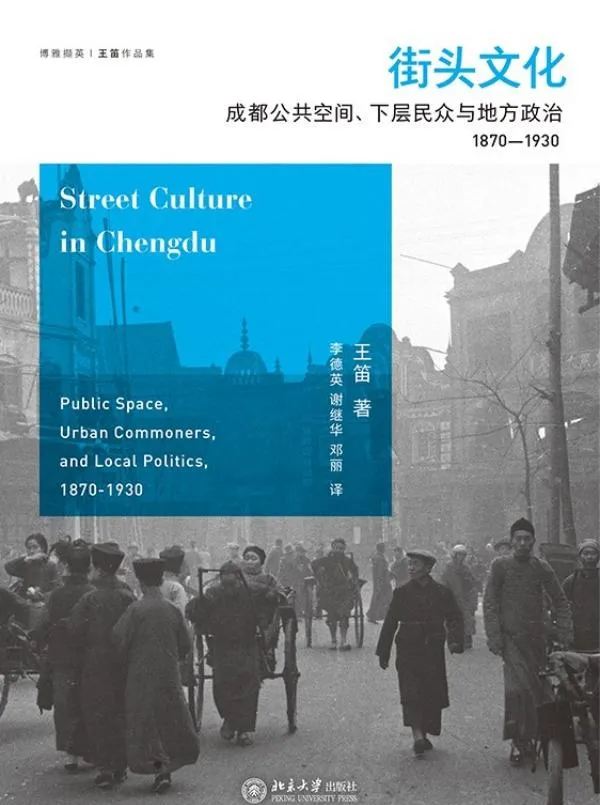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 1870-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版
何其亮: 我覺得自己其實並不能算作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者,因為我的研究路數其實還是以文化史為主。我的學術其實比較任性,體現在我的學術跟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我做上海史是因為在我26歲去美國前,生命中的大部份時間都生活在上海市的黃浦區。其實那裏不光是一個店鋪林立的商業中心,也是娛樂場所的集中地,有很多戲院、電影院等等。所以我後來做戲劇、電影,就是受從小生活環境的影響。但當我到美國讀了一些美國的上海史專著後,發現其實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回看上海,這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太熟悉的東西,我反而要從遙遠的大洋彼岸的角度去重新認識。
現在我搬到香港,又給我提供了一個回看上海的角度。所以我說生活的經歷跟學術息息相關,對學術是有幫助的。我非常支持王教授剛才說上海不是一個有代表性城市的說法。我在自己的一篇博士論文裏寫過一句話:上海不是a representative city of China,上海是a city of representations。對我來說,城市除了城市管理和基礎建設等物質上的東西,還代表著一種想象。這種文化想象會脫離物質一直存在。比如我每次到杭州的孩兒巷,腦海裏便會浮現陸遊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到了香港,從小看港片長大的我也會有意去尋找看過的電影電視裏的場景。這是我研究城市史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跟我的研究方法也有關系。
陳丹丹: 我回應一下王笛老師關於上海研究的問題。我開始研究上海時,正好是李歐梵老師寫【上海摩登】的時候,大家都在談上海是一個很摩登的地方,但我的研究主要是寫上海不那麽摩登和現代的部份。所以我研究的民初上海的清遺民是前現代的,我寫張愛玲也是寫她呈現上海比較傳統中國的一面,其實是在挑戰當時的一種上海敘述。所以我比較關註上海十裏洋場之外的部份,比如王安憶作為共和國的女兒,其作品經常強調上海的邊緣地帶,【長恨歌】之後的作品也是一直探索上海本身所包含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部份。
我在北大讀書時,我的導師陳平原教授當時正在進行北京研究,他提出這個北京研究其實也是為了回應上海研究,所以有這樣一個學術的脈絡在。王教授您說到您做城市研究是受您的導師羅威廉教授的影響,在他的那本【漢口】中,他回應、挑戰了馬克斯·韋伯的資本主義研究——韋伯認為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成熟的城市共同體。所以我覺得王笛老師的這部著作其實也呈現了這麽一個學術脈絡,即除了研究日常文化,我們也會思考一些歷史的宏觀取向,如資本主義的興起、中國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也歡迎大家待會兒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二、城市研究中最感興趣或讓自己興奮的地方
王笛: 的確,我在寫【街頭文化】時,羅威廉出版【漢口】後引起很大的反響,因為如你所說,他回應了韋伯關於中國的看法。韋伯認為中國沒有發展出城市共同體,中國人都是把鄉村視為真正的家,而只視城市為一個謀生的地方。我記得1990年代,魏斐德和葉文心編了一本論文集,叫【上海的寄居者】,可能也是來自這種思考。但羅威廉的【漢口】提出這是不對的,出版以後影響很大。雖然我寫成都街頭文化並非以此為出發點,但我後來在閱讀成都資料時發現了很多例項。成都市民在清代就把自己看作是成都人,不斷強調成都是成都人的成都,有完整的Community,有土地會。過去說中國沒有城市的概念是因為缺乏紀念碑式的建築物,但進入城市的研究後可以發現,民國初年成都就修建了四川保路死事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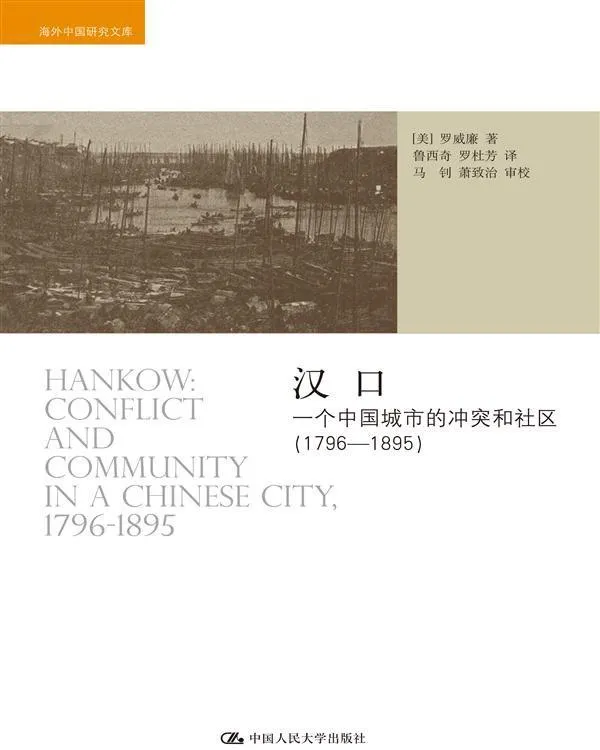
【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群(1796-189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版
當我讀了新的資料,對過去大家很困惑的問題有了一點新發現,這就能支撐我把一個課題做五六年,甚至十幾年。再舉一個例子,成都的茶館有一個功能,在晚清民國時期,人們有了糾紛就到茶館裏去「吃講茶」,好多糾紛就在茶館裏解決了。黃宗智有個重大的發現是為什麽在清代很少有民事訴訟,他認為好多民事訴訟在縣一級裏經過調解就解決了。但他沒有提到在成都甚至江南,絕大部份的糾紛在民事訴訟前已經在茶館解決了。所以為什麽在民國時期有人說茶館是「最民主的法庭」,地方的司法權在相當的程度上被民間像袍哥這樣的組織分化了。當時我在思考這些時覺得這些重大發現遠遠超出了茶館問題的範疇,涉及到了中國的司法系統、社會自治等大的問題,這就是讓我很興奮的地方。
何其亮: 歷史研究的確是一個很令人興奮的事情,特別像做偵探。我前兩天和一些研究生說,研究做得多了,內心會產生一個跟外部世界有聯系但又隔絕開的第二世界,那一刻你會覺得許多東西都似乎是身外之物,沒有那麽重要了,你內心世界的那種滿足是無法形容的。
我剛才說了我做學術比較任性,很多研究和我的日常生活是有關的。比如我做上海(研究)時,腦子裏已經呈現了一幅地圖。較明顯的是2005年我在上海檔案館搜尋盛宣懷出殯的檔案,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描寫盛宣懷家屬必須走工部局規定他們走的那條路徑。我當時特別興奮,因為工部局檔規定的那條出殯路線就是我生活過的地方,讓我感覺特別親切。我還記得那時候我一個人坐在美國南卡羅來納的辦公室裏,當時我腦子裏的世界已經超越了周圍的環境,是在走那條路線,因為我太熟悉那個城市了,我想這就是現在所謂的city walk吧。這就是我為什麽寫東西特別興奮、有愉悅感。
三、為何選擇成都、杭州、茶館、西湖
陳丹丹: 何其亮老師寫過上海,當時怎麽又選擇杭州?剛才我們提到茶館,王笛老師書中有寫到各地不同茶館的比較,提到過成都茶館的獨特在於農業的影響。如果成都茶館文化是受農業文化的影響,那其它城市會不會受到更多商業文化的影響?比如說現在阿裏巴巴在杭州,比如說明清商品經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考量?此外茶館和西湖都是公共空間,就聯系到我們城市研究的一個經典話題:公共空間,請問二位對此有沒有什麽觀點?
何其亮: 杭州是我特別喜歡的城市。1993年我第一次去杭州看到西湖時感覺驚為天人,似乎見到了夢中情人,這種感覺是縈繞在我心頭30年一定要把它做出來的,所以2023年我出版了西湖的書。我一開始想做景觀史,因為高崢教授的【接管杭州】珠玉在前,我想有一些突破,於是想到西湖景觀。但後來我越做越往環境史、非人類史靠攏,不過還是在杭州城市研究範疇內。西湖有一個特點是它城鄉結合。1912年前西湖是城墻外的一個郊區。後來城墻拆了,西湖從城市以外變成城市的中心地帶。剛才丹丹老師提到杭州這樣的城市是不是和商業有關,因為成都是農業有關,有點像芝加哥,有一本名著討論了芝加哥和中西部農村之間的關系。杭州絕對跟大運河有關系,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和杭兩個城市的意義其實就在大運河運輸的關系裏。所以城市發展和傳統時代的商業是密切相關的。後來我還看了一些徽商的書,我發現杭州是徽商離開徽州山區外的重要一站。所以杭州的發達肯定和商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
陳丹丹: 你在香港待了這麽久,對各地飲茶有沒有什麽新的發現?
何其亮: 香港有屬於有閑階層的飲茶文化。但茶餐廳和飲茶不一樣,茶餐廳是去吃一頓飯,很快可以回去接著上班;而飲茶可以社交,也可以獨享這個空間,一個人在那裏靜靜地坐一下午也沒事。揚州也有早茶,我覺得像成都、揚州、廣州、蘇州等地區,不管是商業文化還是農業文化影響,只要有錢有閑人聚集的地方就會有茶館,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
陳丹丹: 對,很有意思,就是揚州飲早茶的習慣還在持續,但在南京,這種早茶文化就不是很濃郁,上海那當然是咖啡館了。大家有沒有新的見解?
何其亮: 我說一下上海咖啡的問題,這要分兩方面看。一方面,中產階層、白領階層興起,有喝咖啡的習慣是正常的,我們經常會看見白領手上拿一杯咖啡匆忙趕到公司上班;另一方面,上海的咖啡文化是被刻意渲染出來成為城市的文化名片,我去了南韓發現那裏咖啡館的密度比上海高,其實不見得咖啡在上海有什麽特別大的特色,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有意制造出來的城市象征。
王笛: 把喝茶作為日常生活,據我觀察,現在也就是四川成都、重慶了,可能是整個20世紀的變化。上海在晚清有好多茶樓,20世紀開始越來越少,我覺得主要還是生活節奏和商業化的影響。像廣東雖然過去茶館也很多,但演化到今天就是吃早茶;在北京,我們所知的老舍筆下的茶館也早就沒有了。我想這還是和地域的生活節奏有關,成都要慢一些,因此它不僅能提供茶館發展的環境,咖啡館也多。在成都,大家不是像剛才其亮描述的,咖啡拿在手上匆匆忙忙去上班,而都是坐在那裏慢慢聊,一杯咖啡喝一兩個小時。所以茶館是根據地區的生活習慣、節奏發展起來的。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由於城市大拆大建,小街小巷逐步消失,街頭文化、茶館文化也隨之消失了。成都現在的茶樓和我們過去概念中傳統的那種茶館還是有很大區別,而那種真正表現過去茶館文化的,大家坐下來沒有什麽私密隨便聊天的茶館,在成都也越來越少。所以我在這裏推薦大家去成都市內人民公園的鶴鳴茶社,以後這種傳統的茶館會越來越少。

鶴鳴茶社
陳丹丹: 王教授提醒我了,像南京的六朝煙水氣,就是【儒林外史】中著名的那段,挑糞的人他們也會相約去看夕照,這一點特別有意思。我們從明清時期開始,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了,所以我想也可以考慮一下這方面的問題。元博你有沒有什麽要補充的?
何元博: 我小時候家門口附近就有一家茶館。大概十年前,西昌城市裏還有三家老式的茶館,但現在經過各種舊城改造、消費升級,可能只剩下一家了。那個茶館和成都茶館還不太一樣,西昌的茶館裏很多是做工、騎摩的的社會勞動階層,他們會在那個茶館裏坐上一整天。在茶館門口,也形成了一些產業,就是摩的產業。因為我們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很多外地或山上的少數民族,如彜族,他們來到這個城市裏後,可能會去從事摩的等行業。他們很喜歡在茶館裏聚集,可能一坐一整天,幾人坐著喝茶,圍著打牌,這是我感覺西昌茶館一個蠻特殊的地方。
陳丹丹: 這個摩的文化挺有意思,我想到了現在從咖啡館出來的打車文化,王笛老師書中也提到了黃包車。
四、喜歡哪些城市研究的著作
陳丹丹: 接下來的問題是,二位喜歡哪些城市研究的著作?王老師您寫作的時候是以哪些著作作為榜樣?
王笛: 我一直強調學術研究一定要大量的閱讀!不僅是閱讀和自己的研究專題有關的,很多閱讀其實是間接的。閱讀的思路一開啟,你在寫作過程中會不自覺地將從其他研究方面得到的啟發用於分析自己的問題。我在寫【街頭文化】時,想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地方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沖突,其實已經超越了成都城市的問題。我在寫【茶館】時,第一卷解決的是: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的沖突,也超越了成都城市本身。
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不關註現代城市,但現在城市的大拆大建,城市的發展對城市文化的影響,不能只是讓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去研究。【茶館】的第二卷,寫1950年到2000年,就進入到了過去我們歷史學很少涉及的、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城市。我作為歷史研究者,要回答歷史的問題,不是說只能讀歷史研究的成果。人類學、社會學透過田野調查提出問題、發現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對城中村的研究,對我來說非常有啟發,我們歷史的研究也可以和他們進行對話。
最近二三十年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科在互相交叉跨越。像【茶館】的第二卷實際上解決的是社會學考慮的問題,包括公共領域的問題。但這些超越了歷史學的討論一定是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的。所以說我們一定要跳出自己的領域,閱讀始終是開放的、不分學科的,始終是要超越自己研究課題的本身。
陳丹丹: 我之前研究城市比較像文學的手法,把城市作為一個文本、一個意象,會用到比如說齊美爾、德勒茲的理論,比較文本化。我覺得歷史學家們就好像給我們開啟了另一個世界,比如您說到茶館背後有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史,然後需要研究到稅收、各種檔案、各個階層等。跟我們文學的研究完全不同,我們文學做城市研究時用理論的話,通常會用文本化的文學理論來研究。接下來我們就交給何其亮老師,就是你喜歡哪些城市研究的著作?對你的影響,可結合經典理論、空間理論來談。
何其亮: 【上海摩登】對我影響很大,它解答了我在博士時期關註的一個主要問題:現代性。【上海摩登】給我們解答了現代性的兩面怎麽結合起來。它有兩個部份,第一部份講的是城市基礎建設等物質層面,另一部份講的是那些作家如新感覺派、張愛玲等,是一種文化表達、美學敘述。【上海摩登】對我來說,不光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上海的問題,而是怎麽把這些東西結合起來。不過我認為書中作者選擇的小說家要具有代表性。如果1930年代都沒人看這些作者的作品,你憑什麽說他就代表了上海社會的一種普遍心態。這也是為什麽我不太研究精英階層的作家,我喜歡做大眾流行的,比如鴛鴦蝴蝶派。
有一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就是【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其實裏面描寫的和【上海摩登】有點像,比如寫鄂圖曼改造後的巴黎,導致像波德萊爾等一些法國作家的心態發生改變。所以我一直比較喜歡這種寫法,即外部環境的改變,如何改變人的感覺和人的表達。這些對我影響比較深刻,我現在的研究很多時候回答的都是這些問題。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商務印書館,2013年9月版
五、「城市研究」在全球語境與中國語境中,現今的瓶頸在哪裏?還能怎樣突破?未來的研究方向?
陳丹丹: 我也想到【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還有【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文學完全是把城市作為文本,再去細讀一些文學文本,我習慣了這種研究後,看歷史學家的著作,會覺得又開啟了一個更宏大的世界。
王笛老師剛才提到社會學、人類學,現在我覺得我們進入了一種社科的時代。社科的進路特別多,比如政治經濟學、數位平台、外賣騎手等。不知道您現在是準備往社科化方向,還是往探索普通人心靈的方向發展?還有怎樣突破現有的城市研究,比如當年想突破【上海摩登】,我所做的嘗試是研究上海不現代的方面,社科的做法好像又跟人文完全不一樣,比如說他們會比較印度和中國的城市管理等,不知道我們應該是去結合社科,還是繼續人文路徑?因為我們人文要突破的話需要新的理論,但其實繼本雅明、列斐伏爾等等之後,理論突破似乎也越來越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現在更社科化了?所以請問二位:城市研究該怎麽突破?我們現在城市研究的瓶頸在哪兒?怎樣面對社科化?
王笛: 我的第一本書【跨出封閉的世界】是社科化最深刻的,裏面幾乎任何問題都要量化,讓人覺得非常枯燥,很難讀。所以我後面的研究有意識地要回歸人文,就是我們所說的語言學的轉向,這種轉向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在那之前,歷史研究的社科化確實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但是也造成了歷史的著作越來越遠離大眾。
海登·懷特寫了【元史學】( Metahistory ),對整個西方歷史學都有很大影響。我在美國讀博時也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我的第二本書【街頭文化】裏沒有一個統計表,就是有意要回歸人文。開始去關註個體,從宏大敘事轉向日常生活,從精英轉向普通民眾,這樣的轉移一直持續到今天,茶館也好袍哥也好,都是以人為中心。其亮剛才說到環境史,環境史是把人放在環境中,也有人,但我這裏強調的是要有個人的故事,個人的經歷。
史學研究的生命力就在它的多元,任何學術的研究只要做出了學術貢獻,那就是它的價值,不可能都像科技發展比如ChatGPT那樣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現在到了年底,要開始各種年度學術熱點等等,我經常收到這樣的邀請要我提出什麽熱點,但我從來都不參與。去找熱點學術是沒有意義的,其所謂的熱點就不是學術,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的課題積累,才能有進步。哈貝馬斯這樣的大學問家非人為可造,但有了千千萬萬個踏踏實實做課題研究的,他自然會就會湧現出來。如果大家都去找熱點的話,100年以後都出不了大家。
何其亮: 我回應一下社會科學的問題,我在做一個結合了社科但不完全社科的課題。我以前做流行文化、大眾文化較多,這次結合了這兩者,是電影院興起和上海城市管理之間關系的研究。因為我一直以來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城市環境的改變會造成人認知的改變,電影院的興起對城市的管理產生了極大的挑戰,我希望把urban studies和film studies這兩個東西融合在一起。
另外一個問題是瓶頸如何突破,我覺得城市研究有好多東西還沒做,比如還沒有完整論述過城市是誰的城市。這個問題在我研究上海時便感覺到了,也有人提出來:為什麽一些在上海的外國人和上海華人,或者說不同的作家(比如說鴛鴦蝴蝶派或左翼),他們寫出來的上海不一樣?誰有權利可以把城市描述出來?王笛老師在書裏指出,劉大鵬的日記十人去看十人寫出的東西都不同,我印象很深。那不同人生活在上海,寫出的東西也不一樣,這是誰的聲音的問題?比如打工人、外賣騎手,是否有一個真正的平台可以去寫出他們的經驗、感受、對城市的看法?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
現在人類學、社會學的人做得比較好,當然歷史學也有很多這樣的做法,比如北京的黃包車夫,老的經典著作如裴宜理【上海罷工】,講了好多工人階級。所以我覺得很多題目都可以豐富著繼續做下去。
六、城市研究中公共空間的消退與網路虛擬公共空間
陳丹丹: 謝謝,其亮老師說的電影院其實也回應了我們之前所說的公共空間。1980年代時去電影院對人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你看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約會不會在電影院了,所以有一種公共空間的變化。而且現在是不是有一種公共空間的消退?因為網路的虛擬的公共空間更蔓延。
王笛: 目前很多年輕人有了社恐癥,但眼下正是我們要回歸日常的時候。雖然網路也可以叫公共空間,但是它是虛擬的。現在不管是城市還是文化、歷史、社會學等等的研究者都要面臨這樣的問題,就是創造一個有吸重力的城市空間。
陳丹丹: 王教授提出的公共空間的回歸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覺得也和當下的數位時代有關系,最近大家都在討論什麽E人I人,即外向的人和內向的人,就是當代靈魂比較迷茫,我覺得在這背後也存在數位時代的危機。我們剛才其實講到的是一種公共空間的變遷,以前1980年代電影院是很重要的公共空間,但現在好像已經不是這樣了,所以其亮老師,你覺得現在實體的重要的公共空間是什麽?
何其亮: 其實電影院不是一個完全的公共空間,它的環境是黑的,是一個半私密的公共場所。電影院還有一點做夢的感覺,因為漆黑的環境裏有一束光在隧道前面,我對這種說法印象很深。
我們說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人的原子化,即人的關系很碎,不能在公共空間聚集。這是技術發展、互聯網興起的一個趨勢。現在看電影的方式越來越多了,慢慢開始有網上觀影,全家老小買飲料爆米花去電影院這種儀式似乎在漸漸消失。所以王老師說要回到公共空間有它一定的道理,是我們怎麽和時代妥協的問題。技術發展到這一步,我們確實不需要離開家就可以看電影,但人是社交的動物,有這個需求。如何回到這種社交狀態也是一個難題。而且我覺得不能把互聯網作為一個真正的公共空間,因為互聯網上充分交換意見的功能比較弱,它產生了資訊繭房,只是重新確認你想知道的東西。因為智慧推播,人接受的資訊變成已經挑選過的,這非常可怕,把人困在了一個幻想的世界裏。這是我一個粗淺的看法。
七、對微觀歷史研究、宏觀歷史與微觀歷史的互動的感想
陳丹丹: 回到公共空間的話題,我覺得電影院其實像一個喻體,讓我想起蔡明亮的電影【不散】,他拍了一個倒閉的電影院的空間,裏面有一位殘疾女性每天從其中走過,她其實是在跟時代告別。那現在我們就從城市研究切入到微觀史吧,王老師您做微觀史,其實肯定有宏觀的抱負吧?您剛才所說的第一本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我不覺得是枯燥的,我覺得有一種樸素的美感,好像開啟了一個宏大的世界。王老師剛才也提到了一些他很喜歡的作品,如【起司與蛆蟲】【蒙塔尤】【屠貓記】,還有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一些作品,不知其亮老師有哪些心頭好?你覺得你研究的是微觀史嗎?有沒有非常喜歡微觀路徑?有沒有心儀的微觀史著作?
何其亮: 昨天準備時我特地想了一想,我的研究肯定是微觀史,都是非精英階層的普通人。作品的話, Ladies of Labor, Girls of Adventure 這本書對我影響很深,寫的是美國紐約移民女工的生活方式,她們喜歡流行服裝,喜歡化妝,看現在被我們稱為爽文小說的東西,裏面都是灰姑娘遇到白馬王子或底層年輕女性遇到了有錢人就完成了階級躍升這樣的情節。這些小說都是地攤上賣的流水線產品,故事有套路,除了人物名字不同,情節其實都差不多。我當年印象很深,這本書最後把這些細節凝練到紐約移民女工的政治鬥爭上去了。女工們看了這些小說後產生了ladyhood的自尊,覺得自己也是有價值的人,也希望在勞資關系上爭取權利。這種自我尊嚴就是從看這些小說追求fashion中來的。這本書對我影響比較深刻,我經常把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的東西和普通人的政治訴求聯系在一起,當然我這種復制不一定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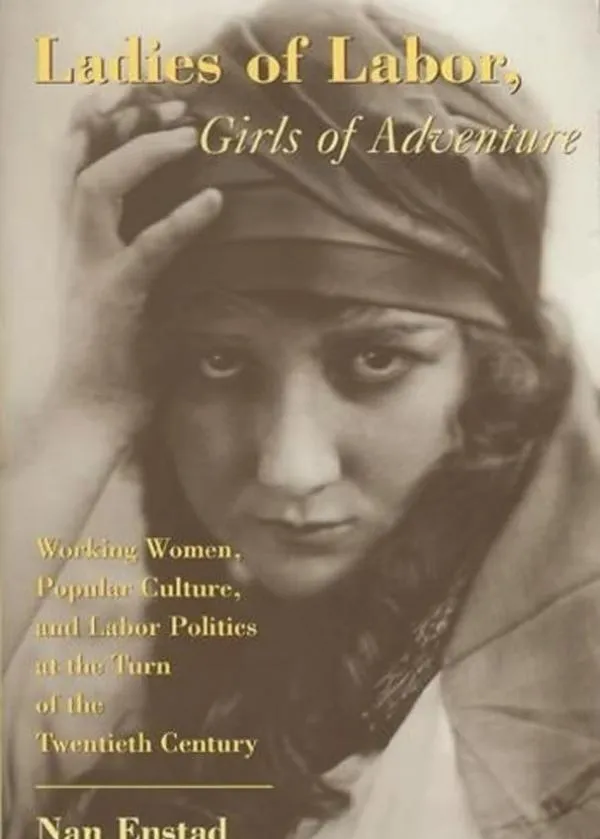
Ladies of Labor, Girls of Adventure,南·恩斯塔德/著
陳丹丹: 王笛老師您有沒有要補充的?您微觀史做到現在,有沒有覺得哪裏存在局限?
王笛: 局限肯定是有的。我當然希望寫一本書,既能回答微觀的問題又能回答宏觀的問題,但這兩者是很難兼得的。做得比較好的微觀史能透過一個個案、一個人的經歷幫助我們認識宏大的問題。如勞勃·達恩頓的【屠貓記】,它展示的是法國大眾文化、工人階級等大的問題,雖然屠貓事件本身不那麽重要,但他能把這個事件提煉出來,觀察後面文化的東西,我覺得做得比較好。
我在【袍哥】一書中,把雷家故事講出來,好多人讀了覺得你去講其他的幹啥?可能我表達得不夠好,讓有的人覺得有些內容是不需要的,但其實我的重點是要透過這些看後面地方社會的暴力秩序的關系。
最近讀了一本書可以推薦給大家,叫做 Stranger In the Shogun’s City ,寫一個農村婦女逃到江戶去謀生。這本書非常有意思,這個婦女的父親是廟裏的,她逃到江戶以後寫了大概好幾百封的信給家裏,就在廟裏留下來了。這些信裏有她闖江戶城的經歷,一家一家的打工,怎樣生存等。江戶時期的一個普通婦女就這樣被記錄下來,寫得非常好看,像讀小說一樣。個人的經歷背後展示了整個江戶城的畫面,剛好又是馬修·佩裏的黑船到達前後的日本轉折時期,各種因素交匯在一起。這樣的微觀的著作就是寫得非常好的。
陳丹丹: 謝謝王教授,之前有一些觀眾提到他覺得社科也有局限,就是可能缺乏對美的感知,我覺得像這種微觀史做得好的,其實它還是來自於一種個人功力吧:對歷史的感知、怎麽去把握那個精神世界等。然後讓我們何元博同學來介紹一下你剛參加的法律史的尤陳俊、杜正貞等幾位教授的讀書活動裏,他們覺得【蒙塔尤】對他們研究的影響是什麽?
何元博: 幾位老師的學科不同,對於【蒙塔尤】這本書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較統一的一點是大家從裏邊學到了一些方法論,包括它的一些研究視角。大家比較關註的是,【蒙塔尤】是怎麽用宗教裁判等檔案,去構建起那麽細碎的鄉村社會關系網路的。杜老師說,她也想用中國的一些檔案文書去做明清時期中國一些村落的研究,希望能從中獲得一些借鑒。仇鹿鳴老師現在做的也是用墓誌銘去復原唐末五代中下層一些人士的社群網路,還有基層生態,這和【蒙塔尤】有一些異曲同工的地方。【蒙塔尤】是鄉村社會史,像王笛老師得【茶館】【街頭文化】,包括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其實是城市史的話題。那麽可以思考,鄉村史和城市史,雖然都可以用微觀史或者新文化史來統攝,但兩者在具體做的時候,是否有一些區別聯系或者分別有什麽特征?以及鄉村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是什麽?
八、鄉村研究和城市研究在使用檔案上的區別
王笛: 元博這個問題,其實微觀史的興起還是從研究鄉村開始的,鄉村比城市的流動性小,人類學所關註的人類行為保留的完整性比城市高得多。城市的特點是移民人口的流動,人類學所要回答的問題在城市中很難找到,這也是為什麽早期城市研究的著作很少。
現在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城市也能像鄉村一樣進行微觀史的研究。問題的關鍵在於微觀史研究最重要的特點:它取決於資料。做微觀史研究千萬不要先選好題目再去收集資料。比如我的【茶館】兩卷本,第二卷就搞了整整12年,太累了,完全不推薦這種做法。寫微觀史需要先看哪些資料有做的可能性。現在鄉村的檔案被逐步發現,華東師大、北大、上海交大等都成立了相應的文獻中心,這些文獻中心逐步從各個鄉村、生產隊裏收集大量的資料,在座的老師同學如果要寫微觀史的著作,要先去翻這些資料。像中山大學的邱捷老師,是把中山大學歷史系保存的南海縣知縣杜鳳治完整的日記整理出來,並寫出了很好的研究著作。我覺得司法檔案資料是以後寫中國微觀歷史的一個主要途徑,但很多地方檔案館由於倉庫庫存滿了,會把存不下的資料拿去化紙漿,我們一定要能搶救一點算一點,這都是我們以後微觀史發展的珍貴資料,一定要珍惜。
何其亮: 研究近現代中國史沒有檔案肯定不行的,而且檔案和公開發行出版的資料有本質性的不同,它更接近於人的真實感受,更準確描寫當時環境中人的想法。雖然檔案也有一個誰是作者、誰是讀者的問題,也有個人偏見,但檔案確實因為當時不公開,寫的東西比較真實。
在我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時候,檔案的作用非常巨大,沒有檔案基本上無法準確地反映那個時代。我做評彈時做了很多訪談,但口述歷史中間出現的資訊誤差太多了,檔案的存在補充了訪談者在記憶上的一些缺失。有時也會出現檔案缺失的問題,比如做民國史時,因為當時可能沒有保存檔案的意識。香港也有這個問題,香港1990年代是電影的黃金年代,但很多材料居然是沒有的,就是因為當時沒有保存資料的意識,拍完電影大家散夥,資料全當廢紙丟掉了。所以做歷史跟做電影一樣是遺憾的藝術。檔案資料有的話我們就盡量保存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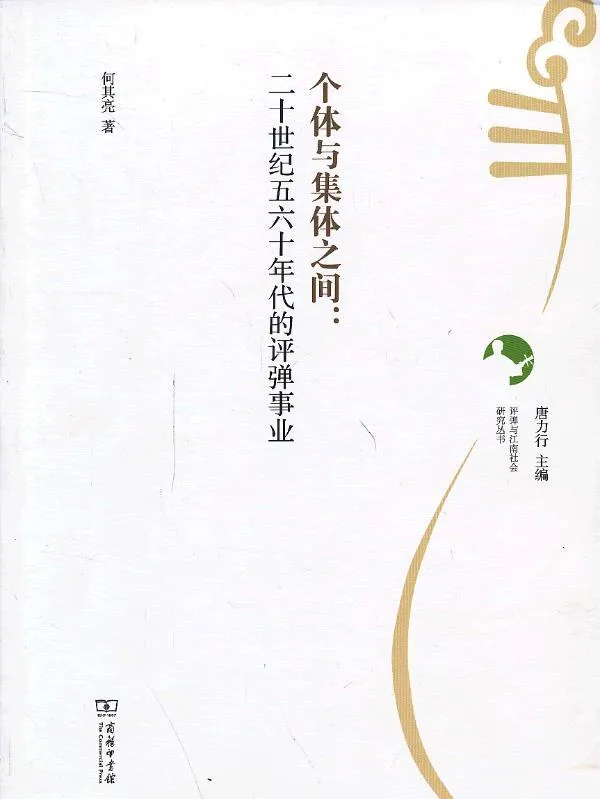
【個體與集體之間: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彈事業】,商務印書館,2013年5月版
陳丹丹: 這邊有一個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的意見,他是做地理學、建築學視域下的城市研究。大家知道現在地理在搞GIS,這位同學就覺得社科現在有兩個轉向,一個是計算社會科學與理工科的結合,另一個是關註精神認知層面,即物質環境和精神認知的交互作用關系。然後我覺得【歷史的消音】這部作品是給大家的一個讀書指南,其中提到了很多可作為範本的經典書籍,還提到羅威廉老師寫陳宏謀,就通向18世紀中國精英意識,我們怎樣透過做一個人的研究去通向整個世紀?王教授還提到了一本書可以作為英文寫作的範本,就是【中華帝國的過去】,不知道何其亮老師讀【歷史的消音】還有什麽心得?
何其亮: 一開始看到王教授讀書不易的那段,我覺得挺感動的,那是時代造成的。想讀書但沒有書的感覺,這在我那個時候已經好很多了。在微觀史上,如今大家都指責的學術碎片化,王教授講得非常好,尤其是年輕學者不可能上來就做個通史出來,都是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做,那你怎麽回答碎片化的問題?王教授給大家做了一個示範,我們如何關心日常生活,非精英的小人物生活,這不光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也是一種人文關懷。歷史是人組成的,哪裏可以天天空談大結構。我們研究法律史時就知道,黃宗智教授的一個基本理念,是成文法和法律實踐是兩回事。所謂法律實踐就是人在做法律,判的人審的人被告原告都是具體的人,不能只做大的結構而不做具體的。這就是我的一些感想。王教授幫我們解答了很多問題,不管是在實際工作層面上還是人文關懷的哲學層面上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陳丹丹: 雖然王教授非常強調微觀史,但我覺得他其實是通向宏觀的。就像王教授不斷地強調微觀史不只是在說一個故事,而是要關註到後面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問題,最終通向一個宏大的世界。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從微觀的視窗進去,去思考、解決一些大的問題,我覺得還是有這樣的抱負是不是?
何其亮: 從現實意義上說也因為每一次你寫的東西,人家會要你講這個案例有什麽意義,那肯定要講你的重要性。我以前美國史的老師總是跟我說significance,意思就是反正我也聽不懂你們中國史研究的什麽,你得讓我聽懂你學術重要性在哪裏。他這麽說讓我印象很深。
陳丹丹: 元博你作為一個正在學習的博士生還有什麽意見嗎?
何元博: 沒有什麽意見了,我對於微觀史也是抱著一個學習並感興趣的態度。對我來說有個難點,因為我現在做的方向是斷代的宋史,可能想做微觀史的研究難度會大一點。也許在某些特定的區域,如敦煌,或材料相對豐富的長安、洛陽,憑借墓誌銘能夠做一點相對微觀的討論,但可能在唐宋大部份地區大部份時候就不知道怎麽去展開一些相對微觀的研究和論述,這可能是我遇到的剛才王笛老師說的材料的限制。
九、接下來的研究計劃
陳丹丹: 有資料的匱乏,但我覺得其實還是需要一些大的手筆的研究,比如說我們之前組織的唐宋變革圓桌討論,還有大分流和現代世界的興起。
接下去交給我們王笛老師,您是不是有幾部作品的寫作出版計劃?是不是通向一個比較宏大的世界?
王笛: 我剛完成了【中國記事】,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時間,關於美國媒體從辛亥革命一直到1928年的新聞報道來看中國,其實就是China through Americans’ eyes,已經全部完成了,上下兩卷。一些美國人在民國初年在中國的觀察和經歷,是非常好的材料,但過去很少受到關註。另外,人民文學出版社馬上出的兩本書都是修訂重印的,一個是【走進中國城市內部】第三版,今天討論的一些問題,包括公共領域、馬克斯·韋伯等都有所涉及;另一本是【消失的古城】的增訂版。我現在正在寫的,還是我已經進行了30多年的袍哥歷史研究,目前第一卷快要完成了,寫的是袍哥的起源,書名叫【開山令】,大概在今年可以完成,是我現在花時間最多的一個課題。
陳丹丹: 我在看您說的【走進中國城市內部】這本書,其實您一直思考的都是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地方和國家的關系,民生、官僚和地方政治,還有袍哥的飲茶、吟詩之中的力量角逐。我覺得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面向我們還沒有提到,就是文史結合,因為王笛老師說他讀了很多文學作品,也從中吸收到很多,所以作品也很多,很像是重新構建出了一個文化的世界。那其亮老師你除了剛剛出版的兩本著作,下面就是研究電影院和管理是嗎?
何其亮: 我今年可以的話,把電影院、電影和上海城市管理這本書寫出來。第二個任務是【人民的西湖】中文版要出了,但因為「人民」兩個字我感覺在書裏沒有解釋得特別清楚,將來會另外出一本關於「人民的電影」的專著吧,這是後面的寫作計劃了。
【人民的西湖】英文版
十、對城鄉問題、城鄉關系的看法
陳丹丹: 我覺得王笛老師【歷史的消音】這本書裏面關於市民的部份,可以跟其亮老師關於「人民」的研究有一個對話。然後這邊有個問題,是剛才那位研究生同學,他提問社會變遷對文化的影響、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我覺得可以讀一下雷蒙·威廉士的著作。我其實研究張愛玲和王安憶時一直在思考城市和鄉村的關系,我寫的是她們的城市書寫之中城市比較鄉村的一面。王安憶有一部作品裏面寫到了農民在城市中受到屈辱,本雅明也有城市是一個墮落的自然史的觀點,不知道您二位對城市和鄉村的關系問題有沒有一些思考?像齊梅爾他寫到大都市會生產一種倦怠的精神生活,後來韓炳哲也提到當代人是倦怠的。倦怠好像是一種城市的心靈。還有我覺得在當代社會,城市和鄉村在數位生活上好像在某個層面,差異已經被大大地抹平了,大家都是一樣地在看抖音,但同時在物質生活中,鄉村和城市又存在差異,不知道二位怎麽看?
王笛: 過去市民和農民是有直接交往的,在我們小時候和改革開放初期,農民都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產品運到城市裏的農貿市場和市民直接交易。但現在沒有了,哪怕菜市場的小商販,都是透過物流批發的菜。過去幾千年形成的城鄉交往模式,被現代物流徹底改變了,農民和城市人之間也被隔斷了,這對城鄉關系的影響非常之大。整個鄉村的日常生活在發生變化,剛才丹丹說到的,從相當程度上來說,好多農民雖然還居住在農村,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逐步的接近,比如上網、看電視、刷抖音,他們也淘寶、拼多多。這對於城鄉關系的影響肯定是深遠的,值得社會學研究。這種城鄉關系隔斷是怎麽發生的,在以後我們歷史學研究的課題裏也都是要思考的。
陳丹丹: 我還想到土地的問題,最近陶然老師有一本書叫【人地之間】,講土地變革,周飛舟老師有一本【以利換利】,也講了地方和土地。我就想到研究城鄉關系應該也要涉及土地關系。謝謝王笛老師的意見,現在把城鄉的問題和人工智慧的問題交給何老師。
何其亮: 城鄉問題我雖然思考過,但對此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就用大衛·哈維的一個說法,世界上沒有城市,只有城市化。以前的擴張是透過物理方面,比如把鄉村的農田變成街道、建築設施,但現在這種擴張是透過一種虛擬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比如抖音、淘寶等,甚至有些高鐵幾乎已經修到了鄉村裏,這些擴張都讓農村的生活方式得到改變。但我覺得城市的擴張是必然的,這是解決人口問題的一個辦法。
人工智慧的問題,我對人工智慧倒不是很擔心。我覺得把它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工具可以,但是缺的數據、材料這些都還需要人去做發掘。人文的工作者需要靈感,人的認知不是大數據或者AI訓練就能學會的,我不覺得人工智慧會對我們有什麽沖擊,有也是好的沖擊,因為做研究確實比以前方便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這是好事吧。
(本文由張芊芊整理,何其亮教授修訂,王笛教授審閱,陳丹丹教授最終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