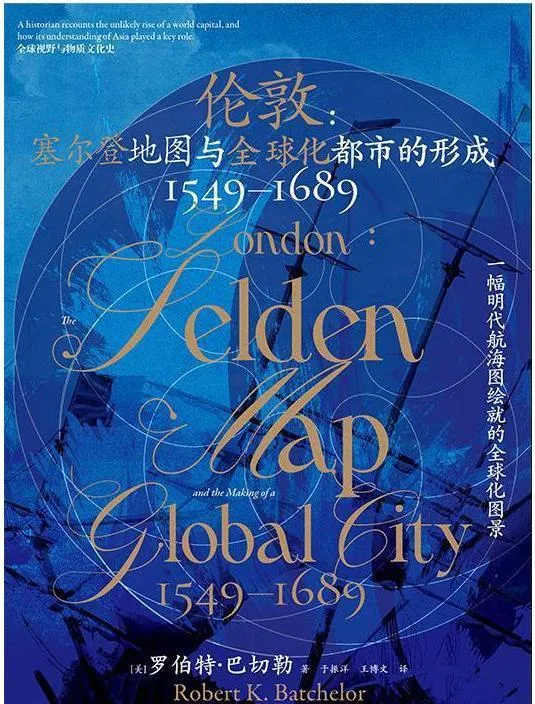很多學者將1687年至1689年倫敦和不列顛尼亞群島發生的諸多事件描述為一個真正的革命時刻,即「現代世界的誕生」。哥白尼和伽利略被轉化為牛頓的數學模型和重力體系,這一過程被稱為「牛頓革命」;「光榮革命」中出現了議會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掌握主權的政治模式,以及最終以1707年「大不列顛尼亞王國」為終結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合並之路,都預示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有著悠久的淵源,往往可以追溯到洛克和牛頓,甚至是17世紀的馬基雅維利時期。與這兩場革命不同,光榮革命總是顯得更加直接和突然。把17世紀80年代的革命與荷蘭早期「激進的啟蒙運動」聯系起來的努力,伽利略的新教轉譯,英吉利共和國時期的激進騷動,一種努力工作和「勤奮」的迸發,城市化,以及培根歸納的一次特別解讀的勝利,這些肯定都是這個故事的一部份。最近的其他一些報道將英國和東亞之間的「大分流」描述為一種自然畸形(lusus naturae),一件自然怪事——幸運地獲得了煤炭、森林、鱈魚,以及疾病導致人口減少帶來的富余土地,進而創造了龐然大物。透過與亞洲的城市化、科學和海洋貿易的接觸,促進全球化的因素的融合及全球化的興起是這本書的主題。正是在倫敦,人們努力將這些不同的力量轉化為「革命」的概念,才使得後來的「英國啟蒙運動」——用羅伊·波特(Roy Porter)的話來說——變得具有韌性、國際化、引人入勝、富有成效。

在普拉西戰役後,勞勃·克雷芙回見米爾·賈法爾,法蘭西斯·海曼繪 (1762)
在1688年至1689年光榮革命的標準「輝格黨」版本中(1681年排斥危機結束時,柴爾德就已經在挑戰這一版本)這場革命代表著新教價值觀和議會主權對反傾向天主教的專制主義在國內與地方上的勝利——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相左。對於一些修正主義學者來說,如波考克,商業秩序的概念在17世紀80年代幾乎沒有發揮作用,因為城市的概念仍然根植於新馬基雅維利式公民人文主義概念,它涉及公民士兵的家庭美德。最近史蒂夫·品克斯提出了一個「新輝格派」的觀點,認為光榮革命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有許多論據——17世紀80年代,輝格黨主張以勞工為中心的價值理論,而包括東印度公司董事約西亞·柴爾德爵士在內的托利黨人,則倡導以土地為中心的理論——為了抵制法國的現代天主教和專制主義的現代性。雙方必須用「現代」和歐洲的術語更全面地闡明他們的政治計劃,他與詹姆士·羅賓森(James Robinson)一起辯稱,這種向政黨政治的轉變推動了一項經濟現代化的計劃,該計劃與革命後出現的國家和議會機構息息相關。然而,這淡化了16、17世紀在倫敦所發生的事情具有的全球性,使現代成為一個相對局部的現象。
在17世紀的倫敦,那些第一次試圖對「現代」提出尖銳突破的人,常常認為自己提出了更普遍、更抽象的主張,就像牛頓在1687年發表的【原理】序言中,用現代科學的概念反對古代科學的概念。這本書的一個觀點是,從16世紀40年代到17世紀80年代,在倫敦出現的「現代早期」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晚期的「現代早期」,最早期的「現代早期」不僅出現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而且出現在明朝、息斯曼土耳其、薩法維和莫臥兒王朝。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建議將帖木兒在蒙古帝國覆滅後在撒馬爾罕進行收集活動(1370—1405年),作為亞洲「早期現代性」的一個起點,同時提醒說,這樣的論述可能會使這一概念超出其含義範圍。倫敦從18世紀,尤其是19世紀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也是C.A.貝利(C. A. Bayly)提出的「現代世界的誕生」的時期,以及倫敦對清朝、莫臥兒王朝,甚至是薩法維王朝和鄂圖曼帝國的成功霸權,都可能僅是遲來的結果。這並不意味著歷史學家應該簡單地描述「多元現代性」和文化分流。這種非線性的、分散的策略似乎經常是為了避免轉譯問題,並且無休止地增加例外主義,這有點像培根的奇異點。在這一點上,人們能夠從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那裏得到啟示,把「現代」這一概念完全拋棄,認為它是某種不可避免的自然與社會、偶然與本質的混合體,來自對當前成功的非常有限的看法,這是很有誘惑力的。
但是,當以政治主權、法治和訂立契約的自由、思想和資訊的自由交流以及一種可驗證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可導致關於真理的持久主張)來定義「現代」這個概念時,它仍然具有廣泛的跨文化的普遍意義——這一系列思想經常被描述為啟蒙運動。為了理解這些實踐具有的深刻的可譯性,這些實踐在一些人看來甚至是「自然法則」,需要重新構建對17世紀及「現代」出現的歷史理解,以揭示全球化行程導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而不是局部的輸出以發揮主導作用。任何對「現代早期」的描述都必須是多中心的。從巴黎、聖彼得堡到北京和江戶,這些政治首都都加強了轉譯工作,以理解和整合正在出現並不斷變化的全球交流模式。這種交流模式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地方層面的——當地的、區域的特別是城市的,是全球化的歷史遺址,是多條全球路線交會的地方。
雖然單一的民族國家可能試圖透過語言的統一來掩蓋轉譯過程,進而「想象」一個社群和一個連貫的地方史,但現代早期的全球城市創造了口譯和轉譯文化,其基礎是透過人際網路在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之間進行跨語言的交流所需要的復雜技術和工具。在塞爾登和格勞秀斯對海商法構成的不同立場中,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試圖將相互承認過程描述為單一的、連貫的、理性的事業時,所出現的矛盾的外在表現。概念上的困難在帝國主義盛行時期再次出現,這與西利(J. R. Seeley)對英國以外社會力量的吸重力的強調和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對市場和原材料的資本主義推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戰」後,阿瑪蒂亞·森從對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的創傷的理解中,歸納出了關於建設能力和實質性自由的鬥爭,這與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提出的君主例外幹預的演繹策略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他來說,全球化是亞歷山大六世的【神聖命令】(Inter caetera divinae)和【托爾德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年)制造的帝國的盛會,尤其是拉丁人的盛會。為了避免格勞秀斯、霍布森或施密特提出的陳詞濫調,這些陳詞濫調在20世紀已經被證明是極具破壞性的,因此需要一種比較的轉譯方法,這種方法往往與把全球劃分為東方和西方、歐洲和中國以及不同的民族國家的敘述背道而馳。倫敦之所以成為一個成功的城市,不僅是因為它在英國、歐洲或大西洋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還因為它參與並被印度洋和東亞創造的經濟、政治和知識的新模式所塑造。
從17世紀晚期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約西亞·柴爾德爵士對「新教倫理」的理解中,可以看出這種方法在揭開歷史行程的神秘面紗方面的潛力。約翰·洛克從卡羅來納和大西洋的視角來理解全球力量,威廉·配第透過對愛爾蘭的調查做了同樣的事情。相較於洛克和配第,柴爾德幾十年來一直在閱讀東印度公司信件中的「印度墨水」(India ink),他對全球力量特別是亞洲力量對倫敦的影響印象更深刻。很難想象還有類似於柴爾德在1681年發表的論文,柴爾德在文中提出完全反韋伯主義的觀點,他試圖自相矛盾地宣稱「東印度貿易是所有對外貿易中最具民族性的」。他試圖表明,倫敦並沒有透過在貿易和商業方面輸出自己的新教價值觀而取得成功;相反,由於倫敦與東亞的聯系,新教價值觀已經出現並變得一致。
柴爾德對因果關系的逆轉是他的論文中最引人註目的地方。沙夫茨伯裏伯爵等第一代輝格黨人對之後的光榮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相信「貿易在新教國家繁榮,因此,新教是我們貿易與航海獲得巨大進步的原因,而不是東印度群島的貿易」。就像太陽繞著地球轉的概念一樣,這是一種常識性方法,常常得到一種神學上連貫的世界圖景的支持。然而,柴爾德認為:
首先,貿易的大幅增長,並不是新教的一貫正確的結果,因為這並不是在所有的新教國家都能得到證明。但無論哪個國家的東印度貿易增長了多少,它在其他對外貿易和航海中的增長都是成比例的。其次,承認中國對新教的改革是中國貿易和航運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現在很明顯的是,我們的貿易和航海的增加,在上帝的庇佑下,是保護和維護我們新教的一種偉大的手段。對外貿易產生財富,財富產生力量,力量保護我們的貿易和宗教,它們交互作用,互相保護。
被韋伯定義的「新教倫理」或「資本主義精神」,並沒有創造貿易和航海;相反,貿易和航海的興起、新教的懺悔勝利,以及後來議會民主的出現,都是由於與亞洲關系的發展,特別是與印度洋和南海的貿易體系的發展。柴爾德的論點對於在「我們的」價值觀和「他們的」價值觀之間進行區分沒有留有余地,但這種區分在18世紀和19世紀不斷地得到重申。這本書已經表明,在英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轉折點——16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早期對新教的定義;16世紀80年代、90年代,與西班牙之間的決斷;17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對荷蘭的商業、法律和帝國戰略的抵制;17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英國「專制主義」與帝國君主制戰略的出現;最終,在光榮革命爆發前的幾年裏,大量的全球性努力投入轉譯過程,顯然幫助解決了當地語言與英語的爭端。倫敦人會轉譯,並且他們不會僅做轉譯。交換發生了,轉譯實踐也得到了發展,書籍被刊印和轉錄,這些行程的蹤跡,有時也包括人們本身的發展,都會追溯到倫敦。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會有一些人工制品保存下來,就像塞爾登地圖,暗示著這個過程的復雜性和參與的人口的範圍之廣,數以百計的其他文本和物體已經從記憶中消失。但在檔案館裏還有許多這樣的故事。還有什麽更好的時機來努力呈現這些集體的、合作的、相互信任的、經常是暴力的勞動者為建立全球交換網路而做的工作呢?還能在哪個更好的時代去在一本書、一幅地圖抑或一場遊戲中尋求歷史的意義呢?這些事物都曾在世界各地流傳並被保存了數個世紀,希望有一天,其中的任何一個事物都會重生並被轉譯。
(本文選自【倫敦:塞爾登地圖與全球化都市的形成】,[美]勞勃·巴切勒著,於振洋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