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林奕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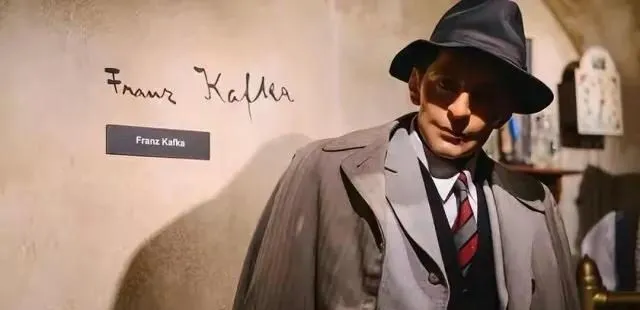
卡夫卡像
一
殘雪將審判一書的核心理解為兩種意誌的對抗,其中的「兩種」之意並非指K和某個具體的人,而是象征性地指向人的內部和外界力量。故事開始的情節就是在承接這兩種意誌的對峙。我在對【城堡】的初解中說過,卡夫卡就擅長制造矛盾使得人物關系被迅速地建立了起來,因為這兩種狀況也就是卡夫卡在現實中的所感。現實中社會關系的復雜荒誕已經超越人心感知的最大敏銳程度了。由於卡夫卡是讀過尼采作品的人,所以他很清楚要用什麽來抵禦這種社會關系的進擊。於是他把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創造成一個幾乎與小說情節中所有其他人物都有矛盾或者是對抗的人,審判中的K與他的叔叔亦然。面對寓所突然闖入了來針對自己的陌生人——自詡自己接受了來自上方莫大的權力來逮捕K的捕手,K非常不屑,因為他漠視了他們上方的權力。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權力顯然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了久也很快就會崩潰,這就是卡夫卡制造K無罪受捕的原因,否則對方是有理由來逮捕他的,也就是他們上方的權力與他有了直接的聯系,K沒有理由去拒絕它。
然而,與K理解相反的是,從捕手到監督官——從上至下都認可了K的受捕的合理性,而面對K的反問,他們不是回避問題,就是試圖搶占邏輯上遊。監督官面對K的請求和解,他不但不嘗試去緩解關系——即便事態已經發展到了多麽嚴重的程度,反而對他說,你把一切都看得太簡單了,你應該對此感到絕望。從這種角度看,監督官的形象已經變得十分嚴肅,他的身份已經開始脫離了實在的狀態,變成了人性中恐懼的淵源——如果一種意識已經陌生到任何人都看不清它,那麽它帶給人帶來的直接印象就是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可接觸的深淵,【城堡】中試圖表達的就是這一點。這種情況在意誌對抗中扮演著十分微妙的角色,因為說不清這種情況是會制止這種對抗進一步發展下去,還是反卻使其深化。於是K處於一種半和諧的狀態,他的名義上還處於被捕狀態,但是他的人身自由暫時得到了解放,這但這勢必會引來更加嚴重的後果。
K獲得者這種至少是被賦予了的人身自由,那他就承認了對方對他的權力——至少在這段自由期間內——是合理的。K從監督官那裏獲得的參加初次審庭的時間是星期日,而庭審地點是在一個相當偏僻的位置,這讓人或許會聯想到這些審判機構帶有象征性的宗教特征。相比於【城堡】而言,卡夫卡為審判機構的形象保留了一定基礎。在到達庭審地點之前,K一直與這個機構強大的陌生性與虛幻性進行斡旋,我們從一段對話中可以看出:
「不過最後他還是踏上了最開始看到的那段樓梯,腦袋裏同時回響起看守威廉姆曾經說過的話,法律是由罪行所牽引的。既然如此,預審調查室肯定就在K隨意挑選的這處樓梯上面了。」
在任何讀者看來,這段話多少都有點唯心的成分,但事實是,審判機構的形象只不過是K內心的深度幻想的一個側面,就好比【小徑分岔的花園】裏,即便可能性在時間中無限地分岔,但我們還是只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特定的一種。說到底審判機構的任何形象或者性質都是依K而定,它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極力的定性。
然而,K找到了庭審現場之後,他發現,庭審的規模不過如同一次小集體會議;庭審的地點也十分令人尷尬,是在一個閣樓內。卡夫卡就透過特意去弱化恐懼物件的現實狀態來制造出可以無限延伸的恐懼,因為現實呈現的審判機構露出水面的部份極其有限,而在水面之下的機構就會像冰山下部一樣龐大——最可怕的是,還是它們還可能只針對你一個人,只不過其暫時被對方的意誌所掩蓋了。
K在庭審上措辭激烈且尖銳地批判了預審法官和可能的高級法務人員的低價作風,但在發言過程中,幾乎底下的所有的議員——包括台上的預審法官——都默不作聲。這種情況往往帶給演說者的打擊是最大的,因為他們忽視了K的針對他們的意誌,或者說是有意以沈默對其進行否認的。K面對這種否認,他不能再依靠思想為自己辯護,因為對方已經沈默了,並將始終保持沈默。在K的發言過程中,台下有人帶頭進行喝彩,其他一些人(不是全部)才發出些動靜,這表明K面前展示出的是虛假的、經過偽裝的,這更給他的處境雪上加霜。末了,整個庭審過程中,一言未發的預審法官——他還被K當眾諷刺過——立刻站起來追隨K出門,並對他說,或許你此刻還沒意識到,就在今天,你主動剝奪一場審訊調查本應給逮捕者帶來的好處。現在K的困境就在於,他改變不了任何東西,因為他的意誌一直處在這個抽象的、虛幻的權力機關的強權的壓制之下,他根本進行不了反抗,盡管離開之前,他對預審法官反擊道,他們所有人都會在K的行動下得到法律的制裁。
二
K的叔叔得知K受到指控一事後,他帶K去見了自己的一名律師好友。K並不認為他的案子已經嚴重到需要找律師幫忙了,因為他是被無罪指控的,如果反而去過分重視它的話,就意味著連K至親的人都承認K是有罪的,至少是犯下了什麽嚴重的過失,從而導致K的刑事訴訟。K在律師分析案子的整個過程中,都是和他的女兒萊妮在一起。當然K即便有外人的輔助,情況也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每況愈下,向著更壞的方向發展。律師下面的還有一個委托人叫布洛克,是一個商人。他向K透露說,律師的接手並沒有使案件的情況得到多大改善,然而律師一再強調,他為商人打的是一場多麽艱苦的戰鬥。這也引出了後文K希望去解雇這個律師。這其實也是很微妙的一點,如果讓K獨自面對這一切,成功的可能性或許反而更大,一旦有了外界力量的加入,這種可能性反而就不可企及了,因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不可預知的個體上就是一種相當冒險的做法,還有一點是自己的權力被這種方式約束了,律師承擔為K擺脫這個訴訟的任務的同時,原本屬於K的對此事的主導的權力就轉移到了律師的手中,現在他更可能地會被事實左右了。
K回到自己的銀行辦公室後,他經一個工廠主的介紹去了一個畫家那裏。這個畫家說自己是為那些法官畫像的,自己也和法院有所往來。K對畫家說,我的無罪並不能讓審判變得更簡單。畫家也對K說,一旦有人讓K強制性與法院產生聯系後,K無論如何都沒辦法進入無罪釋放的結局了,因為他們總能找到理由——或創造出理由——讓K的名義下背負著罪責。他又對K說,如果我在這張畫布上並排畫出所有的法官,並且你在這幅畫面前為自己辯護,你獲得勝訴的可能性都比真實法庭上要高。
可誰知道呢,畫家本人也是K必須承擔的恐懼的一部份——畫家的住所就緊鄰著上次庭審地點,就連門口圍觀的女孩子也屬於法院的一部份。畫家說,統統都是法院的一部份。K這時可能已經意識到他必須與外界對立起來,因為外界任何人都受著某個強大意識的牽引,正緩緩向K湧去。現在不他不得不用手抵擋這一切了。
回到銀行後,K被委任去接待一位義大利客戶,要親內建他去參觀大教堂,可到達之後卻發現客戶沒來。他只身一人走進幽暗潮濕的教堂內部,他見到了教堂的神父,正當他在想神父應該是在做布道時,被他溘然叫停遲疑離去的腳步。他喊出了K的名字——他是監獄神父——所以對K的案件有所了解。此刻就如我所說,K的命運所面臨的嚴肅性已經處於了一個最莊嚴、最具有審視意義的時刻了,仿佛在遙遠的地平線後面、在遙遠的城市裏、郊野處正升起數萬種目光聚集於K的一身,正等待著他最終的結局。此刻我們可以猜到,那個義大利客戶一定程度上是受神父派遣的,小說的嚴肅性已經上升到宗教層面了——「在他看來,大教堂的宏大體量,幾乎已經要超過人類個體的忍受極限了」。隨後神父對K講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整部【審判】的焦點,卡夫卡曾把它單獨抽離出來作為一個短篇,篇名叫【在法門前】。我在前面說過,這時的審判機構已經類似於一個宗教組織了,不論是作為法的守門人,還是試圖進入法的大門的人——前者的義務似乎於試圖入門者相連了,因為他守的大門是專為專門為試圖入門者而設的,可是他又不知道試圖入門者應該在什麽時候進入大門,因此試圖入門者到死都沒有進去——守門人的義務與他的事實所為相違背,守門人可能只是站在法的大門的背面認為,入門人是無論如何都進不去的,因為裏面有一層比一層更大的障礙,裏面的守門人也有一個比一個更有權力,而試圖入門者的目光卻能透視著所有的門,看到法的中心射出的永不熄滅的光線。從這一點層面上看,守門人才是那個真正被蒙騙的人,他已經被自己義務所束縛住了,不能離開法的大門;而試圖入門者是自由的,但他唯一的自由就是通向法的門內,尋求法的解釋,但現在他連這點都無法滿足了。K的案件的審判結果會從大街上隨便哪個人口中說出來,他的命運的審判已經不再是僅由整個審判機構來操控了,它將由任何自然人操控。現在,K必須忍受這件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恐懼感。
幾乎是在K的31歲生日之際,他被兩個不太像是刑事執行人員的刑事執行人員帶到了郊野,接受了死刑。諷刺的是,他在被逮捕的那一天,也正是他的30歲生日,在這一年內,他始終都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麽罪過。故事的最後。K從一棟樓的頂部看到一個俯出窗外的人。他想,那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心人,一個同情者,一個想要提供幫助的人?僅僅是人類個體,還是全人類呢?此時K心中滲透出的交織的希望和絕望,已讓被救贖的可能性變得深沈而博大了。
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