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太阳与梵高的向日葵
「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这首举世闻名的【我的太阳】经由帕瓦罗蒂的演绎传到我耳畔时,我早已有过我的太阳,而且不是比喻,是真正意义上的那轮太阳。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在「红太阳照边疆」的岁月里,在小学的第一堂美术课上,小小少年用铅笔为并不很圆的太阳以及毫不对称的光芒涂了上黑色。老师看到后并没有呵斥,而是耐心地问:「你每天见到的太阳是黑色的吗?」每天温暖我的太阳当然是金色的,但我只有黑色的笔。老师微笑着说,那就不要涂色,不能再这样画太阳了。
瞧我多么无知。自第一堂美术课遭遇滑铁卢之后,我再也没有画出过与所描摹之物有一丝相像的东西,说明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天赋。看着同学能够把向日葵、牛、羊都画得那么逼真,我十分羡慕。到了初中,终于明白,我连立体图形都想象不出来,想画成图画,这不是天方夜谭么?有精神动力,但缺乏智力支持啊。不过,这倒更加唤起了我对绘画的好奇。虽然我根本就不懂,但人有我无,便想时时看上几眼,艳羡人家的独门绝技,附庸风雅而已。
「画法稚嫩,画上有黄色的太阳,一团团卷曲的云雾,画面上方一隅有两只海鸥飞过一艘四方形的船,船上有四个铅笔画的小圆圈。」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在【无极形】中塑造的这个十岁女孩显然比我有天资得多,我老头儿应该仰望之。我常看到大人们在逛商场时将小孩临时寄放在游乐角,孩子们既可玩乐,亦可随意绘画。那些稚嫩的画作充满想象,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些童稚给我当老师绰绰有余。我外甥女零基础,学了半年就能画人物肖像,惟妙惟肖,令我惊叹。
日前去了一趟著名的大窑文化遗址所在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窑村,眼界大开。这里家家户户的墙上全是美术作品,却自称「涂鸦」。人物肖像、天空图景、老物件……装点着这个小小的村落。这是我第二次见识涂鸦部落,上一次是在台湾省台中市的彩虹眷村。一位老军人在那个地方的墙上画满了彩虹线条及动物、花朵、人物,构建起了一个童话世界。结果,整个村子成了旅游景点。这位老人显然不是画家,连画友甚至都算不上,作品是名副其实的「涂鸦」,画法非常稚嫩,像是儿童随意所作,但色彩斑斓,让人眼花瞭乱,觉得新奇。但平心而论,倘使让我去画,我仍然不如人家。我连简笔画都画得走样,更别说照猫画虎。

如同有些人喜欢把装帧豪华的书摆在家中显著位置,以昭告别人自己有文化一样,我也将梵高的向日葵烧制在了一块玻璃小墙上,以示我这个画盲知道这位绘画大师及其作品。其实,我对这幅画根本就不懂,只是为了装样子,生怕别人以为自己不高雅,虚荣心在作祟罢了。
在这种虚荣心的驱使下,我叶公好龙,游走于各种美术展览场所,在上海博物馆参观了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画展,见到了高更、莫奈、梵高、塞尚、雷诺阿等著名画家的传世作品,据说是真迹而非复制品;在浦东美术馆观看了现代派画展,一窍不通,毫无感觉;在内蒙古美术馆见识了当地画家的不同画风的作品,只觉得画得挺好,无法用专业术语进行评判。

在各种参观中,我只是一个打卡者,立此存照而已。有些带着孩子的大人,边看边讲,头头是道,行家一般。我悄悄跟在人家后面,边看边听,倒也收获颇丰。此时,我这个小白慨叹学识不如人家,人家虽非高山,但足为我师,也令我仰止。
我还买了很多画家写的书以及描写画家的书,时时翻翻,想接近人家的神奇世界,结果始终站在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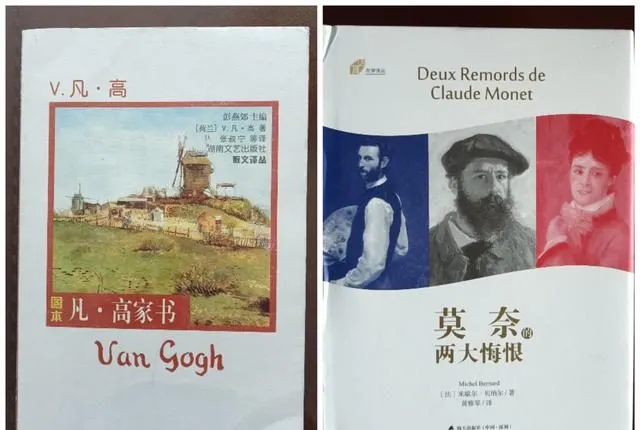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说,「世界上所有的美术馆都挤满了人,就像从前的动物园一样;有爱看新奇事物癖好的旅游者凝视油画,仿佛这是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这位大师阅尽人间沧桑,一下子就看穿了像我这样看星星的瞎狗。既凑热闹,又装模作样,还怕露馅。结果,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我们的「装」被戳穿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说,「白天我去参观画展,久久地在卢浮宫的画廊里游荡。」她也不是画家,但生在法国,每天在卢浮宫徜徉,谁能说人家是在附庸风雅,更何况人家是哲学家波伏瓦呢!
上海明珠美术馆举办【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画展时,我远在天边,否则一定会前往领略一下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在绘画方面的高超造诣。倘使生命中真的有这样的参观,那我就可以说,这次中文狗可不是附庸风雅,而是在扩充专业知识。
我虽是美术的门外汉,但周围却不乏有绘画天赋者。一位暌违已久的朋友用彩色铅笔画各种水果和鲜花,在抖音上晒。当得知人家系初学时,我羡慕不已。呼伦贝尔那家我曾工作过的单位竟然有两位画家。我离开后,我们先后在同一个条线工作。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未向大师索画,人家更未曾表示有兴趣赠我大作。倒是在与两位大师交往的过程中,我赴了数不胜数的饭局,喝了不计其数的啤酒,也领略了一些他们身上氤氲的艺术气质。

在上海的田子坊、豫园、南京路到处都有为游人画像的摊点,画漫画像、肖像画,立等可取。画师皆浓发长髯,年轻有为,极富艺术范儿。我曾观摩数次,每次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人家脑袋与我的大头结构不同。稍稍觑你一眼,即能抓住你的特点,寥寥几笔,你就跃然纸上。于专业人士而言,这或许只是雕虫小技,但在我看来,这已胜那个黑太阳少年千万倍矣。
文学与绘画本来相通,有人样样皆精,有人独擅一门。对通才我向来钦慕,就像活跃于【中国诗词大会】的康震教授,专业乃中文,但画得简洁传神,口才亦相当了得,小我五岁的这位陕北人是我心中的男神。
其实,我大学时的老师班澜先生更是我心中的老男神。老师诗书画俱佳,吟诗作文皆信手拈来,亦常常【班澜说画】【自说自画】,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遗憾的是,作为学生,我未得老师学问之万一,惭愧啊!有文友读了我的一些作文后,称我为班老师的高足,我真是愧不敢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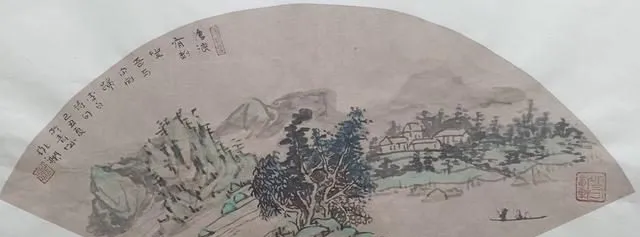
老师学富五车,艺作等身,八秩挥毫著文不辍,而我略识之无,粗通作文,就凭我在参观画展时的那个无知样,仅可算先生之劣徒,岂敢妄称高足,以辱班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