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知識界,動蕩的全球局勢、昔日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仍在持續激發著深層次的政治無助感。與此同時,有關西方政治制度積累的多種實踐經驗、以及知識社會學的諸多建構都在助推一種內省的思潮。人們驚訝地意識到,自柏拉圖以降的政治理論的宏大傳統正在被擱置,越來越多的學術爭鳴更傾向於回顧過去。當所謂的「科學」預測逐個走向幻滅,就連今天的政治哲學家似乎都不再寄希望於建立一個既可解釋當下、又能指向未來的新概念體系。在政治理論家朱迪絲·N.施基利(Judith N.Shklar)看來,如今我們已經沒有政治理論,只剩下文化宿命論。
早在1957年,這種擔憂就推動施基利完成了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後在此基礎上,施基利做了大量修改,寫作了【烏托邦之後:政治信仰的衰落】一書。這部「社會苦惱意識」的診斷書全方位地展現了一位初出茅廬的政治思想家的診斷能力,她在書中旁征博引探討了浪漫主義式和基督教式社會絕望的由來,並對自由主義相關思想的衰落作了闡述。這些共同構成了自啟蒙運動以來,一部「理性政治樂觀主義的衰落史」。時隔半個多世紀,這版作品譯介至中國。而施基利當初斷言的這種無助感有增無減。施基利也不認為這些聲音就是「錯誤的」,她真正擔心的是「它們未能對自己如此反感的世界作出解釋」。
盡管該書無意為彌漫至今的社會情緒提供某種解釋,但回望「政治信仰的衰落」之路仍為我們開辟出一條理解當前境況的新路。它最終試圖重拾的是對思考與質疑的推崇,而這與當今時代的每個人,息息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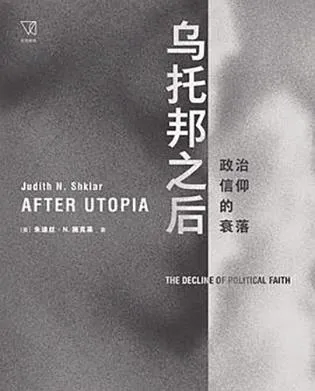
【烏托邦之後:政治信仰的衰落】作者:(美)朱迪絲·N.施基利,譯者:王籍慧,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
阿貝爾·科內利烏斯的散步
阿貝爾·科內利烏斯(Abel Cornelius)是德國某所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有相當可觀的薪金,和妻子兒女住在一棟年久失修但雅致舒適的別墅裏,過著昔日中產階級的生活。在吃過晚餐(意大利沙拉和塗了奶油的黑麪包)後,教授一般會去漆黑的冬夜裏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並趁機活動一下。今日,他那一對經常「貧窮」打扮的兒女要在家中舉辦派對。臨走前,他看到大家夥兒怪模怪樣地摟在一起,姿態新穎,臀部順著某種神秘節奏一扭一扭。而他心愛的小女兒居然和舞伴一起暈頭轉向,神經質地對他顯出不耐煩,最後竟疏遠起他來。
盡管如此,歷史教授在散步時總要在腦中捋一遍明天的課,他將講授跟不上時代的菲利普如何絕望地與新事物以及歷史潮流作鬥爭,與日耳曼人追求自由與個性的銳不可當的勢力作鬥爭。他還準備講頑固的貴族如何反對進步和改革勢力,他們這種掙紮既為生活所唾棄,也為上帝所不容。可是,歷史教授卻痛恨眼下號稱「進步」的改革,他覺得這種改革不合章法,甚至違背歷史。他的心實際上屬於過去,屬於無限的時間和永恒的情調。過去已死,而死亡卻是虔誠和永續性的根源。正是這種對永恒的認知,才使他沈湎於對女兒的愛中,讓自己不致受到狂妄時代的影響。他內心不得不承認,他對女兒的迷戀與死亡有著不解之緣。
阿貝爾·科內利烏斯其實是虛構的人物,他是杜文·曼(Thomas Mann)的短篇小說【顛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Unordnung und frühes Leid)中的男主人公。按照曼的設定,還可以為科內利烏斯的畫像再添上幾筆: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威廉二世的德意誌帝國的衰落;他反對民主政治和進步史觀,尤其是法國人伏爾泰和左拉式的;他在意內心的秩序和舊世界的正義感,反對新的政治、文化、道德和語言環境中價值的缺失和相對主義的溢滿。然而,科內利烏斯並未明確提出政治和倫理上的主張。他是歷史教授,他嘗試理解當下發生的事,他需要時間稍長一些的棱鏡。他在散步時不由得想起「歷史」的本質,他覺得,只有正義才是歷史的真諦。正義是憂郁,它暗暗地與愁苦和前景無望息息相通。
這種憂郁的苦惱意識誘使歷史教授去思考變革中的社會的過去與未來,也正是這種苦惱意識催生了施基利的【烏托邦之後:政治信仰的衰落】。這本出版於1957年的著作是施基利完成於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她也因此在出版前一年獲得美國政治科學協會頒發的伯克黑德獎(Birkhead Prize)。這部「社會苦惱意識」的診斷書全方位地展現了一位初出茅廬的政治思想家的診斷能力,她看起來毫不費力地穿梭於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脈絡中,對近三十年來的思想著作旁征博引,在一連串衰落-修復-失敗-修復-失敗的問診(盡管不是譜系學式的,也並非沒有矛盾之處)過後,她似乎已經絕望地意識到,倘若政治信仰缺位,政治哲學消逝,那麽市民社會的烏托邦也將不復存在。因此,我們才在診斷書的結語部份看到,她為治療現代社會的苦惱意識開出的藥方是多麽無力:一種有根有據的懷疑主義是目前最明智的看法。僅僅因為這個藥方比文化絕望和宿命論更可靠,在經驗上也更無可非議。
什麽是「苦惱意識」?黑格爾曾經無比敏銳地定義過,這是對過去的信念失去所有信心的「疏離的靈魂」(alienated soul),懷疑主義使得它不再抱有幻想,但它卻無法在當前或未來為其精神渴求尋得一個新的家園。阿貝爾·科內利烏斯的歷史課堂諷刺了舊貴族的抱殘守缺和對歷史規律的置若罔聞,而在面對新興的民主政治時,他卻更懼怕新事物帶來的社會與內心的失序,並希望在歷史中尋找永恒之物。
可問題在於,歷史學家科內利烏斯能成功嗎?過去的歷史真的能為未來提供永恒的價值嗎?在施基利看來,一切都要從啟蒙運動談起。

愛德華·蒙克【呂貝克港及霍爾斯坦門】(Lübeck Harbour with the Holstentor)
歷史不是生活的導師
作為一場思想革命的啟蒙運動為歐洲人帶來以下啟示:人類的道德和社會境況在不斷改善,人可以依靠自己及其所處社會做任何想做之事,利用理性構建一個理性社會。這種基於人類理性的樂觀主義便是施基利認同的政治哲學的烏托邦基調,在她的思想史譜系中,它起源於柏拉圖政治思想的宏大傳統。過去和未來都在理性這裏交匯,宗教教義、道德準則、人的實踐規範和判斷都可以經由理性萃取出一個確定不變的要素。從此,未來是一個理性的、無限的歷史階段,理性將在這個階段中無限地展現自身、趨向完美。
基於這樣的認知,啟蒙運動的進步史觀成為思想界的陳詞濫調。在孔多塞那裏,歷史就是「已經發生的」和「還未發生的」,他帶著動人的信心。在理性的感召下,未來的歷史是擺脫「潮起潮落式的」自然規律的歷史,是一往無前的歷史,它掃清了危機、不確定和戲劇性的障礙。
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認為,18世紀中葉以降的歷史觀讓長久以來「歷史是生活導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的箴言失效。歷史原本是道德和政治的蓄水池,如今歷史能提供的僅僅是歷史,過去的歷史停止照亮未來的道路,人類的精神世界陷入幽暗。人類的經驗朝著未來無限擴張,那麽,歷史不僅不會重復,也不會押韻,歷史事件(res factae)和歷史敘事(res fictae)合流,最終變成了一種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不僅如此,法國大革命還告訴世人,在憲法尚未確定之時,歷史書寫就不可能開始。因此,啟蒙運動的進步史觀扭轉了人們看待過去的態度與立場,過去與確鑿的道德原則和價值標準逐漸脫離,成為一個個歷史事件和歷史敘事,還可能是學院裏的一個標本。
進步史觀的反彌賽亞主義讓未來變得無限可能(ad infinitum)。可是,這種「良善的」、「進步的」樂觀主義經不起突發的和戲劇性的倒退,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科內利烏斯教授可能是最敏感和最早幻滅的一批,而他憂郁的苦惱意識便是產生於這種「過去不蘊含道德和價值」(盡管他內心堅信)和「未來可能進兩步退三步」的懷疑和困惑。
浪漫主義及其失敗
第一個嘗試修復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思潮是浪漫主義。在以賽亞·伯林看來,浪漫主義發動的是攻擊。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間的矛盾與其說是施基利認為的詩哲之戰,不如說是兩種人的境況之間的差異。浪漫主義並非明確地反對理性本身,而是反對理性帶來的對人的碎片化的分析,自狂飆突進運動爆發伊始,浪漫主義就致力於人的整體性理念。他們呼籲一種新的看待生命的方式,即創造的方式。而理性所萃取的亙古不變的元素對浪漫主義者而言恰恰缺乏了創造性,這是致命的具有摧毀性的力量。
在這種理念的倡導下,自我表達成為人類最高的目的。「真假不在事物中,而在思想中」的亞里士多德理性傳統被「真理透過審美創造得以開啟和發現」的美學發現徹底顛覆。克爾凱郭爾走向的現代世界,要麽是美學的,要麽是宗教的。尼采毅然決然地支持藝術,支持悲劇性和早期華格納的藝術,他肯定生命,拒絕抽象概念的哲學。
在施基利的行文中,是浪漫主義在啟蒙運動那裏發現了社會中的苦惱意識。荷爾德林在他的書信體小說【海伯利安】(Hyperion)中描寫到,主人公自希臘回歸後發現整個德國民族被撕成了碎片,那裏有工人、教士、雇主和雇員,就是沒有人。每個人都不得不盡心盡力地投入到他的職業當中,並不得不扼殺掉他內心任何與他的確切頭銜不相符的事物。而與此同時,席勒也註意到,作為個體的雅典人要比現代歐洲的個人出眾得多。就是這種後來被定義為「異化」的東西讓人疏離於社會的充分意識得以顯現。進步意味著社會和生產力的進步,是作為整體的人類的進步,而非個體的發展。關註個體自身的浪漫主義拒絕政治,他們拒絕討論政治,而且反政治。政治意味著自我的喪失,當一位詩人參加政黨,那就意味著他已經不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了。

愛德華·蒙克【弗雷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施基利認為,浪漫主義的悲劇和失敗就在於,作為文化力量的浪漫主義或者說「集體浪漫主義」不得不面對政治、對抗政治,最後甚至想要改變政治。從此刻起,個體浪漫主義就終結了,浪漫主義者開始企望共同體和民族精神的構建,於是,浪漫主義的第一個偉大時期就以這種不光彩的方式落幕。但它挖掘出來的社會苦惱意識卻改頭換面地在存在主義、自我超越的哲學、歷史絕望、美學無政府主義、對個性的崇拜和對大眾的厭惡中幸存下來。
殘存的浪漫主義和愈發壯大的苦惱意識在二十世紀的思想家和作家那裏達到了巔峰。但施基利的思想史脈絡剖析在這裏發生了極大跳躍,她將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張力還原為上帝的缺席,因為最高價值的終結和作為一個融貫整體的世界的瓦解,所以二十世紀的思想家,包括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阿倫特、薩特、加繆、加塞特以及荒誕派詩人都要為上帝死後的世界尋找真實的自我,也就是在倫理上如何過沒有上帝的生活。在薩特看來,本真意味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處境,並完全置於其中。我們拒絕外部的價值,同時也拒絕他人的提供,不管他人是否出於好意。因為接受被提供的價值這一行為既不誠實又摧毀人的主體性。對於社會而言,這種本真性哲學的結局或許就是加塞特名著的主題——大眾的反叛。在加塞特那裏,大眾的崛起意味著平均化時代的到來,加塞特毫不諱言,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平庸的心智盡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把它強加於自己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在這些浪漫主義者看來,大眾都是平庸的、沒有精神生活和不會思考的新非利士人(編者註:非利士人在【聖經】中代表那些有信仰但缺乏道義之人)。那浪漫主義者在這樣的時代該做什麽?施基利的回答是,保護自己的完整性不受相敵對的世界的侵犯。
信仰的衰落
疲憊不堪的浪漫主義的另一條道路是投入天主教的懷抱。但施基利開宗明義地說,依靠基督教信仰來彌補苦惱意識絕無可能,因為基督教也同樣感到與現代歷史的疏離。中世紀的天主教在幾輪巨大變革中被擊得一敗塗地,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二十世紀上半葉各種殘酷的戰爭和政治行徑都讓它的整座神學大廈、教會建制和神學政治化傳統煙消雲散。尤其是二十世紀初的事件讓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們相信,歐洲會因為無宗教信仰而消亡。
施基利認為,這些基督教宿命論者無法為現代社會再提供政治哲學的理由還在於,他們關於現代世界的可怕結論背後都是一種極其古老的歷史解釋方法,即每個社會事件最終都建立在某種特殊的宗教信仰基礎上。也就是說,要理解歷史,只需找到將每個政治行為直接與一種信仰綁在一起的因果鏈條。當然,有比這種中世紀的古老解釋更高明的政治哲學,比如卡爾·施米特透過論證神學上的偶因論起源來展開他的討論,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學】將後中世紀的政治思想都當作斯諾替主義的產物來研究。在政治行動領域,法國大革命通常被視為新教的一種表達。
這麽看來,一切西方政治問題最終都是神學問題。因此,一種有趣的邏輯推演就顯得順理成章,即在基督教衰落之後興起的種種事件、改革、革命和思潮,都是通往極權主義的必經之路。
如前所述,施基利在一開始回答基督教能否彌補啟蒙運動的缺陷,能否為現代社會提供新的政治哲學時,便給出了確鑿的否定答案。在現今社會,沒有什麽能夠為宗教復興提供實際的支持,而沒有新的宗教信仰,西方文明將無法從當今的遭難中幸免。施基利在此援引了天主教歷史學家道森的話,有趣的是,這段話體現了濃厚的啟蒙運動史觀:「沒有人知道西方將向何處去,不存在我們能夠借以預測未來的歷史規律。」

愛德華·蒙克【法學】(Jurisprudence)
新世界的藥方
在本書的最後部份,19和20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思想輪番登場,我想,在施基利的寫作框架中,這些輪番登場的思想最終都成為一具具遺骸,成為她論證「政治信仰衰落」的佐證而已。無論是伯克所代表的保守主義的挑戰,還是自由主義的不自信與擔憂(愚蠢與柔弱),抑或是費邊主義和社會主義,施基利寫作的時代無疑都業已證明了它們的失敗。它們唯一的貢獻在於反復提醒世人,我們生活的社會、我們的處境和我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政治生活決定,與此同時,我們並沒有很好地將啟蒙運動以來的政治經驗整合成一幅合理且行之有效的理論圖景,整個政治思想的停滯讓人類社會無處可去,只能不停地盤旋在原地,看著社會的苦惱意識不斷累積。
讓我們回到冬夜散步的歷史教授。他對當下民主政治帶來的黨派分立、劍拔弩張感到厭惡,又對歷史與歷史發展的本質感到困惑,他叩問自己「正義到底存在不存在」。他說,這真是一門擾人思緒的學科,令人沈思默想啊!科內利烏斯教授的感嘆與施基利開出的藥方——有根有據的懷疑主義——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思想是最高的美德。
無論烏托邦是否坍塌,思考它就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少許的懷疑,幾盎司的不輕信,和少量把思想搞清楚的嚴格訓練(胡適)。
撰文/郭逸豪(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所)
編輯/申璐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