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嚴寒黑夜,
人生好像長途旅行,
仰望蒼空尋找出路,
天際卻無指引的明星。
——【茫茫黑夜漫遊】扉頁題詩
在塞利納的【茫茫黑夜漫遊】中,主人公巴達繆是第一人稱敘事者,但作者在再版卷首的題辭中卻聲稱敘事者不是他本人,這部小說完全是虛構的,描寫一個年輕人的經歷,屬於歐洲傳統的漫遊小說。小說發表於1932年,人們當即欣喜地發現,法國又出了一個天才作家,無情地抨擊文明社會。而說到漫遊小說的地域範圍,則是由歐洲一代代的作家逐漸擴大的,從小癩子在一個城鄉的遊蕩到堂吉訶德在一個國家的遊蕩,再到巴達繆的全球遊蕩,地域是擴大了,主題卻沒變,表現的都是世態人情,是「從生到死的旅行。」
路易·費迪南·塞利納(1894-1961),法國小說家、醫生。當過商店學徒,一戰時入伍受傷。戰後入大學攻讀醫科,畢業後參加國際聯盟醫療調查工作。1928年在巴黎郊區市立醫院工作,同時寫他的代表作【茫茫黑夜漫遊】,該小說在1932年出版時震動法國文壇,獲雷諾多文學獎。
撰文 | 景凱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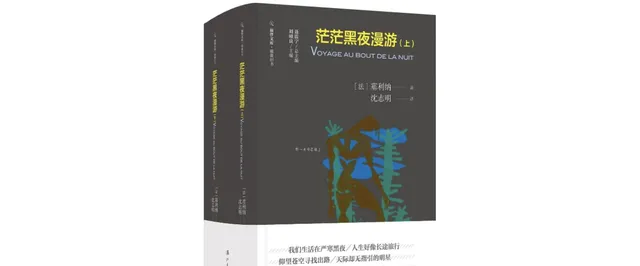
【茫茫黑夜漫遊】,作者:[法]塞利納,譯者:沈誌明,版本:漓江出版社 2020年2月。
一個無家可歸之人的世界漫遊
「我根本沒有想到,委實沒有想到,事情就這樣開場了。」這個不經意的開頭讓歷史時間退到遠景,突現出了個人時間。朋友約巴達繆在咖啡館見面,聊到正在進行的一戰,「我們坐在咖啡館裏一面用眼瞟著女人,一面侃侃而談,興高采烈,洋洋得意。」朋友慷慨激昂地談到愛國,斥責巴達繆的玩世不恭,但恰恰就是這個玩世不恭者看到一支法國軍隊路過,突然便加入進去,從此開始了他的人生旅行。
戰場上的巴達繆感覺自己像是置身在幾百萬瘋子中,從城鎮到村莊,部隊在茫茫黑夜中行軍,炮彈落下來,人像稻草般倒下。不久,巴達繆受了傷,被送回巴黎郊區醫院治療,因為害怕再上戰場,他開始裝瘋賣傻,得以前往北部非洲,住在熱帶蚊子成群的鐵皮房子裏,替歐洲的殖民公司收購貨物,非洲的惡劣條件促使他再次逃離莽莽叢林,雇用的黑人把他賣給船主當水手,劃船越過大西洋,來到美國紐約,一文不名的他走在曼哈頓的摩天大樓間,跟陌生人一起蹲在中央公園的地下室裏拉屎,此後他來到底特律,成了福特公司流水線上的一名工人。經歷了這段流浪,他最終又回到巴黎。

【茫茫黑夜漫遊】英文版封面。
關於巴達繆的家庭,他的過去,作者沒有做任何交待。隨著他浪跡四方,環境與場景不斷變換,遇到的人就像是生命途中的過客,陣亡的上校,護士勞拉,歌手繆濟娜,中尉格拉帕,妓女莫莉,都是一閃而過,就連巴達繆的母親在全書中也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她到醫院來看望受傷的兒子,哭哭啼啼,「好像一條母狗失而復得它的崽子。她大概以為擁抱擁抱我就能助我一臂之力,其實還不如母狗。因為她相信別人讓她來領我的理由,母狗則不然,它只相信自己的感覺。」
在內心深處,巴達繆是個無家可歸的人,他一出場就表現出浪子的氣質,不斷地逃離環境,對任何事都冷嘲熱諷,說話幾近惡毒。戰爭使他對一切英雄主義的言行產生反感,他憎惡這場戰爭,堅信平民百姓只是政治家們的炮灰,而大眾卻為愛國而狂熱,在軍人葬禮上又個個指望自己活得更長久。戰爭也教會他不相信愛情之類的鬼話,對所有遇到的女性他只有肉體的沖動,他從不隱晦這一點,就是說,他從不玩弄她們,都是你情我願的事,這種坦誠總是讓她們最後離開他。
我覺得巴達繆回到巴黎,真正的故事才開始。幾年以後,巴達繆完成了學業,成了一位開業醫生,住在巴黎郊區的朗西,在那裏,「塞納河簡直成了一條巨大的臭水渠。星期天和夜裏,人們爬上陡峭的河岸撒尿。男人們面對逝去的河水感慨系之,他們小便時獲得海員與海永存的感悟。女人們則從不沈思,對塞納河無動於衷。」那裏居住的都是底層人,鄰居整天打孩子,姑娘們私下墮胎,因無錢治病而死去。
小說的前半部都是巴達繆的旅途見聞,至多是他對社會的觀感。突然間,敘事的節奏慢了下來,小說後半部有了一個集中的事件。即使是描寫人的日常生活,一部小說也是要有密度,有戲劇性的。這是一個關於謀殺的故事。
他們中到底誰是瘋子?
巴達繆在巴黎又遇見了羅班松,不同於其他人,這個人物始終與巴達繆如影隨形,從法國戰場到非洲叢林,再到美國紐約和底特律,巴達繆漫遊到哪裏,他就會出現在哪裏,怎麽也甩不掉。實際上,他倆是天生的一對,互相之間實在太像了,說到玩世不恭,羅班松還要更加不在乎這個世界。為了擺脫生存困境,掙到一大筆錢,羅班松答應參與昂魯伊妻子的陰謀,在兔子棚安裝炸藥炸死她婆婆。
昂魯伊一家是巴達繆的病人,辛苦一輩子才擁有一棟房子,這使得昂魯伊常常在半夜突然坐起來,小心翼翼地診斷脈搏,擔心自己會突然死去,他的妻子卻是無憂無慮,除了整天對暮年長籲短嘆,就一心只想著攢錢。她極力鼓動巴達繆,讓他勸衰老而暴躁的婆婆去養老院,惹得老太婆破口大罵,這個老太婆對所有人都心懷憎恨,聽到鄰居孩子病亡,她就會感到特別愉悅。巴達繆理解羅班松發財的欲望,聽到這陰謀並不感到驚訝,覺得朋友幹這勾當也不失為一種進步。
他倆對人都沒有什麽好感,因而毫不在乎人類道德,生活本身對他們就夠不公的了,巴達繆決定隱瞞此事,他想:「勸導人們不要幹這等事的種種言論始終沒有起過作用。難道生活給過他們溫暖嗎?讓他們憐憫誰和憐憫什麽呢?為什麽要憐憫呢?他人?誰見過有人自動下地獄替代他人?從未有過,倒是見過讓他人下地獄的事情。」
結果卻出乎大家意外,老太婆沒有被炸死,羅班松卻不小心誤傷了自己的眼睛,大家決定把失明的他和半瘋的老太婆秘密送到圖魯茲一家教堂,在墓室裏看管骷髏。巴達繆也悄悄離開了朗西醫所,在一家劇院扮演跑龍套的演員。姑娘們在他周圍旋轉,波濤起伏,感覺就像在茫茫海上航行。時光飛逝,巴達繆最後一次看到昂魯伊是在他臨終的床上,他到底沒有活得太長久,他的妻子在病床旁一直惦記著取出丈夫嘴裏的金牙,哽咽著對巴達繆說,昂魯伊居然三十年來從來沒有告訴過她。
在去看望羅班松的途中,巴達繆陷入沈思:「我們念念不忘尋求幸福的嘗試,為此目的而逐漸衰老。我們落到今天的地步不是沒有花費氣力的,我們曾不斷使希望、衰退的幸福、熱情和謊言變得振奮人心,還要我們怎麽樣啊!……我們走進茫茫黑夜,起先驚慌失措,但仍想弄個明白,於是在黑暗中越陷越深。要明白的事情太多,而生命又太短促……」
幸運的是,羅班松已在墓室裏找到了這種「衰退的幸福」。他的眼睛逐漸好轉,還搭上了當地的姑娘馬德隆,協助昂魯伊老太婆招攬遊客來觀賞骷髏,賺了不少錢。羅班松開始對前程充滿幻想,他悄悄告訴巴達繆,等到結婚那天他才碰未婚妻,而巴達繆卻在暗地裏與馬德隆幽會,心裏嘲笑羅班松:「他寄情於永久,我則要馬上到手。」對他來說,這樣做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和責任。

電影【Louis-Ferdinand Céline: Two Clowns for a Catastrophe】海報。
離開圖魯茲,巴達繆在維尼一家精神病院找了個工作,老板巴瑞通靠著辦醫院發了財,他是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經常說出些人生哲理:「請記住我下面的這些話!有兩種瘋子,一種是普通的瘋子,另一種是受文明的固習所折磨的瘋子……我經手過許多這類過分自信的病人,而且他們的病因各異。總之,我認為高談正義的人是最瘋狂的!」在巴瑞通看來,這個社會聲稱追求科學和進步,但實際上已病入膏肓,毫無節制地奔向虛無。他不再滿足於平凡的命運安排,終於決定獨自出走,將醫院委托給巴達繆管理。
他們中到底誰是瘋子?這世界又到底誰是瘋子?羅班松眼睛痊愈後,有一天突然再也忍不住,將成天咒罵他的老太婆從墓室的階梯上推下去摔死,為了躲避馬德隆的纏結,他逃到巴達繆所在的精神病院,這個浪子犯下的唯一錯誤就是居然想要結婚,而不是逢場作戲,但他很快也就厭倦了。他和巴達繆畢竟是一類人,浪跡四方的他們不需要任何約束,他們的內心就像一棟空房子,裝不下愛情和家庭。
對於他們,所謂愛情也不過是性欲的借口,如果把它當真就愚蠢了。小說結尾,因愛情而失去理智的馬德隆找到了他們,在一次集體的外出尋歡後,她在盛怒之下開槍打死羅班松,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我周圍的黑暗太深邃了」
作者越寫越對這兩個厭世的朋友充滿同情,巴達繆既是故事的當事人,同時又是一個無情的旁觀者和刻毒的思考者。在醫院養傷時,巴達繆就對勞拉說:「一萬年以後,我敢向你打賭,這場我們看得了不起的戰爭將被忘得一幹二凈。」經歷了許多事件,他認為昂魯伊的妻子不比自己更壞:「雖說人在生活中不能上升,只能下降,但她卻不能下降到我沈淪的程度。對她來說,我周圍的黑暗太深邃了。」羅班達死後,他在塞納河岸看著清晨去上班的工人:「他們的背後依然是茫茫黑夜。他們總有一天也要死的,但怎麽死法呢?」
塞利納本人顯然是一個否定型的天才,這種天才喜歡撕下生活的假面,呼叫各種悲慘事件來考察人心,欣賞人性的崩塌。人來到世上,終將死去,就像在「茫茫黑夜」中漫遊(這個意象組成的句子反復在小說中出現),最終都會被黑暗吞沒。結局都一樣,沒有例外。可大多數人總是極力忘記這一點,想要比別人活得更快樂,更幸福,反倒是那些崇惡之人常常看懂了命運的真相。

塞利納,1955年左右。
實際上,人類之所以能夠存活下去,能夠行善的唯一希望就在於,大家都相信世界不會馬上淪陷,這一觀念可以轉換成一個思想實驗,那就是,假如人類確定無疑,這地球明天就將不復存在,我們已經到達時間的盡頭,所有的人又會做出什麽行為?這就是巴達繆和羅班松奉行的生活準則,他們對人生完全失去興趣,在他們與所有人之間,隔著即將消失的世界。借由巴達繆的心理活動,塞利納道出自己的絕望哲學,小說中的許多議論都可以作為某種人生警示,值得在這裏再摘錄幾句:
必須只爭朝夕,不要白白死去。疾病和貧困驅散你許多小時、許多歲月,失眠使得你成日成周昏昏然眼前一片灰色,癌癥或許已在你的身上滋生,血淋淋地從直腸謹慎小心地往上爬。時間永遠是不夠的!
你活像留作紀念的街角老路燈,但街上幾乎沒有行人。
我的情感有如一幢別墅,只適合度假,不宜長住。
我曾千方百計地糟蹋自己,企圖讓生活拋棄我,但沒有成功,因為我到處離不開生活 ,離不開自己。我曾拖著沈重的步子遊蕩,這樣的時代徹底結束了,讓別人去放蕩吧!世界的大門重新關上,我們已經到達世界的盡頭,有如節日接近尾聲。
我們的全部不幸恰恰來自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活下去。
有誰能夠完全否認這些話道出了生活的本質呢?由於物質幸福已成為現代人的最高目標,人與人之間才充滿了冷漠,個個虛情假意,互相忌恨,卻不知一切看得見的幸福都是虛妄的,自己的人生節日剛一開場,就已進入盛宴的尾聲,很快就將人去樓空。
在巴達繆眼裏,這世間就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全書唯一誠實善良的女人是莫莉,能讓他偶爾想起時內心充滿溫情,她靠著賣淫掙錢,極力勸巴達繆不要繼續漫遊,倆人將來在一起開個小賣店,可他卻拒絕了。這世上無論胸懷大誌的人,還是身份卑微的人,永遠都活得碌碌有味,他們不願正視不幸,拒絕對生活的一切消極看法,整個世界就是如此頑固,而巴達繆早已明白:「其實在我們離世以前,世界早就先離開我們了。」
這句話也是塞利納本人的寫照,他後來遭到全社會排斥,不是由於這部小說,而是由於他的政治立場。惡的盡頭往往是虛無主義,因為對世界過於絕望,塞利納在二戰中選擇站在了惡的一邊,與海德格爾、龐德、齊奧朗等人一道,被歷史所譴責。像他這麽絕頂聰明的人,心裏自然很清楚,跟歷史是無話可說的。他當初可能沒有想到,自己也會像巴達繆一樣,在活著的時候,就已體驗到世界先離開他的感覺,而那些總是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並從中獲得自我滿足的作家們,大概率是不會擁有這一人類經驗的。
作者/景凱旋
編輯/張進
校對/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