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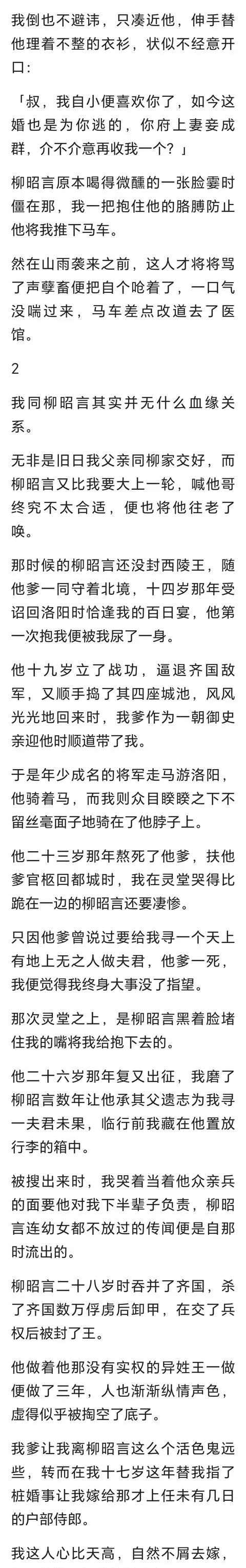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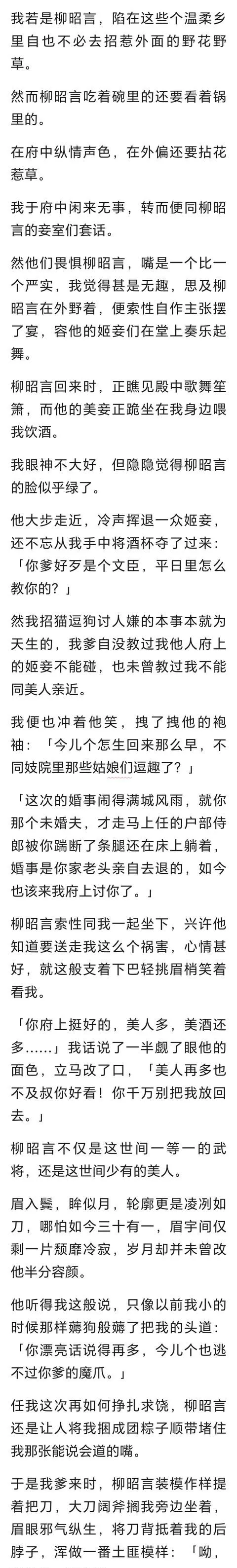
「小女大婚之時西陵王將其擄走,如今這般又是想做什麽?」
我爹在朝中待了半輩子,什麽場面都見過,自是一番人精模樣,全將我逃婚這過錯全都賴在了柳昭言頭上。
然柳昭言卻也認得幹脆:「今兒個很簡單,給本王籌十萬兩,一手交錢一手交人,不然本王就將她給剁了。」
世人都傳柳昭言嫖妓養女人早就將打仗得來的賞賜與家底虧空個幹凈,如今將我拐回去卻打著這麽個如意算盤。
我和柳昭言都以為我爹會拿錢來換我,我嗚嗚咽咽地同柳昭言搖頭,不妨我爹卻是出了聲:「剁吧,我看著。」
柳昭言楞住:「你女兒不要了麽?」
我爹則氣定神閑地摸著胡子,徑自朝主位一坐:
「小女頑劣,如今婚禮上這番一鬧,自也無人敢娶她,潑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的水,由不得我管,西陵王既擄走小女,應當負責。」
他頓了頓,復又加了句:「可小女畢竟是老夫獨女,西陵王又未娶正妻,這正妃之位理應由小女來做。」
柳昭言本想坑我爹,不妨卻反過來被我爹坑了一把。
當場拽著我爹的領子將人拽進後屋。
我被冷落在一邊自是郁悶,手在椅子上磨了半天,到底將繩子磨斷了,不聲不響地繞到後屋靠在窗邊旁聽。
那會兒他們談得應當差不多了,我也再聽不得什麽,我只知柳昭言做了這麽個接盤之人甚是不悅。
而我爹臨走時拍了拍他的肩,只留了一句話:
「阿言,你是我看著長大的,如今落得這般下場終歸是朝廷對不住你,莫要因此生了恨心,絕了自己往後的生路。
我本不想讓思潼與你有所牽扯,然她偏生歡喜你,我這幾日想了想,將思潼放你身邊,她未必不能救你。」
「你真覺得一個乳臭未幹的小丫頭能讓我回頭?」柳昭言卻驀地冷笑出聲。
那時正逼近黃昏,我立於窗邊,透過窗前薄紗看不清柳昭言說這句話時是什麽表情,只覺得他身影蕭條得過分,總容我生出那麽一二不該有的憐憫來。
4
不出三日,我同柳昭言便草草辦了場婚禮。
畢竟這事兒算不上光彩,那差點娶我的侍郎頭上還是一片青綠。
柳昭言初時並不願,但在我拿著繩子深更半夜要掛老槐樹上吊時,柳昭言黑著臉把我抱下來,吩咐將樹砍了後,便也答應了我。
於是我叫他叔一叫叫了十七年,洞房花燭夜喝合巹酒時我改口喚了聲夫君,柳昭言嚇得手一抖徑自將酒潑到了我的臉上。
這酒潑花了我的妝也就算了,當事人偏還笑出了聲,我正待發怒他卻是拿出一方帕子替我擦了臉。
「柳昭言,你喜歡我嗎?」我氣勢洶洶地問。
他則戳了戳我額頭,還不忘笑話我:「小孩子說什麽喜歡?你可還小。」
柳昭言慣會敷衍我,然而他那夜卻甚是溫柔,細致地將我頭上的釵環摘下,又褪去一身繁重婚服掛在一邊,在我以為他要同我睡一處時,他卻道:
「你先睡吧,我去院外透透氣。」
「我們今兒個大婚,你第一天就想出去找女人,小心我告訴我爹。」我拽著他衣袍不讓他走。
柳昭言無奈:「雖然你總不讓我省心,可好歹是我看著長大的,怎麽可能讓你落人笑柄?我就在院外守著,過會便進來。」
我心知柳昭言一時半會也接受不了便宜侄女成他娘子的事實,今夜自也不急著同他圓房,便也隨了他。
那夜直至我熄燈睡下,半夜復又夢醒之時,床榻邊依然是空的。
我遂披衣起身走至院中,月光溶溶而下,映著光下竹影隨風而動,蟬聲於耳邊淒切鳴叫。
我四處尋他不見,正覺得柳昭言又哄騙我,卻不妨回身時看見屋頂上坐著的人。
此時他微曲著一條腿,另一條腿垂在檐下晃蕩,手中還拿著壺酒,正垂眸笑看著我:「深更半夜起來作甚,還怕我跑了?」
「那你深更半夜坐屋頂上又想作甚?」我當即反問。
他兀自喝了口酒,眼神幽遠地看著天邊零落的星星,聲音也空遼得很:「我在想讓你嫁給我究竟是不是一件對的事情。」
以前的柳昭言並不是這樣的,他不會去顧慮什麽,更不會在決定了什麽事後依舊難以抉擇,大半夜爬屋頂吹冷風。
我總覺得我是遭嫌棄了,索性在檐下同他張開了手:「抱我上去。」
柳昭言今夜甚是好說話,從屋頂躍下,一把抱過我的腰,旋身便帶我上了屋頂。
在沈沈晚風中我閉眼抱著柳昭言,哪怕已然坐在屋頂上偏還不肯放開他。
他大概覺得是夜裏太冷,怕我凍著,還將我往懷裏帶了帶。
「我知道你那些妾室都是幌子,每日花街柳巷亂竄也是為了做戲。」我在他懷裏輕聲開口。
柳昭言並未否認。
而我則又道:「既然如此我便是你唯一的娘子了,我同你成婚哪還有什麽對的錯的。」
「可嫁給我,定然不會有什麽好歸處的。」他悶聲說。
我覺得他想得太多,索性趁他不備在他唇上親了一口。
柳昭言在娶我這方面已經夠想不開了,總覺得是他老牛吃了嫩草,今夜我偏又在老虎頭上拔毛親了他。
霎時間,柳昭言方才的愁緒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拎著我的後領將我提了起來:「韓思潼,你膽兒肥了,連你叔都敢親?」
5
其實柳昭言是個可憐人。
他娘死得早,自幼便在北境長大,從北境第一次回洛陽那年他年僅七歲,那會我還沒出生。
聽我爹說啊,他當時年紀小,總還想不通,為何北境風沙襲人,屍體遍野,齊人為何總在北境挑起紛爭。
他人生初始,見到的卻盡是烽煙刀鳴。
因而他初回洛陽,見著滿目紙醉金迷,安逸自在,最初覺得不忿,不忿以後便也不願離開了。
臨別前,柳老將軍想將他給拖走,他當時硬是抱著我爹的腿不放,說要給我爹當兒子,哭得直哆嗦,非要賴在這不走。
這洛陽繁華安樂與他往日認知差距甚大,他才知道並不是所有人的日子過得都如他所知那般淒慘。
一個小孩子這般想其實並沒什麽錯。
可柳老將軍是個粗人,自顧不得當時柳昭言心中那些千回百轉的心思,只一句話就滅了他往後的所有念想。
他提著柳昭言的領子將他提溜上了馬,告訴柳昭言,這裏並不屬於他,他天生就該吹盡北地風沙,天生該殺人拜將,如今貪圖一時安逸,往後便只能死在敵人的刀下。
小孩子哪能接受這些?
我爹只知道他離開的時候一直在哭,哭得甚是撕心裂肺,直至馬行遠了都沒有停歇的意思。
於是十四歲的柳昭言再回來,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當時傳聞柳昭言十三歲時便帶兵立了戰功,取了敵軍副將的首級。
我不知道他是幾歲開始上戰場殺人的,只聽說他第二次回洛陽時性子沈寂了不少,也失了本該屬於他的一身少年氣。
他看花看月,看洛陽繁華似乎都已入不了他的眼,整個人反倒透出一股死氣來。
我一直覺得,柳昭言不適合當將軍,他幼年時既貪妄富貴平安,畏懼戰爭與鮮血,那麽他便不該去殺人。
他合該當一個文臣,哪怕當討人嫌的紈絝公子哥也好,這般逼迫他只會將他重塑成邊界感甚強之人,直到成為一個與世格格不入的異類。
他面上第一次透露出那麽一二鮮活時,便是在我百日宴上抱我之時,哪怕我那時尚在繈褓,還尿了他一身,他還是抱著我笑出聲來。
我不知他當時是如何笑的,大概便如冬日雪融,秋霜初化那般,定然恍眼得很,勝過旁的千萬般顏色。
那會北境平安了三年之久,他便在洛陽待了三年,每日嚴於克己,從未曾懈怠半分,而我亦從繈褓中的娃娃成了牙牙學語的幼童。
他後來不練武時便總愛抱著我,他本少言,自也不會哄孩子,我極愛抓他垂落腰際的發,而後放嘴裏含糊不清地咬。
他便也將自己的發從我嘴裏拽出來,反倒伸手戳我的面頰,我同他笑他便也跟著笑,我哭他便手足無措地杵在那。
我爹見他甚喜歡我,因而兩府往來時,見他抱我,便也極為放心的在他回去時讓他把我帶走養上幾天。
柳昭言哪會養娃娃呀。
我總是幹幹凈凈的被他抱走,灰頭土臉的被他送回來。
他十七歲那年又奔赴北境,臨走時並未有諸多留戀,唯一求的一樁事就是想把我帶走。
後來似乎也覺得自己這要求挺過分,說出的下一秒便反了悔,臨走時未曾再求什麽,走得比誰都要幹脆。
那時我其實尚未記事,一切只是從我爹那得知的,我隱隱知道自己也算被少年時的柳昭言喜歡過的。
他在後來的兩年裏立了戰功,亦逼退了齊國之人,再回來時,少年將軍已然成名。
我年紀尚小對他總還有些模糊印象,再見時便也生了親近之心。
不知是不是重逢那天我非要當著那麽多人的面騎在他脖子上讓他丟臉的緣故,在我記事後,他似乎並不喜歡我,待我冷漠得很。
我雖黏他,他卻並不愛搭理我,總讓我滾到一邊別杵他面前礙眼。
只不過啊他府上總有吃不完的糖以及各種玩意兒,他自己定然用不著,唯一的可能便是為我留的。
而我在他面前哭上一哭,他便蹲下來面無表情地給我擦眼淚,開口語氣也很冰冷:「不許哭。」
我因此哭得更兇,而他只會僵硬著身子同我對視,眼神偶露無措。
直到我抱著他將眼淚蹭他衣服上,他才會將手搭我背上輕輕拍著我的背緩緩抱住我安撫。
他在洛陽與他在北境的時間應當是對半而分的,我記得他陪過我一些年,又分別過一些年,如此迴圈往復。
他後來雖不喜我,可柳老將軍卻甚喜我,我曾在將軍府吃糖吃壞過幾顆乳牙,最後牙疼難忍的時候還將一切錯推給柳昭言,柳老將軍訓他時我便總躲在老將軍背後同他做鬼臉。
老將軍還不止一次說將來要給我尋一個天下至好的夫君,我總背著柳昭言偷偷告訴柳老將軍說我將來要當柳昭言的媳婦。
他便也瞇眼笑著應下來還同我拉了鉤,承諾我長大後定然會逼迫柳昭言來我家提親。
只可惜,柳老將軍死在我九歲那年,因而所有的一切便也都不作數了。
那一年柳昭言扶柳老將軍的棺槨回到洛陽,我在靈堂上又一次見著柳昭言,他當時在棺前跪得筆直,面色卻慘白得嚇人。
聽說柳老將軍當時身陷敵陣,而齊軍已然逼近邊境小城,柳昭言在救他父親與救一城百姓之間選擇了後者。
聽說柳老將軍死無全屍,是柳昭言親自拼湊的屍骨。
還聽說啊,柳昭言在那一戰中也負了傷,差些便也死了。
我第一次接觸生死,除了畏懼與恐慌,卻也還被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傷占據。
柳昭言沒有哭,我卻在柳老將軍的棺前哭得甚是淒慘,柳昭言見不得我哭,他踉蹌著站起走到我身邊,將我抱在懷裏輕聲問:「哭什麽?」
我那時候就只是覺得難過,卻說不出旁的理由,到嘴邊只能哭著答:
「柳老將軍不守諾,答應給我的夫君還沒兌現便死了。」
柳昭言聽了卻是空落落地笑,繼而指著靈堂便罵:
「恬不知恥的老東西,說死便死了,留下一堆爛攤子別想我幫你收拾。」
他將我抱出靈堂後,卻出奇的沒有將我放下,就只是抱著我,直至我聞著了血腥味,低頭瞧見我被血浸濕的衣裙以及淋漓滴落於地的鮮血。
柳昭言似乎也才反應過來,在我驚慌失措的哭喊聲裏,他卻是捂住我的眼睛,他說:
「思潼,別哭,只是傷處裂開了而已,沒事的。」
他說沒事我也信了,不讓我哭我便真不哭了,只死死摟著他脖子不願松開。
他抱著我走得很慢,直至走進一處屋子,他便也就勢靠坐在角落,抱著我將頭埋在我的頸邊,手捂著我的眼始終沒有放下。
我問他疼不疼,他說我抱著他便不疼了,我又問他難不難過,他說我哄哄他就不會難過了。
我依稀同他說了許多話,他也極有耐心地答我,直到他聲音漸緩,我如何喚他他都不再應,而他一直捂著我眼睛的手也垂落下來,我才看清身下氤氳了一地的血泊。
我終究還是在他懷裏哭嚎出了聲。
及至後來的許多年,柳昭言不僅一次借此事怨懟過我。
他說我若聽他的不去哭,無人聽得我的哭聲去救他,他早就可以死了,也省得日後繼續被我禍害。
我則不理他胡言,反而逼他發誓,他是因為我才活下來的,往後我若不允,他定不能輕易去死。
然而畢竟我年紀小,柳昭言也始終把我當成個孩子,我說的話柳昭言一向不當回事。
我很早便明白了,柳昭言這人是世間少有的混蛋。
6
柳昭言一直篤定我腦子有病,然而有病的其實並不是我。
回門時我爹說有病的是柳昭言,他分明有心病,輕易治不好,也輕易想不開。
我覺得這話並不錯,卻不敢當著柳昭言的面同他說。
其實他姑且算是個合格的夫君。
只因娶的人是我,他便也收斂了不少,整日盤算著遣散一眾姬妾,也再未找過他近年在那些煙花柳巷裏認識的相好。
他說我還小,自不想寵妾滅妻讓我被世人笑話。
柳昭言事事其實都替我考慮到了,可我卻依舊不想同他做一對有名無實的夫妻。
他每夜甚是自覺地打著地鋪,從未對我生出旁的半分心思。
直到那夜下雨,雷聲入耳總還攪得人難以入眠,我思及旁的姑娘都是害怕打雷的,便索性起身順帶踹了一腳正睡在地上的柳昭言,用平靜到沒什麽起伏的聲音同柳昭言道:「叔,我怕。」
「你這像怕的樣子麽?」柳昭言笑道,而後自顧自翻身繼續睡。
我索性下了床,死命晃著柳昭言,偏不讓他再睡。
柳昭言徹底被我磨煩了,猛地起身吼我:「韓思潼,今兒個有完沒完了?」
我向來是沒完的,只不過演技不甚好,輕易哭不出來,柳昭言每每兇我,委屈勁兒上來,自然也落了淚。
因著柳昭言這一吼,我倒真溢位幾滴淚,抹著眼睛道:「可我還是怕。」
自小到大,我哭上一哭,柳昭言定然是拿我沒辦法的。
直到我如願讓柳昭言上了榻,我初時只是讓他抱著我,在他呼吸漸緩之時,低喚了幾聲他的名字,見他不應,索性便也將手伸進他裏衣中。
柳昭言舊日征戰,身上落了不少傷,我觸及他身上那些疤痕之時早已忘了再去撩火,反倒將他裏衣又扒開些想看清他身上的傷。
然而我身邊之人如蟄伏已久的野獸般,在我並不設防時翻身將我整個人壓制在床上。
暗夜裏那雙眼睛帶著森然寒意,繼而伸手捏住我的下巴,聲音也冷得嚇人:「你到底想怎樣?」
我被他這般模樣給嚇到了,故作鎮定地親了親他的面頰,他卻驀然俯身吻了下來,動作甚是粗暴,箍著我不讓我有絲毫喘息的機會。
那眼神也像要將我抽筋扒骨般,甚是嚇人。
我踢他踹他,他反倒一把扯過我的發,嘴上猶自道:「你想要那我便給你,你現在在抗拒什麽?」
直到這次我當真嗚咽出聲,他才停下動作,身上的戾氣漸收,輕輕揉著方才我被他捏疼的下巴:「別哭了。」
其實我知道,柳昭言只是想嚇唬我,讓我厭惡他,繼而遠離他,不再與他纏結。
可真把我惹哭後他卻又反悔了,只能收起方才故作兇惡的神情安慰我。
可那會我也當真受了驚嚇,心裏頗覺委屈,被他抱懷裏哄時心中依舊揪成了一團,什麽囫圇話都說出了口:
「柳昭言,要是我不在你風光回城的時候騎你的脖子,不在牙壞的時候跟你爹告狀,不對你胡攪蠻纏撒潑耍賴,你是不是就不會這般討厭我?」
我在他懷裏抽抽噎噎語無倫次地說,他到底也慌了,給我擦著眼淚不經思考就道:「我沒討厭你。」
「那你喜歡我嗎?」我兀自抹了抹臉,又問。
柳昭言苦笑,在我以為他又要糊弄過去時,他卻道:
「思潼,你是我這輩子最珍視的人了,你該有光明如錦的前程,而不是跟我這麽個爛人待在一處。」
說來的確可笑,他分明是一國之功臣,人人都該敬慕仰望,可他卻偏生同我說他是個爛人。
7
柳昭言的姬妾據傳聞都是他於國中各地尋訪來的美人。
可柳昭言卻並不讓我同她們接觸。
直到她們被遣散離府那日,有個姑娘遞話想要我送送她。
我本不欲去,然那個姑娘是在柳昭言身邊待得最久的,我不想讓柳昭言總把我當個小孩,他這些年究竟有沒有喜歡過旁人我還是想尋她問問。
初到約定之地卻並無人赴約,我渾渾噩噩尚未探出究竟,反倒在打算離開時被那位姑娘用利器抵住了脖子。
好巧不巧柳昭言便在此時趕來了。
平日我在柳昭言面前尋死覓活也就罷了,單純就是氣上他一氣,自也不可能真的去死。
然而真當如今生死懸命之時我卻還是怕的。
倒也不是怕自己就這麽死了,單純只是怕柳昭言。
柳昭言少時沈默寡言,中年又放浪形骸,在誰看來都是個沒什麽脾氣的,自也沒幾人知道他瘋起來是個什麽樣子,畢竟看過他發瘋的大多都已經死了。
「在我府上待了這些年,總該知道規矩,讓你做什麽便莫要違背我的意願,你同一個孩子計較什麽?先把她放了。」
柳昭言在數步之外站定,聲線卻沒什麽起伏。
我身後那姑娘只是冷笑,手裏的劍又往我脖子處送了送,我生怕她一個不穩直接劃了我的脖子。
她故作鎮定地開了口:
「西陵王,你當年覆滅齊國,世人都說你功高蓋主,你遭帝王猜忌,被冤枉有謀反之心,還被逼迫上交兵權,整日只能裝作歡場浪子,來借此抵消帝王疑慮。
你心中不忿,又想助齊國復國,借齊國之手霍亂整個楚國都城,便私自在府裏藏了齊國暗探,又暗中豢養死士無數,本該大業將成。
可你現在為了這麽個女人將我們所有人盡數送走,是為了自此收手麽?」
一個國家可被覆滅吞並,但這個國家的人是沒辦法殺盡的。
齊國那個無能的君主在國破時連同他們齊國數位重臣一同失蹤,朝中亦有人言齊國殘軍早就已經喬裝成普通百姓,暗藏於各城之中一直在尋機反撲。
可又有誰會想到,暗中相助他們的會是當年親手覆滅了齊國的柳昭言。
柳昭言此時的聲音偏生冷靜得嚇人,他一字一頓開口:
「我不會收手,誰都不會讓我收手的,如今送你們離開,只是因為你們使命已盡,我不用你們再為我收集情報,也不必留你們在我府上做齊國國君的眼線。」
他方說完,後方有暗器驀地射出,那姑娘身子微僵,似被射中。
而她似乎知道自己入了死局,臨死還想要再拉個墊背的,利器將將要劃破我脖子之時柳昭言卻一刀斬斷她執劍的手,而後將我整個人托拽進他懷裏。
柳昭言捂住我的眼睛,便又揮了刀,我面上濺了一片黏膩,有什麽東西滾落於地,我聞到濃重血腥味,而抱著我的那人始終捂著我的眼。
我聽得他同旁人冷聲吩咐:
「離府的那二十三個暗探一並殺了,將她們的頭顱送還給她們齊國的君主,順便替我警告他,不日起事,沒有我的吩咐,還請他的人莫要妄動。」
柳昭言一直都是人人畏懼的殺神,亦漠視人命到了極處。
當年他覆滅齊國,萬名俘虜被他盡數坑殺,如今更不會在乎這二十多位曾假扮成她姬妾的齊國暗探。
他不讓我看面前的血腥場景,只將我帶離了此地,一路無話,直至回到屋中,他到底放開我,而後竟是一個不穩扶住身側桌沿,捂著自己的心口急促喘息。
在我不知所措上前想扶他時,他卻驀地擡眼看我,那眼神裏的悲傷太過濃烈,開口時就連聲音也帶了顫,他說:
「我這輩子受的最重的傷便是送我父親棺槨回洛陽前的那一戰,長刀自我胸骨劃至小腹,齊軍羽箭亦擦過我的後心將我穿透。
我帶傷奔赴洛陽送我父親屍骨還鄉,並不覺得疼,可那天太冷了,只有你這小家夥身上還有些熱乎勁兒,我想抱著你等死,好歹不至於死得太過難受。
可你偏生連死的機會都不給我,讓你不要出聲,你還哭著將人給引來,非要從地獄裏將我撈上來,你既讓我活,可你有沒有想過你若出了事,我會如何?」
我想過的,我也知道,但我卻不敢說。
我只緊緊摟住他的腰,像他以往安撫我般輕拍著他的背,可他身子卻顫得厲害,我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戰栗,他說:
「我棄過你一次,始終是我對不住你,你是不是因為當年的事想報復我,所以故意入了她設的陷阱?你恨我當年棄了你,恨我當年不要你。」
「思潼,可我覺得疼啊,疼得喘不過氣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疼。」
聽他這般說,我卻也難過起來,小聲哭喊道:
「叔,我錯了,我以後都好好保護自己,再也不去輕信他人,我不會死,你不要再疼了。」
雖說做人不能太自視甚高,可我就是知道,柳昭言將我的性命看得比他自己的還要重。
我猶記得十二歲那年在他出征前夜給自己備了一袋幹糧,躲進他置放衣物的箱中。
那會我年紀甚小,膽子卻甚大。
怕自己被悶死,每夜無人時偷偷從箱子裏鉆出來透風,這般過了七八日才被發現,被人拎至了柳昭言面前。
柳昭言自他爹死後,整個人便頹了,因我沒讓他死成,他記仇得很,在我面前話變得挺多,卻多數是來挖苦我的。
他見我第一眼就毫不客氣地兇我,我心中悲憤無以復加,便當著他身邊十數位兵衛的面哭著讓柳昭言對我負責。
我至今都記得他當時的臉色甚是五顏六色。
那會已行軍半路,他想讓旁人送我回去,終歸放不下心,便將我留在他身邊。
他這次復回北境,本是為了尋仇,然我當時在軍營中被護得很好,以至於並不知他當年的打法有多不要命,剎鬼修羅之稱便是從那時起傳出的。
他扒了齊兵的皮做戰旗,將他們的頭顱剔骨做夜燈,甚至一把火生生燒死百余名戰敗俘虜,將他們焦黑的屍體堆砌於邊關鬧市。
手段太過狠辣,不留余地,終究會遭到反噬。
於是老天又一次讓他做了選擇。
齊兵欲行險道過雁門關,一旦被他們踏入,雁門關後的那幾座城池必遭屠戮。
那一戰中,齊人為報復柳昭言,亦派了一支人數不多的軍隊分道去屠了他的兵營。
為將者,身上擔著諸多責任,又有諸多不由己,柳昭言選擇什麽本就不言而喻。
他為了守住雁門關棄了我和營中的一眾傷兵。
於是兵營中留下駐守的傷兵盡數死了,有數人瀕死之際將我壓在了身下,阻隔了齊兵的視線,也讓我保住了性命。
可柳昭言並不知道。
舊年他在平了雁門關外一戰後立刻折返營中,遍處尋不見我的屍骨。
他以為我死了,同柳老將軍一樣被齊人砍成一堆碎屍爛肉。
他後來說,他跪在那心疼得似炸裂一般,直到四肢百骸漸冷,看這滿目屍骨都已然麻木。
他覺得他爹走了以後,若還有什麽是他沒辦法失去又沒辦法割舍的,便只剩我了。
後面的他沒說,但我知道。
那時我被壓在重重屍骨之下,費了很大的勁兒才爬了出來,第一眼便看見跪在不遠處的將軍手中持著刀朝著自己的脖子利落地劃了下去。
他以為我死了,所以他要將他自己的命償給我。
我驀地在他身後哭嚎出聲,他手一顫刀也落了地,只是頸側卻留下一道極深的傷口,還在汩汩冒著血。
本就是一刀削去半邊脖子的力道,他連自刎也向來夠狠。
就差那麽一點,我同他便是一輩子的天人永隔。
他是因我自刎,又因我收了手中的刀。
他既答應我去活,便也當真只為了我一人去活,我若哪天死了,他也決然不會多活一日。
從那一天開始,我便也知道,我的命同他的是連在一處的。
因而後來我逼迫他娶我,我分明知道他有多怕我死,可總還用死威脅他,可勁地戳他的心窩子。
現在想想,終歸是我的不是。
8
其實柳昭言自從滅了齊國回到洛陽,在慶功宴上被當今聖上擺了一道後,放權放得甚是幹脆。
我自是一門心思撲在他身上,而他則滿心滿眼都是那些個秦樓楚館的花花姑娘。
然我爹始終是個清醒之人,他不讓我同柳昭言一處,甚至直言柳昭言這男人心思已經歪了,我如何都要不得,還不惜給我安排了一樁不甚靠譜的婚事。
如今我同柳昭言雖還未生米煮成熟飯,但畢竟陰差陽錯之下成了婚,也算一根繩上的螞蚱。
我最近總在糾結該怎麽讓柳昭言收手。
畢竟他幹的這事兒如何都說不通,真幹成了他同樣也裏外不是人。
齊人殺他父親,亦毀了他一輩子,他反手滅了齊國,一個一心為家國的將軍,如今又為何要相助齊人復國?
七日後是皇帝的生辰宴,柳昭言自也不避諱我,他說他打算在當日動手。
我去尋他那會,他為了將我撇幹凈,休書都寫好了。
他雖是武夫,卻寫得一手漂亮字,然而他第一次為我動筆送的不是情書,而是休書。
他氣定神閑地在院裏擲飛鏢玩,而我則氣急敗壞地將休書給撕了個粉碎。
我甚少同柳昭言發怒,只因我年紀小,同他發火在他眼裏不過是一只認他捏扁搓圓的紙老虎。
然那次我先是待柳昭言一陣拳打腳踢,還嫌不夠般死命咬他脖子。
他舊年頸部那處傷極深,因此落了疤,我咬起來覺得硌牙,便也無理取鬧地埋怨起他來。
柳昭言果然看著我笑,我自也笑不出,索性便同他說了狠話:
「柳昭言,你要是死了,我也會疼,我不僅疼,我還要殉情跟你死一處!」
柳昭言果真在我又欲說什麽時死死捂住了我的嘴,瞪我道:
「年紀小什麽渾話都說得出口,趕緊給我把話收回去,我自不要你下來陪我。」
柳昭言話一說完我同他自己都楞住了,他說漏了嘴,而我亦得知了他這次本就沒打算活。
他遂也嘆了口氣,似被我攪擾得頭疼,坐在一邊木桌上兀自按著自己的額頭,良久才打破這死一般的沈寂,他說:
「思潼,我爹自幼便教我忠君忠國,我總在被迫做著我無法理解的事,被迫殺人,被迫在家國與私情之中來回撕扯徘徊。
我一直不認同這些道理,可依舊不知緣由地去奉行,老天總讓我在家國與至親中做選擇,我其實畏懼殺人,厭惡戰爭,甚至並不想將所謂的家國百姓放在第一位。
我很早就累了,在我第一次做出抉擇的時候,我便覺得這般無休止的戰爭於我來說本就是酷刑,他人言我大義,我卻覺得我所做的一切盡是錯的。
我分明厭惡殺戮,可到頭來卻只有借著殺戮才能得到快慰與解脫。」
他說這些的時候並沒有看我,只看著桌上那把陪了他大半輩子的長刀,刀上的血跡永遠抹不去,揮刀時的刀鳴便如萬千怨魂悲鳴。
我心中所有憤懣終究漸消,我知我喜歡他,在窺得他那些難言的心思後卻只剩悲憫與心疼,我緩緩走近他坐在他身邊,頭順勢枕在了他肩上。
「我為國征戰半輩子,該失去的都失去了,想留住的也沒能留住。
我覆滅齊國,居功後被帝王畏懼猜忌,為了保住性命還要雙手奉上自己的兵權,我不忿自然也不平,我甚至覺得這般的家國挺可笑的。
都城之中為爭權奪利,人人醉生夢死,邊境之上為護一方國土,人人命不保夕。
歸根究底,人的命終究是不同的,我總要去恨些什麽才能讓自己接著去活。」
他將他的恨說得如此輕易,反倒讓我愈發無措起來。
我輕聲問:「所以你要助齊國復國與自己的故國抗衡?」
「不會的,我還不至於這般胡來。」
他笑著看我,眼睛微彎,繼而輕輕撥開我掃至眼尾的碎發,極平靜地說出了比我的猜測更胡來的預想,「齊國不會復國,我只是想借他們殺盡朝中武將文臣,讓偌大朝野形同虛設,然後我啊,順勢將所有齊國余孽一網打盡,在報復了所有人之後再好好的去死。」
柳昭言所計劃的一切太過瘋狂,他不僅要自毀,連帶著還想讓所有人都陪葬。
他哪是想要造反?分明就是已經在戰場殺瘋了。
他如今是世間至惡之人,也難怪我爹說他連帶著將自己的生路都絕了。
「那你可舍得下我?」我恨聲問他。
他顯然被我這話問楞住了,思考良久才道:「自是舍不得的。」
我在他說舍不下我的時候,欺身摟住他的脖頸吻了他。
他這次沒有推拒,反攬過我的腰身回應了我的吻。
彼時秋日紅色楓葉落了滿院,在一吻終了後,我倚在他懷裏,聲音不由自主帶了無措與委屈:「柳昭言,你真想走也可以,你得把我一起帶走。」
「小孩子莫要說氣話。」
「你死了,沒人願意娶我這麽個寡婦。」
「我活著時是殺神,死了自然也能成厲鬼,你往後瞧上誰,那人若不敢娶你,我做鬼都不放過他。」
「別人求死都是心如死灰,無可留戀,可你哪怕什麽都沒了,你還有我,黃泉路上哪輪著你摻上一腳?」
「那我到時候盡量靠邊站站,再走慢一點,不礙著旁人去死。」
柳昭言早該死了,或死在他父親離世的那個深秋,抑或死在五年前自己的刀下。
是我一次又一次留住了他。
他對人世無甚留戀,生死皆無畏,可我卻偏要強求。
9
柳昭言赴宴前一晚大抵知道同我講理講不清,索性也狠了心腸罵了我一通。
他嫌我煩他,說我纏人,還言我從小到大都是個討厭鬼。
彼時齊人的殘兵已然喬裝入了洛陽,將會於第二日月升之時集於宮外。
而柳昭言手上有百名死士,亦有他爹舊年的殘部,在齊人帶兵攻入時,他們也同樣會將整個皇宮包圍。
不過是一招螳螂黃雀的把戲,偏柳昭言玩得極歡。
然他偏也不貪權勢,他恨齊人,同樣也恨皇城中君謀權鬥的把戲,他索性玩了場大的,臨末兩方俱損他解了心間之恨順帶再把自己搭進去。
我是如何都攔不下柳昭言的。
他離開前留了幾個死士護住我,任我如何哭喊眼睛都不曾眨一下,就只捂著自己的耳朵皺眉看我:「近些年怎麽愈發能嚎了?」
生死攸關處,偏他還在閑話家常。
他知道甲胄硌人,穿之前似也糾結了一番,然後同我張開了手:「最後再讓你抱一次,你過不過來?」
我哭著跑過去掛在了他身上。
他揉著我的發,在我耳邊驟然笑道:「思潼,你既不願同我和離,我自也舍不得你因我而被牽連的,所以你……不要怕。」
他這話甚是含糊,偏在我欲問個分明時,他卻不想再開口解釋什麽。
後來直到他走,我試圖細細理出一些頭緒來,也大抵猜到了一些。
我從始至終於他來說都只是一場難以設防的意外,若我當初嫁了人,安安心心當著侍郎夫人,那麽所有的一切便都在他的計劃之中。
他借齊國之兵謀反自毀,我同他毫無幹系,自也不會被他牽扯半分。
然而我嫁給了他,他是不是會為了我,給自己留有半分余地?
我猜得其實並不錯,柳昭言到底收了手,在後世落了一副他最討厭的愚忠之名。
當日宮變,齊兵攻入皇宮,宮內卻空無一人。
柳昭言臨末良心發現,也到底不欲讓自己落一個罪臣賊子的稱號,老老實實地裝作一個同齊人為伍,忍辱多年只為將齊國余孽盡數殺盡的忠臣。
宮中之人早早撤離,皇帝亦讓柳昭言帶著他的殘部與死士將所有齊國余孽包圍。
彼時齊國國君被殺,剩下的士兵無主,再加上柳昭言不要命的打法,也已然成了強弩之末。
可柳昭言千算萬算,都未曾想到,在一切已成定局之時卻有一個殺手藏於他的死士之中。
那夜宮中火光徹夜未熄,我在晨光初現時見著了柳昭言的屍體,安安靜靜躺在那,已然沒了任何生息。
跟著他的副將說,當時齊人已降,可柳昭言殺紅了眼,不欲將其收押,非要趕盡殺絕。
然而柳昭言舊年戰場上負了不少傷,哪怕好了仍然是多年的隱疾傷痛,如今身手早已不如年少氣盛之時。
柳昭言在天明時終究力有不殆,被偽裝成死士的齊國殺手看準時機趁他不備一劍貫穿了心口。
舊年戰場之上刀劍無眼,他數次涉險,九死一生,都安然活到現在,又怎可能會死在這麽個小小的宮變之中?
到頭來啊,他願意為我讓步,沒有去做那遺臭萬年的惡人,卻不願為了我去活。
我想,到了如今,他一生被命運玩弄,一生命不由主,也算徹底解脫了。
10
尾聲。
柳昭言這一死,自然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他受了追封,而我亦無須同他撇清關系,安安靜靜在西陵王府做著我的寡婦。
我不願再改嫁,轉而在府裏養起了小白臉。
這小白臉模樣甚俊俏風流,觀面相也不過才二十出頭,年輕貌美在我爹看來自比某個老家夥要好上許多。
我自不顧旁的,偏愛拉著他在柳昭言牌位前調情。
小白臉甚是膽大,在同我上了幾次床後,不僅將柳昭言舊日的刀沈了塘,還將柳昭言的牌位給砸了。
不過是仗著我的寵愛任性胡來。
柳昭言死得幹脆,臨死前留給我的也不過是王妃的無用身份,以及他多年謀劃起事被徹底掏空的家底。
我恨他惱他無處發泄便只能在夜深人靜時拿小白臉撒氣。
小白臉別看他長得好看,衣冠之下一身的疤,我膽子小自不敢去碰,只可勁咬他的臉拽他頭發。
他也不是沒脾氣的,在我一口又咬壞了他花大價錢做的人皮面具時,他也徹底怒了,一把將臉上那缺了一塊的面具撕了下來,恨聲道:
「韓思潼,家底都空了,你兩三天就咬壞一個,日子還過不過了?」
「以前嫖姑娘花錢如流水,如今沒了錢你不得可勁在床上討好我求我養你?」
我嬉笑著看他,手細細描摹著他甚是深邃的眉眼,如何都舍不得撒手了。
這小白臉正是柳昭言。
他總覺得自己老,也為了防止被旁人窺得自己的身份,整日頂著張二十歲的面皮在我面前扮嫩裝年輕。
世人都以為柳昭言死了。
他雖在最後收手,可他同齊人相謀是真,豢養死士亦是真,皇帝自然忌憚他,就算他沒假死,皇帝自然也不會讓他活。
柳昭言索性便自導自演了一場戲,死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所有人盡數騙過去。
然而他到底待自己甚狠,心口那處利器傷與舊年所受箭傷本就在同一處,堪堪擦過心臟,但凡偏上一分,抑或是傷處過重他沒挨得過來,他便只能是埋在地底的一具屍骨。
他怕自己當真死了,因而之前從未給我希望,他將話說得甚絕,亦讓我知道了他的必死之心。
他將自己死後之事全都安排好了,卻一直未讓我知情。
直到我深更半夜路過靈堂看到從棺槨裏爬出來,面色蒼白,正同我笑著的柳昭言時,我以為他詐屍了,渾渾噩噩地讓他帶我一起走時,他才說出了一切的謀劃。
他本就起了反心,也從來不把天命皇權當回事,他想不留余地地毀了一切後去死,可我說喜歡他,還硬迫著嫁給了他。
他舊年疼我珍視我,在我長大後又因我的纏結復又生出那麽一絲不可為外人所道的情意。
柳昭言糾結了一番後,便也不想去死了,他想試試為我活上一次。
於是他假死後改換了身份,收斂了所有弒殺之心,亦戴上了人皮面具徹底成了另一個人,就為了年年歲歲伴著我。
如今我好好養著他,掏空我爹的家底給他買上百八十副人皮面具自也不是什麽難事。
柳昭言啊,一向好養活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