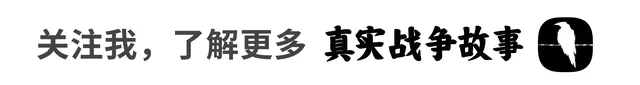
戰場「變形記」
從小我就記得,奶奶晚上總要起來好幾次,說聽到院裏頭有聲音,是二叔回來了。
二叔離家的時候和奶奶交代過,只要半夜院裏有半塊磚頭落地的聲音,就給他開門,那是他回家了。
奶奶從此以後,就沒睡過囫圇覺,半夜裏總是伸長了耳朵聽,總覺得有磚頭落地的聲音。
所有人都覺得二叔死了,直到1988年,我在家門口看到一封神秘來信,我才相信了奶奶的直覺。

我們家在陜西省渭南市澄城縣西永固村(當時叫薛家嶺)。家裏最先上戰場的,是我的父親。
父親是家中老大,最聰明,也最受奶奶喜歡。他從小就給地主家幹活,看學堂裏的有錢人的娃娃念「人之初,性本善……」他也跟著念,念得還怪好,老師就註意到了他,叫到跟前讓他背書。
父親還真的背出來了。老師看他很聰明,專門拿了張紙教他念這些字,說其他娃娃都背不下來,讓他有時間常來學校背書,給這些娃娃看看。
長大了,父親也是家裏的頂梁柱,只是他一個人要養活一家七口人,還是很困難。我們家成了全村最窮的一戶。
遇上災荒年,一家人就得餓肚子。家裏實在沒辦法,只能把十幾歲的三叔過繼給了鄰村的王家。剩下的還是吃不飽飯,交不上人地主家的租子。
雖說日子再苦,大家也是不願去當兵的呀!子彈不長眼睛,上了戰場,說不定哪天人沒了家裏都還不知道。

我們家西永固村的老宅已經荒廢
但也有不得已的時候,1943年光景很是不好,「三年不下雨」,實在沒辦法父親就去當兵了。
我們這裏雖然沒有日本人,但國民黨還是到處拉壯丁,拉一個壯丁給一鬥麥,村裏有錢人不願意去當兵送命,就找人替,父親想著給家裏掙點救命口食,主動替人去了。
要是能逃回來最好,逃不回來,也相當劃算,總比在家等著餓死的好。
父親當了8個多月兵,終於找到機會,成功跑了回來,在家待了兩個晚上以為太平了。誰知剛好又碰上拉壯丁的,直接就把父親拉上走了,管你情願不情願。
上次成功逃了一把,父親信心滿滿,這次進了部隊,也一直等著機會逃跑。一天晚上,父親正摸黑準備逃跑,想不到,沒走幾步,就撞上了一個人。
「誰!」
父親一哆嗦,說話的正是他們的連長。
連長匯報後,說要槍斃他。人斃了,衣服不能浪費,淩晨兩點,連長押父親到刑場,把他身上的衣服脫得一幹二凈。
看眼前這個架勢是跑不了了,父親立馬跪在地上求連長,掏出身上幾個銅板,求連長能在他死後把他的屍首送回老家去。
天亮了,部隊所有士兵都圍在了刑場跟前,長官們也來了。父親全身赤裸只穿一條短褲,被槍抵著上了刑場,幾聲槍響,有人應聲倒地,都是和父親一樣做逃兵的。
天氣有點冷,父親只穿個褲頭,又驚又嚇,光著身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大氣都不敢出一口。輪到他了,他突然急中生智,跪下大喊:長官,我是冤枉的!
父親跪著往前挪,膝蓋磨出來了血也沒停,終於挪到了長官跟前,大聲說,長官,我不是逃兵,我是抓逃兵的。
過了良久,長官開口了,這是個好兵,把他給放了。
打這以後,父親再也不敢跑了,就在部隊裏小心翼翼地混著,一晃三年過去了,抗戰勝利的時候,父親還沒輪到上戰場。
一想,就這樣跟著部隊混口飯吃,也是一條出路。只是覺得愧對一大家子人,部隊就駐在縣城,離家裏很近,卻就是回不去。
父親正懊惱時,二叔突然出現在部隊,自己找上門的。

父親第二次被抓壯丁不久,我的爺爺就去世了。
一家人在鄰村租地主的地種,現在家人想讓爺爺葉落歸根,回薛家嶺安葬。
本來想得好好的事,沒想到老家親戚誰都不讓二叔進門。最後辦事兒那天,一個人都沒來參加葬禮。
家裏實在太窮了,親戚都怕牽扯上關系,要多一口人吃飯,不敢搭理。
一晃爺爺去世快三年了,三年守孝期滿了就要「換服」,把白衣服脫掉,換成紅衣服。這是我們這裏的大日子,如果不辦得風風光光,就會讓人看不起。
二叔擔心會像三年前一樣,沒一個人上門。於是打聽著找到了父親部隊。
二叔和家裏商量好了,這次來是替父親當兵的,讓父親回來辦事。等家裏的事辦妥,兩兄弟再換回來。
走的時候,二叔特別和奶奶交代過,只要半夜裏院裏有半塊磚頭落地的聲音,就給他開門,那是他回家了。
那時候,全家人都堅信,以為就像當年父親回來一樣,二叔也會在某一天的深夜突然出現。不管是逃跑回來的,還是換回來的。
沒想到,命運這東西完全沒個準數,不是說換回來就能換回來的。
我爸在村裏確實是算個能耐人,回家以後各種走動、求人,找地主借了「高利貸」把事給風風光光辦了,全村人都來捧場。
在家呆了兩三個月,父親決定去把二叔換回來,到了縣城才知道,打完抗日戰爭,駐紮了兩三年的部隊,突然開拔上了前線。
我爸在部隊呆三年沒上戰場,二叔去三個月就趕上打仗了,還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安靜了多年的村莊也開始熱鬧起來,農村的院落很大,士兵住進了鄉親們的院子,奶奶記得最先家裏住進來的官兵夥食很好。
一家人餓得不行也不敢出聲,一個穿軍官模樣的人先給奶奶端一碗吃的,剛開始奶奶不敢要,軍官說他們還有,讓奶奶先吃士兵才準吃。
有一次奶奶正吃飯呢,就聽見南邊槍聲響,幾個鐘頭以後,發現外面死了很多人,才知道是打仗。
等到了跟前,看死人身上的軍裝不是一種顏色,村裏有懂這些的人說,灰衣服的就是解放軍,黃衣服的就是國民黨。
給奶奶端飯吃的人,就是穿黃軍裝。
後來,大家都說國民黨軍紀敗壞,好在我們這裏沒遭到什麽禍害,不過在當時,小村子裏訊息閉塞,也沒人說得清這些事,只要當兵的不搶我們村,就謝天謝地了。
何況二叔還在他們的部隊呢。

仗打得越來越兇,一邊是胡宗南部隊,一邊是彭老總部隊。
幾十萬大軍圍在一起打,小戰鬥頻繁發生,大戰鬥也不少,我們這裏的壺梯山是連線陜北與關中的交通要道,兩支大軍在這裏開始布兵。
有一天,天正熱著,附近防虜寨的人跑進村裏報信,說他們那裏有共產黨死了,好像是你薛家嶺村的人。
我們村加入共產黨的只有一個,叫薛印合。
這個人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管我父親叫伯伯,我們八家共同祭祀一個祖先,每年都輪流祭祀。
他讀過書,思想進步,很早就奔赴延安,加入了共產黨,現在是解放軍,上面派他回來負責收集情報,領導遊擊隊。
那時候解放軍是從南往北打,薛印合小隊一共有七個人,他們在一個墳地裏面隱藏著,這裏面有很多柏樹。本來預定的時間是兩小時以後再打,結果突然提前了,敵人發現了他們(因為出現了內奸),他們中只了一個,其余的都犧牲了。
村裏人一聽,好幾個人包括我爸就去幫忙背屍體,推著鐵軲轆車就去了。走之前,薛印合的媽說,我兒子有24顆牙,你去了那裏要是有人有24顆牙,就是我兒子。
到了那兒,一看,野外裏到處躺著人,都被打得血淋淋的,把人害怕的,已經認不出屍體。
我爸端了一盆水,拿了個手帕,壯著膽子走過去,把臉上那血擦了擦,看清楚相貌,再把嘴掰開,數了數牙,說這就是我的侄兒。
屍體用席子一裹,捆上繩子,用鐵軲轆車拉回來,埋到他家的地裏了。
這個薛印合就是現在我們縣最有名的革命烈士薛仲舒。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給薛仲舒修碑時,我們村有個人負責糊花圈,但那人沒文化,看這個兩旁的悼聯空空的,就給編了個順口溜,在兩個悼聯上寫:人生在世要公平,花開還有幾日紅。
結果人家革委會公社那幫人就狠狠地批鬥他。審問他,問你和這人有啥冤有啥仇呢?
革委會說他這句話就不對,不能寫「公平」。革命烈士犧牲怎麽會是不公平?胡說八道。意思是他侮辱了革命烈士。
其實糊紙匠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們是一個爺爺的人,能有什麽仇呢?就是沒文化編了個順口溜,惹了禍。
前幾年縣裏頭又建烈士紀念碑,工作人員突然打電話給我幾個遠處的侄子侄女,讓他們趕緊回來,要開烈士紀念大會,其中有一個是他們的爺爺,也就是我的三叔。
三叔成了革命烈士,這是我們家誰也沒有想到的。

三叔過繼給鄰村的王家,改名叫王天錄。
三叔具體怎麽上的戰場不知道,烈士碑上寫他是主動跟著解放軍部隊走的。
我們家只知道三叔犧牲是在陜西眉縣馬家鎮戰鬥,這已經是1949年的夏天,這場大戰,解放軍大獲全勝,胡宗南部隊慘敗。
三叔在彭老總部隊,二叔在胡宗南的部隊,不知道兄弟倆是不是也在戰場上刀刃相見?也許,他們到死都不知道,失散多年的兄弟就在對方陣營裏。
三叔的碑文上記載,他隨軍行至眉縣,戰鬥打響後,他去搶救一個傷員,一顆炮彈落下,光榮犧牲了,時年24歲。
戰爭結束後,政府給三叔的養父家送了烈士牌。養父母家給他領養了個孩子,孩子很爭氣,很有出息。

三叔的烈士墓碑
三叔犧牲的訊息傳來後,家裏一直瞞著奶奶。只是時間長了,奶奶就問,老三這孩子怎麽好長時間都沒到我這裏來了,大家哄她,說三叔是到外面做活去了。
全家人都不敢和奶奶說三叔死到戰場上去了,因為怕她受打擊,老二兒子不見了,老三兒子給了別人也死了,她經受不住打擊。
再過幾年,奶奶有些埋怨,總是說,我把他看十幾年,結果人家看都不看我,不認我這個娘了。
二叔還是一點訊息也沒有。所有人都覺得二叔死了,只有奶奶不這麽覺得。她留著二叔所有的衣服、鞋子,一樣都沒扔,說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奶奶晚上都要起來幾次,總是說自己聽到院裏頭有磚頭落地的聲音,好幾次爬起來一看,可哪有人嘛?
此時全國已經解放了,父親開始磨豆腐置了一份業,做豆腐滿街的賣,一個人養活了一大家子,慢慢的生活也好起來了。
因不知道二叔到底是死是活,我爸決定為他領養一個孩子,說是將來要繼承二叔的香火。
東家挑,西家選,又借遍了全村家家戶戶,終於湊夠了八石糧,娃娃進了我們家的門,又漲兩石糧。讓開口叫奶奶,大意了——這娃娃連話都說不清。
每天早上母親把堂弟的衣裳遞上,把他背到學校,讓他念書。沒想到光小學五年級就念了8年,老師氣得挑眉毛:把你娃領回去,他學不下。
父親安排他去學技術,也沒學成,長成大人後給娶了媳婦,成了家。不管怎樣,用父母的話說是「終於有交代了。」
一家人都以為二叔的事兒已經塵埃落定,卻沒想到,二叔的失蹤,陰差陽錯地打亂了我的人生。
從小到大,我在校一直是優秀學生,高中畢業去搞團工作,做了些成績,半年之後讓我兼職大隊的婦女工作,一職兩責。
團支部把優秀團員的名字上報縣,我也在其中,我就寫了份入黨申請書。黨組織考察後說,你都合格,就是有個親人下落不明,批不了。那是70年代中期。

我(一排右二)參加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二叔不在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心裏一直對二叔有愧,覺得本來失蹤的應該是他。幫二嬸改嫁,替二叔領養了小孩,照顧他長大成人,只能透過這些事兒來彌補了。
逢年過節家裏總會給二叔添雙筷子。但說一句良心話,是死了還是活誰都不知道,確實咱就是聯系不上。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寫過入黨申請書。
最後沒辦法,我自己做生意去了,收蘋果。有一年收蘋果掙了不少錢,那時候一輩子都沒見過那麽多錢,然後就擴大繼續收蘋果。
一年又一年,父母老了,奶奶也走了,她沒能等到磚頭落地的聲音。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我也成了家,生了第一個孩子,還沒滿100天,父親就病了。
父親生病已經有半個月了,那天他起不來床,黑眼珠往上翻,兩頰深深地陷進去。
村裏正好來了些老人,見著我爸這個樣子嚇了一跳,「緊寒的話6天,慢寒的話9天。這病都已經過了9天了,看來人活不成了……」
這一說,我們這才意識到這病有多麽嚴重,母親在家照顧父親,我趕緊去給裁縫送布做壽衣。
那是1988年的冬天,我急匆匆地出門,在大門口碰上村裏的韓老師,他遞過來一封信,我歪頭看了看信封,一眼掃到了「台灣」兩個字,但卻讀不通順,都是些「老字」。
當時哪有心情研究這個,我腦子裏嗡嗡的靜不下來,一心想手裏的這塊布。
「韓老師,你趕緊把這信拿給我媽。」我又不放心的囑咐道,「她就在屋子裏,我爸病重的,我得趕緊走。」
行行行。韓老師滿口答應。
剛走到裁縫家,把布放下,村裏人就來喊我,說救護車都到你們家門口了。
在醫院裏一住就是幾個月,到過年前父親的病竟然好全了。我和醫院工作的小妹說,年前有封從台灣來的信,準是二叔寄的,怪不得這麽多年他音訊全無,原來是去了台灣。
等到第二年春天,小妹回家說,在住院部工作時剛好碰到統戰部的人,聽說我們家收到了台灣的信,他們願意幫我們查人。
這是我們家等了幾十年的好訊息,我趕緊讓母親把信找出來。
一問,母親楞住了。仔細一想,當天韓老師確實進屋來了,但家裏亂哄哄的,韓老師什麽也沒說,就離開了,更沒提信的事。
我的心裏隱隱覺得,大事不好。趕緊去找韓老師。
可萬萬沒想到,韓老師拿不出那封信了。我問了半天,他前面說不知道,後面支支吾吾說信被他燒了。說是過年學校打掃衛生就把廢紙全燒了,不光燒了我們家的信,所有廢紙都燒了。
我火一下上來了,朝著他嚷了起來。韓老師也很生氣,說就是燒了,還要攆我走。我們吵了起來,
最後韓老師差點哭了,說倆家沒仇沒怨,還是親戚,燒信是他的錯,請原諒。
我問他是不是看過信的內容,他說沒有,我問他還記得信封上面的地址了嗎。他也說不記得。
好吧,我也哭了,又生氣又無能為力。
是因為覺得死人晦氣燒了那封信?還是害怕那兩個字燒了信?信上都寫了什麽?信件的地址是哪裏?
甚至有人幫我分析,會不會是信裏有錢,韓老師拿走了,所以不願意告訴我。
我們什麽都不知道,只能死死纏結著韓老師,隔一段時間就找他一次,想讓他回憶一下,每次得到的的回答都一樣——燒了,不知道。
父親更是生氣,說不管韓老師是不是親戚,都要把他拉大隊去理論理論。我擔心父親身體,趕緊勸他算了。
這封來信成了我們家的謎案,也成了新的希望。
有信來,說明二叔人還在呀。

直到1992年熱起來的時候,大概是五六月,麥子熟了,才有了一點訊息。
父親中午從外面回來,就急匆匆讓我帶他上隔壁的村子北莊去,那時候飯快做好了,父親卻等不及說回來再吃,得趕緊上北莊去。
原來北莊有個老人從台灣回來,父親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二叔的線索。
父親那年已經82歲了,我可不敢騎單車帶他,好在路途不遠,我一路用單車推著他到了北莊。
我能感受到父親內心的激動,他和奶奶一樣,等待著那塊磚頭落地。
那從台灣回來的老人已經89了。雖然是從台灣回來的,和我們這邊的老頭也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我有些聽不懂老人家說話,只看到他直擺手。
旁邊人轉譯說,他說部隊不一樣,參軍的地點都不一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
老人還是耐心幫我們分析,既然來了信,人肯定還在。他告訴我們,他在台灣生活,活得也很好。
我們唯一能提供的資訊就是二叔的名字——薛丙順。
老人擺擺手,不作數,台灣的人和咱們這裏的人不一樣,很多人都有幾個姓幾個名字。他讓我們想想征兵時候登記的是誰的名字。
我爸的登記名字是薛景玉和薛丙乾,二叔登記名字應該是薛丙順,總之,這三個人都有可能,但是當時抓壯丁時候也可能是頂替別人,也有可能用了別人的名字。
這麽一來,資訊就更加復雜了。
這次回來後,父親很難過,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找我說過話。

父親、小妹和我
有一天他主動找我,還說要給我看樣東西。
他把我帶到我家專門放祖宗牌位的桌子上,我們家人過節日都要在這桌上「獻祖宗」,每次獻祖時都在這兒放一碗飯把筷子放上,對著他們說,爺爺奶奶先叫你們吃。
今天不是獻祖的日子,父親開啟一個用紅綢子包好的東西,竟然是一塊牌位,仔細看上面寫著二叔的名字和出生年月。

父親和二叔的牌位,二叔的已經模糊不清
父親說,你二叔在不在我也不知道,在也好,死了也好,反正都沒有找到人,都是我的遺憾。把這個東西放在跟前,以後獻祖的時候一起獻了,也是個念想。
母親說,你看你這樣子幹啥,二弟人肯定在呢。
父親說,趁我在著呢,要讓家裏的娃養成這個習慣,別忘記了。
沒過幾天就是八月十五,父親特意坐著看著我獻,說以後自己老了,不在了,你們也這樣獻吧,我就放心了。
父親知道自己老了,他有預感,自己等不到那半塊磚頭落下的聲音,得提前交代好後事。
父親走是1994年春節,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兒,但都沒有什麽好結果。正月初六,父親說他夢到一輛車停在我們的老房子跟前,要接他走,覺得是個不好的預兆。
父親的小妹當天也做了一模一樣的夢,感覺心裏不踏實,特意來我們家拜年。那天晚上,父親就去世了。
我想,如果二叔還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會不會也做了這個奇怪的夢?

薛存芳阿姨在父親去世後,她也沒有停止尋找二叔。
采訪時,薛阿姨說這麽多年,不知道是不是找魔怔了,反而更覺得二叔沒有死,就在台灣。
她甚至和家人做了詳細分工,準備去台灣待一年兩年,慢慢找。後來去咨詢才知道,台灣不是她想去就能去的,這才不得已停止了計劃。
現在,他們家尋找二叔的任務已經交給薛阿姨的兒子,薛阿姨兒子從上大學就開始就在給台灣朋友、海基會等寫信。
我采訪過太多尋找「二叔」的故事,在我心裏,二叔已成為戰爭失蹤者的代表。
對於大多的戰爭失蹤者家屬來說,幾十年過去,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尋找的過程才至關重要,它代表著——永不忘記。
這些失蹤的親人,因為是父輩心裏放不下的惦記,也成了後人想要解開的謎。這個謎就是我們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
對於每一個走上戰場的士兵來說,死亡都不是真正的離別,忘卻才是。
編輯:霞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