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於思(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閆文捷(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周睿鳴(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
來源: 【青年記者】2023年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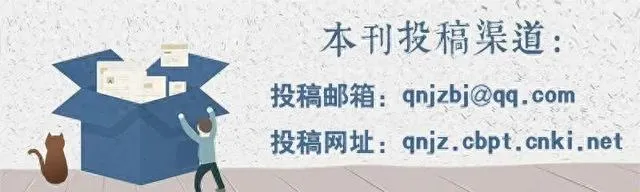
導 讀
本文結合事實核查的中國實踐和韌性修復的全球經驗,從虛假資訊應對的個體和媒體韌性兩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系統韌性的跨尺度指標,提出了將事實核查作為系統韌性有機組成部份的分析框架,以期對未來的比較媒介體制和數碼新聞真實觀研究有所啟示。
2019年起,新冠疫情以及與其相伴共生的資訊疫情加大了虛假資訊對公共生活乃至人類生命的威脅;在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散布資訊以操縱選舉也成為特定國家互聯網研究機構工作職責的一部份。近年來,客觀事實在塑造公眾輿論方面的影響力不如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媒介體制應對虛假資訊的復原力或韌性(resilience)成為極具理論潛力和現實意義的傳播議題。混合媒介體制(hybrid media system)是一種因數碼化和網絡化特征而將媒體和政治邏輯相融合的媒介系統,[1]媒介體制不再局限於機構化媒體,而是分布於新聞組織的內部和外部,體現了新聞文化和實踐的多種混合。[2]各類行動者為了特定目的將各種元素組合在一起構成數碼媒介體制的要素,展現出從組織到集合的過渡。[3]國際事實核查運動將新聞機構以及秉承相似機構價值觀的學術、政治和民間社會團體整合在一起,[4]超越並擴大了傳統意義上新聞專業領域的制度邊界,生成了新興的制度模式,並使之時刻處於正在構建和形成的過程當中,這為理解數碼傳播場景下的韌性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機遇與挑戰。
然而,究竟何謂媒介體制韌性,至今仍在不同分析單位和研究取向間存在爭議。既有研究曾以歐美國家中自我宣稱未遭遇過虛假資訊的公眾比例來反映媒介體制的虛假資訊應對韌性,[5]這固然是在跨國比較數據限制下提升可操作性的選擇,但這項單一指標一方面樂觀地預設了各國公眾已經具備基本的虛假資訊分辨力,另一方面也忽視了數碼韌性的多重構面。因此,有必要對媒介體制韌性進行重新概念化,探討其中涵蓋的多重指標,使之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間更具普遍性,以豐富當前新聞傳播學界有關提升數碼韌性、應對數碼宣傳的思考。
透過事實核查應對虛假資訊的中國實踐
從中國的事實核查實踐來看,無論是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還是在疫情期間和「後疫情時代」,事實核查都扮演著從虛假資訊中恢復秩序和媒介體制韌性的關鍵角色。事實核查這一新聞樣式最初以監察政客等公眾人物在政治活動(特別是選舉活動)期間的言論為己任,把核查政客公開聲言的事實性作為核心任務。伴隨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事實核查被新聞從業者拓展至政治議題之外,抗擊包括新冠疫情在內的科學、健康和公共衛生範疇內的問題資訊,向公眾提供科學而負責任的事實。在中國,目前從事虛假資訊事實核查的行動者主要有互聯網平台、國有媒體和高校社交媒體平台賬號等,它們以各自不同的組織形態,在數碼媒介體制中相互補充地發揮著韌性的恢復作用。
2016年前後,事實核查在中國落地。騰訊推出了一款名為「較真」的事實核查服務。「較真」是一個頗具本土特色的詞匯,在漢語中,有接近真相之意,常常被用來描述人類在認識和交往行動上的嚴肅認真,表示與含糊相反的狀態。與其名稱一致,以「較真」為代表的互聯網平台事實核查既可能包含啟蒙理性指引的專業事實核查,也可以表示如「辟謠」在內的某個去偽存真的認識過程。這項由騰訊新聞推出的服務主要透過騰訊的微信公眾平台提供給公眾,而微信公眾平台為有意願向訂閱使用者傳遞其制作的互聯網資訊的機構和個人提供了賬戶開設和推播的條件。2016年至今,「較真」每天推播至少1篇文章,以健康、公共衛生和科學議題為主。騰訊還為「較真」開發了可在微信內執行的小程式,將「較真」生產的所有核查條目整合在數據庫中,供使用者檢索。除此之外,較真還可以透過騰訊新聞網頁和移動應用程式存取。
2021年秋,澎湃新聞上線了事實核查欄目「澎湃明查」。從議題上看,「澎湃明查」聚焦國際新聞,關註社交媒體平台上紛至沓來的問題資訊。「澎湃明查」是在2022年上海本地國有企業第二輪註資後獲得澎湃新聞重點支持的欄目,擁有自己的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依托澎湃新聞時事新聞中心國際報道組的記者和編輯,「澎湃明查」已經維持了兩年多的常規運轉,每天都有新的核查條目透過網站和微信公眾號釋出。
高校也是事實核查在中國在地發展中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透過微信公眾平台非週期性地推出師生依托學院相關課程制作的事實核查作品;創立於2017年10月的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核真錄」也以其對社會議題的關註吸引了廣泛的關註和社會的共鳴。[6]盡管這些作品沒有穩定的生產常規,議題類別也不集中,但在新聞教育和研究領域也產生了社會影響。
透過上述案例可以發現,作為生產實踐,事實核查實際上延伸了媒介體制制度化了的、被正當化的新聞組織扮演的社會角色,是新聞組織透過嚴肅議題捍衛公共生活的元件之一;作為新聞樣式,事實核查被新聞從業者賦予了專業導向,文本和敘事框架折射了新聞從業者以職業身份凝聚社會共識、塑造共同價值的期望。沒有新聞從業者這一社會精英主導,它不可能作為一種創新的新聞樣式推出、與公眾見面,更不可能在當下問題資訊叠出的數碼媒介生態中為修復資訊失序發揮獨特作用。
透過事實核查應對協調資訊操作的全球經驗
良好的內外資訊環境不足以構成杜絕虛假資訊和提升新聞信任的必要條件,虛假資訊應對韌性還將由國家和媒介體制的結構性特征導致。[7]由於網絡化的外國幹預是能夠引發體制性危機的威脅,亦有研究將媒介體制韌性定義為與其他國家爭奪本國受眾註意力的能力。[8]在這一視角下,協調資訊操作(coordinated information operations)是外國/本國政府及其代理人/政黨和公職候選人使用社交媒體/付費廣告傳播誤導性觀點或虛假資訊以影響本國公眾/其他國家公民及政治的方法,既可以由在國家政治軌域上有既得利益的外國勢力使用,也可以由國內行動者使用,以歪曲公眾可獲得的資訊,利用社交媒體平台的影響力和「巨魔軍隊」(troll armies)等工具來產生和傳播特定觀點或虛假新聞。[9]這時,事實核查機構的介入對敘事戰具有較好的緩解作用,有助於透過對虛假資訊的駁斥來恢復公眾對新聞業的信任。[10]
目前,全球範圍內對抗協調資訊操作的行動模式主要有適應力模式和家長式行為模式兩種,前者承認公民的資訊權,在此基礎上致力於促進公民必要的批判性思維和資訊素養的建立,後者則由包括歐洲對外行動局(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在內的第三方機構負責揭露虛假資訊及傳播此類資訊的媒體。[11]相對而言,事實核查兼具了兩種模式的優點,不僅在短期效果上有助於及時發現和揭露虛假資訊,長期來看,建立事實核查新聞的閱讀習慣也能夠提升使用者謹慎思考的思維方式和能力,培育批判性思維和務實、謙遜的社會文化氛圍。[12]例如,在俄烏沖突中,PolitiFact、FactCheck.org以及The Fact Checker等美國精英事實核查機構開展了一系列信源透明度高、稽核機制成熟的查證工作;[13]英國允許Full Fact等獨立事實核查組織以非營利性慈善組織的名義運作,透過真實和準確的資訊稽核賦權於知情公眾;[14]日本也成立了事實核查組織FIJ,逐步推動涵蓋初步甄別、新聞媒體核查與釋出和事實核查新聞評價三個環節的標準化核查體系。[15]從全球性組織來看,包括美國、法國、阿根廷等國家在內的國際事實核查網絡也在專業政治核查、公共資訊核查、社會管理核查和戰略宣傳核查方面做出了大量嘗試,透過全球共同體的形式,致力於在跨國語境當中協商出特定的職業準則並將其制度化。[16]借助事實核查修復新聞信任已經積累了相對豐富的全球經驗,透過這些經驗在彼此之間千差萬別的媒介體制中對抵抗協調資訊操作的適應力行動模式和家長式行動模式進行有針對性的結合,亦將有助於遭受不同程度協調資訊操作的社會改善其所處的資訊環境。
作為媒介體制韌性要素的事實核查
盡管「韌性」一詞已經廣泛地被運用於理解個人/關系、家庭、組織、社區和國家等人類系統,但如果缺少了對這一概念之含義、衡量方式和實作途徑的學術共識,透過溝通提升人類社會系統的韌性也就無從談起。有學者建議,任何對「韌性」的概念化和理論化都應當區分如下幾個重要方面:何物的韌性、應對何物的韌性、為誰提供的韌性、由誰提供的韌性、韌性規模、韌性形式以及作為韌性要素來源的系統維度。[17]
對前兩個方面而言,媒介體制韌性是其在應對虛假資訊沖擊時的復原能力。在提供韌性的主體方面,常有學者提出批評稱,韌性概念往往將社區、社會和其他系統在面臨不可預測的威脅時需堅持不懈的責任從群體轉移到個人。[18]實際上,從韌性體制應當具有的特征來看,負責鞏固或擴大韌性的責任可能既來自公民,也來自社群或國家。具體到媒介體制韌性的責任主體方面,在微觀的個人層面上,韌性被操作化為一種為什麽有些人在遇到幹擾時能適應、其他人則不會的個體差異,[19]這時,韌性意味著人們能夠應對虛假資訊帶來的壓力,並從意外挫折中恢復過來。[20]不同於國家層面的宏觀韌性更多地被看作一種透過囊括一部份人、排除另一部份人來喚起團結感、堅定感和社會信心的政治修辭而非可以觀測的具體指標,[21]社區這一中觀分析單元對考察韌性而言具有更強的現實性。在這裏,社區韌性被視為一種「回歸常態向前看」(bouncing forward)的集體能力。[22]社區韌性的概念化理解適合用來分析媒介體制的虛假資訊應對韌性,其原因在於,首先,學術界對虛假資訊應對韌性的評估多以媒介體制為分析單元,而媒介體制的特征需要以地區為邊界。其次,社區韌性作為一種集體現象,往往需要在特定事件發生後才得以體現,特別是破壞性事件。盡管虛假資訊在社交媒體時代的泛濫看似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新冠疫情也被認為催生了資訊疫情,後者為考察不同媒介體制應對虛假資訊的韌性提供了契機。有學者進一步區分了社區韌性的兩個主要來源:社區是否擁有足夠堅韌的個體或媒體,[23]從個體面對虛假資訊時的脆弱性和據此形成的新聞信任兩個方面來考察虛假資訊對韌性的影響。[24]無論是媒體擁有韌性還是組成社群的個體擁有韌性,基於二者互動而形成的社群韌性都能夠促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體制或系統的韌性不是在孤立狀態下發揮的,而是與其他系統的狀態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得體制獲得抗沖擊能力。有學者將韌性區分為致力於恢復現狀的保持性韌性、透過改變邊際來調適的邊際型韌性和以轉型為特征的更新型韌性。[25]這時,所謂制度的穩定和良善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擁有和表現出來的單一內容,而是一種模式化調整的反應過程。[26]僅僅將個體或系統的韌性視為一種適應能力是危險的,這種觀點將使人們忽視韌性在形成過程中所需的支持、機會和資本。[27]前文述及的三種韌性反應中是否以及采取何種韌性形式,取決於系統內容、個體和其他行動者的行為,以及歷史、文化、價值觀和其他社會政治變量的共同決定。[28]綜上,媒介體制韌性刻畫了一種受社會歷史影響的動態過程;它由體制內容、機構和行動者共同決定,故而在系統和子系統層面有所差異;它既可以是一般的(如針對虛假資訊),也可以是具體的(如針對資訊疫情)。虛假資訊應對韌性是特定媒介體制展現出的資訊系統自凈復原能力,是一種包含個體韌性差異在內的跨尺度(cross-scalar)集合特征,表現為社區在面臨挑戰時展現出的穩定性、適應力和彈性。[29]作為一種結構性情境,高水平的應對韌效能使公眾免於或較少受到虛假資訊的影響,減少對低質素資訊的接觸、傳播和采信。
結合上述討論,媒介體制應對虛假資訊的韌性可以被概念化為處於特定媒介體制中的媒體和個體所具有的虛假資訊應對韌性兩個層面。其中,媒體韌性強調媒體是否有能力在與虛假資訊的競爭中勝出,使人們更少地透過演算法或社會網絡接觸到虛假資訊;個體韌性則強調人們是否在真假資訊良莠不齊的資訊環境中依然願意相信專業媒體。媒體韌性方面,考慮到自報告式虛假資訊遭遇比例可能高估了公眾的資訊素養,因此,應當重點關註事實核查機構對各國資訊疫情的判斷。個體韌性方面,由於演算法和新聞客製等技術在社交媒體時代的介入,人們可以選擇自身信任的新聞源,這也構成個體新聞信任的內部認證機制。[30]綜上,媒介體制的虛假資訊應對韌性應當被視為由多個方面共同表征的復合構念,既包括特定國家或地區公眾自報告和在專業機構事實核查中較少遭遇虛假資訊的情況,也包括公眾信任新聞總體和個人客製化新聞信源的比例。這種媒介體制虛假資訊應對韌性采納韌性分析中跨越系統與個體的跨尺度視角,前文述及的虛假資訊幹預模式的適應力模式和家長式行為模式也分別對應恢復個體韌性與媒體韌性的實踐策略。
結語:在後疫情時代重思媒介體制韌性
將媒介體制韌性視為一國或地區內部公民平均虛假資訊判斷能力的個人化視角幾乎使「韌性」被簡單地等同於個人層面的媒介素養或批判性思維,[31]造成概念本身及其理論機制的倒退。而將數碼媒介體制的虛假資訊應對韌性區分為媒體韌性和個體韌性兩個面向,同時加入事實核查作為媒介體制韌性的有機組成部份,這種跨尺度視角下媒介體制韌性的衡量方式響應了既有研究的呼籲,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單一尺度的韌性可能帶來的問題。需要註意的是,虛假資訊可能並非對媒介體制韌性造成沖擊的唯一威脅,除了資訊疫情的泛濫之外,與社交媒體平台幾乎同步發展的民粹主義似乎也難辭其咎。在回應「應對何種沖擊的韌性」問題時,這些對新聞業、民主乃至公共生活的逐漸湮滅應當承擔責任的因素需要進一步發掘。
如果說韌性反應過程由國家、機構、公民社會和個體共同制定,但體制的韌效能力則可能由制度內容決定,這種韌性是一種恢復能力,「回歸常態」意味著體制回到危機事件到來之前的狀態,那麽,將韌性視為一種動態變化的過程仍是十分必要的,這種歷時性分析將幫助研究者對初始韌性(onset resilience)和崩潰恢復韌性(break-down resilience)作出必要的區分,[32]從中洞悉特定的媒介體制內部因何種行動者的努力而產生了韌性的波動。此外,「韌性」一詞似乎包含了一種固有的良善價值判斷,但如果人們將提升適應力作為應對破壞性事件的唯一對策,淡忘反思和吸取教訓的意義,那麽,社區也將失去包容和變革的可能。[33]作為一柄「雙刃劍」,韌性既能拯救人類,也可能阻礙人們對復雜性的理解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與繁榮。但社會和政治系統的韌性比工程或生態更復雜,因為社會既不適用於計劃及其帶來的對個人和群體能動性的抹殺,[34]也不能避免恢復常態帶來的新問題,包括常態可能依舊不耐受沖擊或對「新常態」不夠開放。[35]即便如此,當媒介體制韌性致力於讓真相在意見市場中勝出、促使公眾對新聞業保持基本信任時,其試圖恢復的秩序或常態依舊是合乎規範和常理的。[36]從這個意義上說,透過事實核查增進對媒體系統韌性的深入理解,不僅有助於推動未來的數碼新聞真實觀研究,[37]對數碼媒介體制展開比較,[38]亦將提示人們在日常生活和智識思考兩方面與良莠不齊的資訊長期共存。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全媒體時代提升政治傳播效力與媒介體制韌性的跨國比較研究」(批準號:23BZZ097)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Chadwick, A.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3-4.
[2]Edgerly, S.,& Vraga,E.K. Deciding What’s news: News-ness as an audience concept for the hybrid media environment [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20,97(2): 416-434.
[3]Reese,S. D. The i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Conceptualizing the press in a hybrid media system [J].Digital Journalism,2021,10(2):253-266.
[4]Graves,L.Boundaries not drawn [J].Journalism Studies,2018,19(5): 613-631.
[5]Humprecht,E., Esser,F., & Van Aelst, P. Resilience to online disinformation: A framework for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20, 25(3): 493-516.
[6]張誌安, 張指晗. 社群新聞的混合文化實踐及其專業化可能——以南京大學「核真錄」為例[J].新聞與寫作,2019(12): 59-65.
[7]Adger, W. N.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24(3): 347-364.
[8]Perusko, Z., Vozab, D., & ?uvalo, A. Media audiences| Digital mediascape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audience practices across Europ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9),23.https://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3447.
[9]Meserve, S. A., & Pemstein, D. Terrorism and Internet censorship [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20, 57(6): 752-763.
[10]Khaldarova,I., &Pantti, M. Fake news: The narrative battle over the Ukrainian conflict [J].Journalism Practice,?2016, 10(7):891-901.
[11]Romanova, T. A., Sokolov, N. I., & Kolotaev, Y. Y. Disinformation (fake news, propaganda) as a threat to resilience: Approaches used in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 Lithuania [J].Baltic Region,?2020, 12(1): 53-67.
[12]劉沫瀟,姜飛. 新實用主義真理觀視閾下西方事實核查實踐探究——以RMIT ABC Fact Check為例[J].新聞界,2022(02): 87-96.
[13]浙江大學事實核查研究小組. 中美核查新聞生產的比較分析——以俄烏沖突為例[J].全球傳媒學刊,2023(04): 90-112.
[14]陳金.賦權、技術與規範:獨立事實核查在英國的發展與流變[J]. 新聞知識, 2021(10): 9-14.
[15]陳雅賽. 日本網絡新聞事實核查實踐與啟示[J].青年記者, 2020(10):84-85.
[16]向芬,楊肇祎. 全球新聞創新共同體:基於事實核查工作方式的比較研究[J]. 新聞記者,2023(02): 32-45.
[17] Holloway, J., & Manwaring, R. How well does ‘resilience’ apply to democracy? A systematic review [J].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22,29(1): 68-92.
[18]Chandler, D.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ideology of resilience [J]. Politics, 2013,33(4): 276-286.
[19]Afifi, T. D. Individual/relational resilience [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46(1): 5-9.
[20]Theiss, J. A.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resilience [J].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8,46(1): 10-13.
[21]Bean, H. National resilience [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46(1): 23-25.
[22]Houston, J. B. Bouncing forward: Assessing advances in community resilience assess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ory to guide future work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15,59(2): 175-180.
[23] Houston, J. B.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communication: Dynamic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and among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organizations [J].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46(1):19-22.
[24]Brgoanu,A., & Radu, L. Fake news or disinformation 2.0? Some insights into Romanians’ digital behavior [J].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2018,18(1): 24-38.
[25]Bourbeau,P.A genealogy of resilience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18,12(1):19-35.
[26]Bourbeau,P.Resil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mises, debates, agenda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5, 17(3): 374-395.
[27]Houston, J. B., & Buzzanell, P. M. Communication and resilience: Concluding thoughts and key issues for future research [J].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8,46(1): 26-27.
[28]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Scheffer, M., Chapin, T., & Rockstro?m, J.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15(4): 20-28.
[29]Baldersheim, H., & Keating, M. (eds.) Small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Vulnera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16: 16-17.
[30]Tandoc,E.C., Ling, R., Westlund, O., Duffy, A., Goh, D., & Zheng Wei,L.Audiences’ acts of authentication in the age of fake new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8): 2745-2763.
[31]Humprecht,E., Esser,F., Aelst,P.V.,Staender,A.,& Morosoli,S.The sharing of disinformation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nalyzing patterns of resilience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3, 26(1):1342-1362.
[32]Boese,V. A., Edgell,A.B., Hellmeier, S., Maerz, S. F., & Lindberg, S. I. How democracies prevail: Democratic resilience as a two-stage process [J].Democratization, 2021,28(5):885-907.
[33]Buzzanell, P. M.,& Houston, J.B.Communication and resilience: Multilevel applications and insights.A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um [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8,46(1):1-4.
[34]Capano, G., & Woo, J. J. Resilience and robustness in policy design:A critical appraisal [J]. Policy Sciences, 2017, 50(3):399-426.
[35]Reid,J.The disastrous and politically debased subject of resilience [J]. Development Dialogue, 2012,58(1): 67-81.
[36]Dahlmann,O.Security and resilience [J]. Resilie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Humanitarianism, 2011,2(1):39-51.
[37]吳濤,張誌安. 新新聞生態系中的事實核查及對新聞真實觀的影響[J]. 新聞與寫作,2022(07): 37-45.
[38]哈林·曼奇尼, 比較媒介體制: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M].陳娟, 展江,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4-5.
本文參照格式參考:
劉於思,閆文捷,周睿鳴.作為媒介體制韌性要素的事實核查:中國實踐與全球經驗[J].青年記者,2023(23):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