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思·亨利(Michel Henry,1922—2002),現代法國哲學的重要人物,他從胡塞爾現象學出發,關註主體性和個體的內在感受,最終發展出極具深刻洞見的哲學體系。亨利的哲學作品涉及眾多領域,代表作有【顯現的本質】【身體的哲學與現象學】【馬克思】【精神分析的譜系學】【野蠻】【看見不可見者】【生命與揭示】等。
本訪談刊於【異樣】( Autrement )雜誌,第12期,1993,「好奇、知識的眩暈」(La curiosite,vertiges du savoir)。好奇被引向其原則,一種看的欲望,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不僅被渙散所威脅,而且因此錯失了不可見者的廣泛領域:藝術、倫理和宗教——胡塞爾的希望,即對於精神的某種普遍主體性的希望,如同黑格爾的絕對知識的野心,遭到了摒棄——「不可見者是最為確定的」,康定斯基的理解——宇宙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其現實性,正如我們的生命是變動的、遭受的生命——唯有對於不可見者的待命,能夠使好奇變得合理。[譯註]拉布魯斯(1968— ),哲學博士,詩人、作家,其研究兼及哲學和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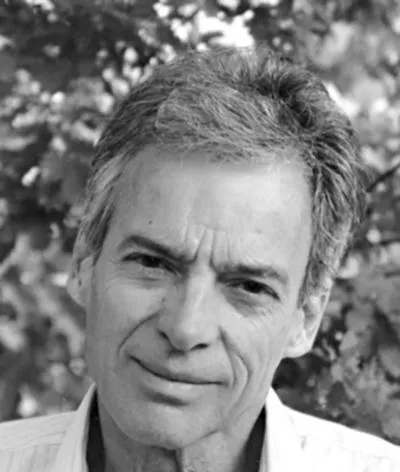
妙思·亨利
拉布魯斯(Sébastien Labrusse)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人們通常認為好奇誕生了知識和求知欲。然而,帕斯卡爾蔑視那些「在科學中鉆研太深」的人,宣稱好奇是徒勞的、無用的。您是否認為,好奇——或者何種好奇——是科學的實際動機?
亨利: 我堅信,好奇是科學的實際動機。這一點甚至應當引起我們的註意,因為,如果我們仔細反思這一點,這個簡單的命題隱含著,科學有著一個外在於科學、先於科學的動機。說科學的動機就是好奇——怎樣的好奇我們會再說——這意味著,科學源自我們的生命,並且在我們生命的某些特征中,因為好奇是一種生命的模式。然而,科學似乎表現為自身構成自身的基礎;於是,在這裏涉及一種理論的發展,這種理論發展不僅能夠證明它所建立的一切,而且,在一種反身行動中能證成自身的前提;一個完全自足的思想系統得以建立起來,其嚴格性、其結果、其價值,都是不可置疑的。將知識(作為一種認識)與好奇聯系起來,這意味著科學包含在某種不同於自身的東西中,我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比科學更大的東西。科學有一個在先者,這個在先者非常重要:因為,即使在一種面貌頗為可疑的好奇的形式下,這個在先者才出現,就好奇是一種生命運動而言,這意味著:這種令人贊嘆的科學,自治的、客觀的、宣稱具有普遍性的科學,屬於某種我們還未曾言說的東西,這就是生命。好奇,作為求知的欲望,也就是去看——認知(savoir),就是看到(voir)——因此,好奇來自某種不同於認知的東西。先於認知,有一種想要認知的欲望。這種好奇雖然是多義的,卻因此表明在世界上科學認知並不是唯一的認知。知識內嵌於我們的生存之中。這在我看來才是最本質的。這樣一種求知的欲望,後來變成科學,但並不孤立於一切環境。有著另一種東西,知識並不能獨立發展,而是不得不關聯到一定的環境,帕斯卡爾就談到過這種環境,從而無法追問到知識的最終論證。在這裏已經出現一種關於好奇的倫理學的出發點。
拉布魯斯: 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專門用一章來論述好奇(譯註:參見【存在與時間】第36節),揭示出好奇與「存在者的嘆為觀止的靜觀」毫無關聯,並且指責好奇如同某種多動癥,「到處都在而又無一處在」。如果渙散是好奇所固有的,好奇就成為註意力的障礙,您是否認為,就有人把神秘主義理解為一種靜觀態度而言,我們可以將好奇定義為神秘主義的對立面嗎?
亨利: 我認為,當海德格爾分析好奇之際——在他的著名論述中,他將好奇比作某種跳躍,只是跳到某個地方,然後再跳到另一個——他就限制了提問。為什麽?因為海德格爾所談論的,是當代世界特有的一種好奇,是今天的時代特有的好奇,與我們的媒體世界相關。在這一點上,我們只能表示贊同。然而,時事的特征是什麽?就是某種昨天還不曾有、明天已然不在的東西。在時事之中,有著某種突發式的出現,卻是在一切深刻的歷史之外,在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外,在一切持續性之外。時事的影像來到這裏占據了精神的一個瞬間,然後立刻就消失了。時事,其特征在於瞬間性,顯現出第二個特征:無意義。因為,當時事到來時,人們觀看它,但因為時事是無意義的,立刻就會消失,從而讓位給另一件時事。說到底,人們從一個瞬間跳到另一個瞬間的這種時間性,是海德格爾關於好奇的分析基礎。當代人的好奇是被制造出來的,關於這一點,海德格爾當然有道理。這樣一種好奇,似乎與註意力相關,但恰恰是要求註意力馬上從一個物件跳到另一個物件。因此,在這樣一種觀看中,有一種內在矛盾,因為這雖然是一種觀看,但是其真正的興趣並不在他所看到的東西,而是放棄他所看到的東西,從而轉向另一個東西,而後者馬上也將遭受到同樣的命運。由這種好奇出發,我們還可以恰當地談到人們想做的一切壞事。

【存在與時間】書封
拉布魯斯: 但這是不是海德格爾自己的批評?海德格爾對好奇的指責,是否仍然在傳統中?
亨利: 是的,這其實回到了帕斯卡爾的主題。實際上,好奇的這樣一種碎片化,也是媒體世界的發動機,在今天已經發展到極度誇大的地步,但是一直以來都存在。因此,必須深化關於好奇的分析,這種好奇是對某物的好奇,但又立刻放棄,因此得承認,這種好奇總的說來只是對自身的一種逃避。它一直與某種並非自我、僅僅只是一個事件的東西緊密關聯;但緊密地關聯於來自外部的某種東西,在外在性之中尋求,從結構上來說,這就避開了一個領域,即探索自身的領域。這已經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貶低,從而去關心一個全無利益的領域,而這個領域呈現的特殊性就在於並非自我。然而,不關心自身,這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就是絕望。因此,我相信,好奇的特征之一就在於總是朝向外部——在這裏,觀看本身也被質疑——就此而言,好奇實際上是可疑的,因為必須理解的是,好奇似乎把我們帶向某種東西,我們必然背離某個其他的東西;它使得我們朝向外部,但是它也使我們背離並非世界的某些東西,即背離我們的生命本身。
拉布魯斯: 我們能否進一步說,使我們背離是它的諸種功能之一?
亨利: 是的,這種功能有一種價值:對於在世界中到來的東西保持註意。然而,正是因為這一點,好奇從其本質上來說是模棱兩可的——與這種價值相關聯的,是一種根本性的反價值(antivaleur)。這意味著,對某種有趣的東西感興趣,卻又對那無疑更重要的東西(我稱之為「生命」)不感興趣。因此,如果這種渙散(這種渙散就在於對自身的偏離)是好奇所固有的,我不確定,是否必須用註意力來與之對立,在一定意義上,註意力顯然高於好奇,但註意力仍然屬於觀看與可見者的宇宙。註意力是一種意指,與好奇相反,註意力持續地關註它所要看的東西。因此,註意力想要開啟的程式,在於讓可見者真正呈現出來。實際上,這種在場可以抵達的,或者是一種直觀,或者是一些分析。但註意力和好奇一樣,都是觀看的模式。註意力是一種本真的模式,而好奇,則是一種飽受質疑的模式。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在閱讀了【野蠻】後對我說,他曾用他的一生來關註微觀物理學中的粒子問題,這確實是一個令人贊嘆的宇宙,但他發現,在這段時間裏他從來沒有關註過自己。因此,正是個體,作為獨特的自身,作為本質性的東西,在這樣一個觀看的宇宙中陷入沈默,在此意義上,這種宇宙是在那些被看見的東西之中才被給予的。
拉布魯斯: 如果透過人們自然的好奇傾向,從而讓科學持續地進步,對於人類而言,在這樣一種想要全方位地認識一切的意誌之中,是否有一種風險?實際上,您在【野蠻】中分析的,不僅僅是文化危機的主題,也是關於文化的摧毀的主題,您曾經將這種危險和摧毀關聯到科學與技術的首要地位。您如何解釋這種文化的死亡,也就是說,藝術、倫理、宗教的死亡,似乎這與好奇的死亡並不是同時發生的,因為知識越來越復雜並且專業化?
亨利: 答案也許已經在前面概括出來了。為什麽文化的危機殘留在好奇之中,以及危機恰好就來自知識?恰恰因為,在萬物的本性之中,也許本來就應當存在兩條可供人類前行的不同道路。人類,順著好奇的道路——即使在這個詞的較高貴的含義中——發展出了專門化的知識;也留下了另一條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人們將遇到藝術、倫理和宗教。在諸如蘇美爾、埃及等古代文明中,知識的發展伴隨著文化的綻放。二者齊頭並進。而在我們的現代世界中,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悖論:一種分離,一方面是科學知識的高度發達,以及各門學科的互相分割,另一方面,則是文化的衰落。但是,如果文化在另一個區域得到發展,有著不同的好奇、知識與觀看的區域,這種悖論也特許以得到消除。因為,文化屬於不同於客觀知識的另一種秩序,對客觀知識的聚焦,卻導致了對生命領域中的其他一切的偏離。然而,文化屬於遭到客觀知識遺棄的生命的領域。但是,除了科學知識外,是否還有客觀知識將物質宇宙主題化,並且將目光投向它呢?如果有,那又是什麽知識呢?這就必須要加以分析。
拉布魯斯: 是的,知識在今天已經碎片化了。您是否認為,哲學能夠重新具有一種野心,實作知識的統一化,而且這種哲學既不混同於科學,也不再指向上帝?
亨利: 我相信,有一個明顯的答案能夠回應您的問題,那就是胡塞爾的哲學。胡塞爾完全信服嚴格科學知識的理想的合法性,他把知識的碎片化視作一個難題。胡塞爾清楚地看到,諸門科學在取得進步的同時也變得四分五裂,這些科學使得不同類別的研究成為可能,而每一種研究為了取得進步,都不得不發明一些新的概念體系,簡單說來,每門科學都與其他科學分離開來,毫不誇張地說,簡直有爆裂的危險:這是一種斷裂的知識。如果人類的統一性,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協調一致,應該基於知識——這個預設是我不能同意的——如果有著一種人類的道德統一性是以知識的統一性為前提,那麽這種知識的破碎確實是極度危險的。對於這種碎片化,胡塞爾的回應在於,某種統一性是可能的,只要人們理解到諸門科學都是由同一種心靈的活動產生的,而這種活動,胡塞爾命名為「先驗主體性」。例如,胡塞爾很好地揭示出,幾何圖形與抽象關系在大自然中並不存在——價值也不存在。因此,我們不能把這些科學中的實在視作客觀實在。我們應當理解,是人的精神產生了這些實體。完成這一運動,從客觀性回到建構出這些客觀性的創造性活動,也就是重新找到統一性的家,因為同一個精神能夠創造出這些科學。對於胡塞爾而言,如果我們能夠回溯到他稱之為建構性主體性的這種主體性,那麽我們就重新找到了統一性,這種主體性不是個體的,而是一種普遍精神的主體性。就此而言,確實是一種令人贊賞的解決方案,能夠以某種方式從知識的宇宙中將人拯救出來。如果諸多知識之所以如此破碎,只是因為在其客觀面向中來考察,也就是說在其意向相關項之中,或者說是被思考的面向,那麽,在其意向行為的面向中,在思想的面向、在能夠思考的面向,我們又重新找到這種根本的統一性。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同樣在其創造能力中找到一個自由的人,不同於作為物件的人,即被簡化為分子和原子的人。人的先驗的人性,能夠在這種知識的宇宙中得到拯救,只要我們將自身理解為一種整體,而不是還原為意向行為的面向,還原為進行思考和創造的思想,而是作為一種無限的自由的精神——盡管我們的產物似乎是外在強加給我們的一些客觀性。
因此,胡塞爾提出的確實是一種相當精彩的解決方案,但是正如我剛才和您說過的,這並非我的方案。為什麽呢?首先是因為,這些建構性活動必須是能夠被揭示出來的,但這些活動是匿名的,我們看不到;這些活動生成了那些我們能夠看到的東西,但是這些活動本身卻是在某種匿名性和不可見性中完成的。於是從這裏,我們要指向另一種維度。關於一種自身不可見的事物的認識,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由此,可以知道現象學方法的全部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我采取了一種非常批判性的態度,雖然我也是現象學家;我在後面會講到實際上不可能獲得一種關於這種暗夜中的、神秘的主體性的任何知識——這也是我對胡塞爾的批判——這樣一種主體性所生成的,不僅有科學物件,還有物件本身。我們能夠揭示出物件之所以在此,僅僅因為有著某些感知行動,這些感知行動建構了可感材料。我們的世界,不是一個完全現成的世界。世界的建構是某種特別復雜的綜合活動的結果,這些活動仍然有待澄清。於是,在這裏就涉及要去澄清和認識這些建構活動,我的觀點與胡塞爾相反,這些活動是不可能透過觀看來加以認識的——透過一種簡單的目光的轉向,這種轉向所能做到的,僅僅是使目光不再朝向物件,而是朝向主體。我們不僅有關於可見世界的經驗,還有關於生命活動的體驗,然而並非透過觀看。生命並不窮盡於知識的活動之中。知識活動只是生命的一種模式,然而,生命還有很多其他的模式。這就是為什麽,胡塞爾關於科學知識的令人贊嘆的反思,仍然是片面的。因此,發現知識統一性的可能性,並不位於被建構的、意向相關項的這一側,而是在建構性主體的活動這一側,後者最終隱含著對生命的認識。
拉布魯斯: 現在提一個關於好奇的倫理學問題。您是否認為,好奇在倫理領域也有一席之地?有人曾說過,人天生就是好奇的。因此,就此而言,這是一種自發的態度,一種倫理態度(ethos)。然而,實踐一種好奇的倫理,這是否合適,這是否意味著,對好奇加以衡量和約束,在這種情況下,要以何種價值的名義?
亨利: 如果好奇將科學知識紮根於早期的運動中,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將好奇視作在認知和科學方向上的延展,相反,必須把好奇回溯到使之可能的背景中,科學本身也要內嵌到這樣的背景中,並且,在這些條件下,我們應當向主體提出一些倫理學問題,既然好奇在此處呈現為一種自發的態度,從而也是一種生命的運動。因此,好奇把我們帶回這個領域,也就是倫理的領域,也就是說,在這個倫理的領域中,對於生命及其各種自發的運動加以追問。好奇是一件好事嗎?這種生命的自發態度,尋求觀看並且進而尋求科學的認知,這是否合法?誰來評價這種好奇?但是,各種價值並不足以用來判斷好奇,因為這些價值本身就成問題。誰來提出這些價值?有一個評估的原則。這個原則是怎麽樣的,它本身是否具有價值?這就是倫理學的主要問題。好奇,原本只限於科學式觀看,透過其背景,突然地提出了關於人性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無法以程式化的方式回答。因此,我只是暫且可以說,倫理學指向生命的領域。為什麽?因為在科學所運作的世界或者宇宙中,根本不存在價值。為了獲得價值,就必須有某種評估。那麽,這個不是理論的而是實踐的評估原則到底是什麽?這就是生命。這種評估體現在何處?生命就萬物與生命的關系來評估萬物。生命是有害和有益的標準,這一點首先從食物開始。在大地的地表上所生長出來的東西,就這個層面而言,就已經有了價值學意義上最原始的區分對待。緊貼著生活世界的地基,有著各種價值——生活世界(Lebenswelt),如胡塞爾所用的術語。如果用海德格爾的說法,從那種粗野的存在者出發,這些價值將是無法解釋的,只有關聯到生命,這些價值才可以得到運用。生命就是一切原則的原則。但評估生命的價值是怎樣的呢?這些評估的合法性又是怎樣的?唯一支持這一點的就在於,生命本身所設定的價值是好的,就是肯定和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好的。正因為生命是好的,所以這種評估系統也是合法的。我們可以假設一種邪惡的生命,或者如尼采所說的,一種病態的生命,它會使價值發生顛倒。一種本真生命所持有的所有價值,因此都可能被視作錯誤。對好奇的評估之所以可能,也只有從一種並非病態的生命出發。病態的生命,也將是一種絕望的生命,一種拒絕生命的生命,逃避自身,整天從事科學,僅僅關心客觀世界和物質世界。
拉布魯斯: 禁忌呼喚著僭越,也會激發著好奇,第一次好奇,就是亞當和夏娃的好奇,是想要認識善與惡進而獲得不死的能力的一種欲望。好奇與僭越有怎樣的聯系,在哪方面好奇又是與上帝對峙上帝的?
亨利: 如果好奇是觀看的一種事實,觀看相信自身,意味著想要觀看一切和認識一切,如果這種觀看被引入一個從原則上遠離了觀看的領域,才談得上有著某種僭越。如果有一個不可見者的領域,任何一種觀看,既不能也不應進入其中冒險。即使有人偏要這樣做,最終也只是一種蠻力,必然會歸於失敗。僭越並不是一種倫理的前見,而是一種純粹哲學的、現象學的問題。是否存在一個不可見者的領域?如果不存在,我看不到有何種僭越能夠透過好奇而運作起來。如果不可見者的領域是存在的——如果生命就屬於這個領域——那麽,想要看見不可見者的意誌,就已經是一種僭越。但是,這一意誌將歸於失敗,因為您也許總是能夠解剖一個大腦,進行掃描,但是您永遠不能因此明白什麽是笛卡爾意義上的我思之物,也就是說一種純粹的關於自身的經驗。在哪方面,好奇將引向與上帝對峙?當然,這裏只需要假設說,想要看見生命的意誌,就是一種想要看見上帝的方式,並且將其歸結到我用我的目光所統治的東西,以及我能夠完全地解釋出來的東西的條件。
拉布魯斯: 如果好奇對於人類代表著一種危險,是否必須放棄黑格爾的「絕對知識」的野心,而絕對知識就是諾斯(Gnose,譯註:來自希臘語,意為一種深入的、真正的知識。通常用來指基督教的一種學說,強調對於上帝的認識是一種直觀,這種直觀是一種內心中發生的啟示,這一派的學說也被稱作諾斯替主義或者諾斯替教)的野心,追求的是關於宗教的各種奧秘的最高知識?用一句話來說,面對好奇所帶來的風險,不可知論是否是唯一的理性的解決方案?
亨利: 對於絕對知識的野心,必須追問的是,黑格爾指的是哪類知識。絕對知識是意識的知識,卻是一種物件的意識,在可見的領域內進行觀看。在一種對其自身本質的觀看之中,意識朝向自身形成表象,因此,黑格爾關於絕對知識的定義就其原則而言就已經出錯。當然,存在著一種絕對知識,但是這種絕對知識並不服從黑格爾的結構,因為黑格爾的結構是一種關於物件的意識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之中,意識始終有一個物件,物件始終與意識不相應,從而最終要去尋找一個相應的物件,即意識自身;但是,意識也將知識看作一個絕對物件。我認為,黑格爾的全部辯證法所利用的各種知識手段,相對於絕對而言都完全錯誤,只能導向失敗。此外,如果黑格爾的哲學達到絕對知識,將會是歷史的終結。然而,歷史仍會繼續……這種知識,並不是古典意識所能夠獲得的,在胡塞爾這裏,古典意識仍然是關於某物的意識。然而,我們絕對不可能像具有某物的意識那樣,獲得關於絕對的意識。確切說來,這種意識隱含著一種控制,因為,當這種知識被托付給觀看時,對於被看者就有一種支配。觀看總是多於那被看的東西。那被看的東西,之所以被看,僅僅因為有著一種觀看在觀看它——這就引導著把人的位置設想為一種知識主體。只有知識被理解為一種觀看,才會有一個主體——長期以來都是如此。主體認識的是什麽?一些物件。然而,一個物件,是我放置在我面前的東西。因此,當薩特順著這種認識模式來描述存在之間的關系時,他就讓這種關系變成目光之間的鬥爭,每個人都將他的目光投向他人,從而將他人化約為他的一個物件。在這樣一種服從於觀看與被看的結構的知識中,某種全能(toute puissance)以潛在的方式隱含在其中。因此,我們理解了,這樣一種知識就是一種支配的知識,科學引發了一種支配的技術。但是,對於這種知識,我們可以進行批判——因此也對好奇加以批判——實際上預設了某種認識。
拉布魯斯: 在【顯現的本質】中,您發展了關於某種直觀的、絕對的知識的觀念,艾克哈特大師是這種觀念的支持者之一。您談到了關於本質和不可見者的知識的可能性,似乎也在暗示某種不可知論的必然性,如何調和二者?
亨利: 如果存在著兩種類別的知識,這種調和才是可能的:一種是基於觀看的知識,另一種則是生命的認識(savoir)。如果這些認識的本質完全不同,如果涉及的是本質性的東西,如果本質性的東西是不可見的並且屬於生命的領域,那麽,關於客觀的物質世界的認識就是相對的。這並不意味著必須停止認識世界的實踐,人類認識物質事物並將其組織起來,從而讓生活得以可能,讓生活服從其目標,這非常重要。但是,這種科學知識根本無法通往本質性的東西。這種知識根本不涉及我們之所是的本質性的東西,承認這一點,就此而言可以算作一種不可知論,也就是說一種懷疑論,質疑客觀知識能夠讓我們抵達我們之所是,即作為非生物學意義上的先驗生命。實際上,這種知識只是在生物學意義上來處理生命,將生命簡化為一些粒子、分子和神經元,從而在不知不覺中把這種知識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傾向於認為僅僅存在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
拉布魯斯: 倫理學的好奇是不是更傾向於您在【野蠻】中所說的「生命的認識」(le savoir de la vie),它對立於科學的客觀知識,您能否能更精確地描述一下您所理解的「生命的認識」?它是一種宗教知識嗎?
亨利: 倫理學的好奇指什麽?它是一種與生命相聯系的好奇,而不是逃離生命。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好奇的概念,去談論一種不再是科學知識的源頭的好奇,而是一種與生命的認識相關聯的好奇。但是,在談論這種新的好奇的概念之前,讓我們精確地描述一下什麽是生命的認識。生命的認識,是一種異乎尋常的認識,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究其根源就來自這種認識,它使生命成為可能,與生命相協調,是生命的本質。例如,為了研究一部生物學專著,您讀了一本書,書中印滿了印刷符號,這意味著您擁有一種感性認識,這種認識讓您可以看到這些字母並進行閱讀;隨後到來的是另一秩序的認識,因為這些字母具有一定的意義,於是有某種意識的認識的介入,這種意識能夠形成這些字母的意義。形成意義的能力並不是一種感知的能力,因為我們的心靈能夠形成意義這種神秘的存在,即使某物並不在場,甚至無須將該物表象出來,以不同於影像的方式。在這裏,我們有一種認識,這就是意識的認識——意識創造出意義,也創造出影像。在生物學專著的閱讀者這裏,感性認識和知性認識得以如此這般地運作起來;使那些包含在詞語中的意義的理智把握得以可能的,正是意識的認識。當這位用功讀書的讀者感到疲勞,離開書架稍作休息時,他必須站立起來,並且使得這種最簡單、最原始的認識得以執行起來——這種最簡單、最原始的認識,已經參與到感性知識和知性知識之中。我們如何能夠站立、行動、走出去?
必須註意的是,那些最偉大的哲學家早已遇上這一難題。笛卡爾說了什麽?「我是一個思考著的東西」(res cogitans)。然而,「我之思維」(cogitatio)是一種不可見的東西,我們看不到摸不著,雖然這個不可見的東西是最確定的。借助這個「我之思維」,我們就已經進入生命的認識中了。然而,在【論靈魂的激情】中,笛卡爾說,如果我做夢,我在夢中看到的一切都是虛假的。關於夢的論證,笛卡爾又重復了整個傳統——但是,他也把論證徹底化了——這個論證就在於,假定我所看見的東西是虛假的,不論是感性的看還是知性的看,包括看見2+2=4的這種看。讓我們假設,理性真理的明見性也是可疑的。在我看到2+2=4之際,如果有一位惡靈在欺騙我,如果這一切只是一個夢,那麽還剩下什麽是確定無疑的?那麽,應當剩下來的,不應該是進行觀看的存在。現在,笛卡爾說,如果我在夢中體驗到一種害怕,這種害怕是真的,甚至是唯一能夠得到確定的東西。於是,這種害怕越是真實,我就越是體驗到這種認識,也就是說這種認識就越是被體驗。因此,正是對於害怕本身的這種揭示,與觀看全然無關。害怕的自我揭示,是一種遭受,一種完全獨立於觀看的先驗的感受,正是在這裏有著生命。因此,生命向自身揭示自身,直接地、無間距地,不需要任何一種觀看;這種直接性,並非一種概念,而是生命關於永不停息的生命本身的一種情感。生命的所有模式,包括知識的模式,最終都屬於這一秩序。我稱之為徹底的現象學。
關於生命的認識,我還要說,這是一種直接的認識,因此無視一切歷史、沒有空缺,因此是絕對,因為這是一種感覺,卻是一種完全地認識它自身的感覺。這種認識,與宗教類的認識是否有某種關聯?是的。為什麽?因為這裏涉及生命,生命是神聖的。正是生命,是一切宗教事物的支撐。為什麽生命本身是神聖的?因為生命的認識,不僅完全不同於基於主客分離的認識,也是一種不包含任何支配的認識。生命的特征就在於其相對於生命自身的被動性。我出生,我不是被創制的,我是根據某個事件從而在生命之中,一個我絕對無法對其負責的事件。這個境況規定著生命的本質,實際上在生命的每一瞬間仍然不斷重復產生類似的境況。我的生命,相對於生命自身而言,根本上說來就是被動的。在與自身的關系中,生命體驗著自身。體驗自身,意味著從根本上來說,相對於自身而言是被動的,也就是沒有任何首創行為,沒有自由。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沒有權利去觸碰生命。我們也不能把生命給予我們自身。我們如何有權利和能力走出這種境況?生命的本質是無法解脫的束縛。因此,有著一種持續的自身體驗,居於我們的各種能力之中,使我們能夠去觀看、行走,——但是,相對於這種根本性的能力,我們自身卻無能為力。各種宗教,都不過是以各自的方式表達了這種無能為力,這種無能為力內嵌在我的生命的被動性之中。「我是在生命之中」(Je suis dans la vie),這意味著這種生命穿透了我,這是一種奧秘。我完全地在我的生命之中,同時,我之所以在我已經接受並且持續接受的生命中,不是為了任何東西。如果我們不能給生命以傷害,那正是因為生命是絕對的贈禮。在現象學上,這種生命向自身的被動的給予,使得生命的問題關聯於上帝的問題。因為,經歷自己的生命,如同接受某種東西,這就必須體驗到對於自身的某種無限的崇敬。這已經是一種宗教。
拉布魯斯: 您的哲學是一種生命哲學。因此,為了澄清生命的現象,您在【顯現的本質】中曾致力於可見者、不可見者、揭示的研究。此外,在最近的一本書【看見不可見者】中,您還研究了康定斯基的抽象畫。好奇,如果能定義為一種觀看的意願,這種好奇與不可見者有怎樣的關系?您能否精確地描述一下不可見者的概念?不可見者是否就是奧秘?康定斯基的藝術中的精神性,是否讓我們看見不可見者?
亨利: 在【顯現的本質】中,我所做的不過是在現象學上區分了事物顯現的兩種方式:一方面,在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在生命之中。在世界之所是的光明空間中,這個空間也是一個可知的空間——透過一種思想的觀看,我看到了某種數學空間之中的圓形和三角形——這是事物得以顯現的第一種方式,預設了某種間距、某種可見性的視域;這是因為,在事物之後有某種螢幕,這些現象才得以在這個螢幕上顯現出來。這種螢幕是一個先驗的螢幕,海德格爾的哲學最終就是對這個視域的描述,對於海德格爾而言這個視域就是時間。這就是他所說的「綻出」(ek stase),也就是一種根本性的「在外面」(au dehors),正是「在外面」才浮現出事物的現象性。根據現象學,意識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在外面的。因此,我就存在於與事物的關系之中。
上述這些都是對的,但也是片面的。【顯現的本質】一書就致力於重新考察這些描述,並且揭示出這些描述的有效性及其限制性,因為它們使一種更原始的揭示方式變得完全模糊,這就是生命之所是的方式。我的提議在於,這種揭示方式在其自身之中,完全不同於在外部性之中的萬物的呈現方式。這種揭示是一種感受,一種原始的自身感知(se sentir),這就是我們的存在的肉身。因此,對某些事物的一切感知,都預設了感知的自身感知。我們的生命正是居於此處。世界就其總體來說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我們首先在生命之中。我們向世界的敞開是一種生命的事實,這種敞開應該抵達一個點,在這個點,生命在完全沒有光的直接性中體驗著自身。這是一種不可見者,也是最為確定的。從現象學的觀點來看,不應該將不可見者一詞視作否定的。不可見者實際上意味著揭示的第一種形態,即最根本的卻是隱秘的,因為我們不能看到它,但毫無疑問,因為那自我體驗到的東西,我們不能說沒有體驗到。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生命得到了揭示,我將其看作源始的揭示。
我一直很喜愛繪畫,但是有一天,我發現了康定斯基的精彩著作,在其中我看到了對生命現象學的某種闡明。康定斯基對繪畫的分析,在我看來,恰好印證了對可見者與不可見者的現象學分析,不可見者才是本質性的。這種證明令人心血沸騰,不僅因為這是由一位天才創作者寫出的,也因為這同時是關於可見者的分析,因為繪畫是一種視覺藝術。康定斯基的直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他認為繪畫所表象的並不是外在世界,而是我們的靈魂,不可見者!這個充滿想象力的計劃預設了我們有一個靈魂,靈魂是不可見的。但這如何可能?如何畫出靈魂,使之被看到?這就是美學問題。康定斯基指出,顏色不僅僅相關於視覺,顏色也在我們內心形成印象:顏色不是一種客觀的性質,它能夠作用於我們的感受。康定斯基關於顏色動態的分析非常精確,不論是令我們激動的黃色,還是令我們平靜的藍色。激動、平靜,都不過是我們心靈的一些樣態。因此,我們能夠證明一切顏色都是雙重的:既是可見的,又是不可見的,但是不可見者才是其真正的實在。因此,一切的圖形因素,既是內在的也是外在的。康定斯基就主張,一切圖畫都基於不可見者,不僅包含抽象畫,人們選擇一種顏色是由於這一顏色的變動的、情感的權能。從而繪畫就構成了一種證明,本質性的實在是不可見的。因此,繪畫所給予的不僅是讓人觀看,而且讓人感受。繪畫使不可見者得以被觀看,根據繪畫所讓人感受到的東西的比例。繪畫讓人更多地感受可見者,而不是讓人看見不可見者,因為繪畫使得可見者變得不可見,這才是繪畫的深層的本性。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將證明擴充套件到世界,世界也是由一些形式和顏色構成的,並且證明,這種揭示也是雙重的:所有的東西,既被揭示為在我之外,也被揭示為在我之中的生命的發展。我相信,正是這一點能夠還給世界以其本有的詩意,以及心靈之所是的這種肉身。這個肉身,就是我們之所是。因此,就我們的生命是一種變動的、感受的生命而言,宇宙的實在就在我們的生命中。
拉布魯斯: 在【顯現的本質】中,您評論了艾克哈特大師的表述「人,認識上帝者」(Gottwissendermensch)。我們能否說,在您看來,關於這種認識,人對上帝感到好奇?反之,在這同一個傳統中,我們能否說上帝對人感到好奇?
亨利: 這讓我們返回好奇,並更精確地定義好奇。我們可以看到,好奇實際上意味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因為,如果我們把好奇定義為一種求知的欲望,而沒有把這種認識與觀看聯系起來,那麽我們可以說人對上帝感到好奇。在這個尺度內涉及的就不再是觀看,而是沈浸在一種揭示之中,最終沈浸在一種情感、一種情緒中,好奇就取消了一切的活動,一切的激動,一切的統治,從而去思考,有可能體驗一些我們從來不曾體驗過的東西,因此采取一種完全被動的態度,從而能夠獲得一些從未經歷過的體驗。尼采談到了人的「最大的追獵」。我的理解是,這不是朝向外部、朝向可見者,而是朝向人的內在經驗。在這方面,人類也特許以感受到一種強度更高的實踐,超過到目前為止所經歷到的一切。藝術,是那種能給予個體一種可能性,使他們能在自身中感到從未體驗過的力量與情感的一種宇宙,給他們敞開一些更強大、更高的生命形式。於是,我們可以承認好奇,好奇是這樣一種待命,能夠承擔某種類別的信仰,也就是說讓某種具有優越性的經驗得以可能:其中愛是啟示,一種內在的歡樂和某些審美經驗。這些歡樂,讓存在的某種擴大得以誕生,即朝向無限制性和不可見者的擴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對上帝感到好奇。正是艾克哈特大師指出,一種期待和謙遜的態度,能夠讓我們通往一些我們原本不知道的歡樂。一個從來沒有愛過的人,是不知道愛帶給人的歡樂有多強烈的。閉上雙眼,某種好巫師能獲得其自身的充分權利。誰知道人的生命被賦予什麽?
因此,我們能否反過來說,上帝對人感到好奇?對我而言這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麽呢?我一直想讓人們理解,存在著兩種生命,一種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一種是先驗的生命。使我的生命變得活生生的,乃是在絕對意義上的生命。僅僅在我的生命中,我才能夠註意到在我之中展開的這種絕對的、無限的生命。因此,如果我對上帝感到好奇,我也許能夠體驗到這一運動。但是,我無法置身於這種無限的生命中,來說這種無限的生命對我感到好奇。因此,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在這種無限的生命中,我一直都只是被動的。無限的生命總是先於自我,根據我能夠對其有所體驗,我又與之同時俱進,但總是存在著某種出生之前的東西,在自我之中運作著。我能夠以現象學的方式描述我所體驗到的生命,並且顯示出在我之中的生命的本質,但我不認為我可以成為這種絕對的生命,以這種絕對生命的名義來言說。因此,當涉及這種絕對的無限的生命,追問就不再有效。追問,就是提出一個問題,並超越這個問題進入一個視域,並從這個視域出發來考察人們所言說的東西的合法性。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問為什麽,也就是進入一個外在的設定,透過這個外在的設定,人們才能夠提出「為什麽」的問題。這種追問,對於與生命相關的一切而言卻是不適應的。生命從來都不會外在於自身,生命也不在某種視域之中呈現,因此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十分荒謬的。這也是西勒修斯(Angelus Silesius,譯註:1624—1677,出生在波蘭的神秘主義神學家。海德格爾在【論根據的本質】一文中也參照過這首詩)的話中之義:
玫瑰不為什麽,盛開只是因為盛開,
它既不在乎自身,也不想要被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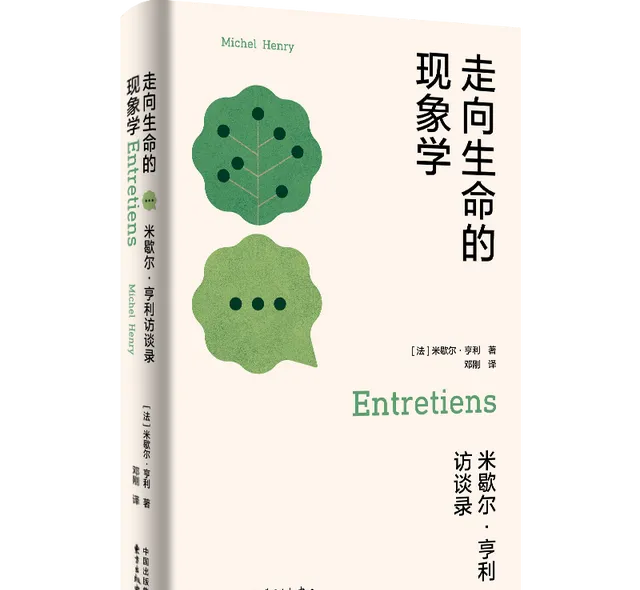
(本文選摘自【走向生命的現象學:妙思·亨利訪談錄】,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