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約克(Tom Yorke)和強尼·格林伍德(Johnny Greenwood)想在三人樂隊The Smile裏得到什麽?有什麽是只有他們二人和爵士鼓手湯姆·斯基納(Tom Skinner),以及偶爾加入的薩克斯手羅拔·斯蒂爾曼(Robert Stillman)在一個新名字下能完成,Radiohead不可以的?
一個原因是,格林伍德再也忍受不了Radiohead在錄音室裏的工作方式了。他的耐心被耗盡。早在2009年約克就告訴媒體:「格林伍德雖然受不了我們的工作節奏,他對一些靈光乍現,又被樂隊棄之不用的素材很感興趣。」
「拜托,來點強力的。」「好啊。」約克同意了。
2016年的【A Moon Shaped Pool】之後,Radiohead成員各自投入繁忙的個人計劃,樂隊貌似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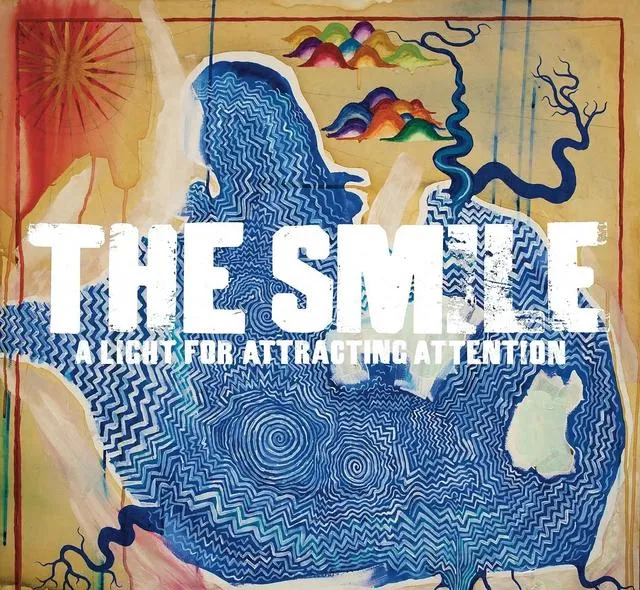
【A Light for Attracting Attention】封面
2022年,湯姆·約克和強尼·格林伍德的The Smile首張專輯【A Light For Attracting Attention】發表,建立新樂隊的音景。電吉他自我解放,和鼓點一起搏動。像止不住的眼皮跳,預示的是不祥還是好運尚未可知。Radiohead是黃昏,The Smile就是清晨。晨露猶新,要經過一整個漫長的白天,才會來到憂郁的黃昏。
放下Radiohead的名字,The Smile無需盡全力保持住內聚力。約克和格林伍德變年輕,使The Smile在疲倦、多疑、陰郁和不公的世界裏,抱擁一線希望。在猶疑不決的時刻,器樂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一直在破除搖滾陳規的Radiohead,在微笑中拾起一些傳統,好告訴大家:鉛灰色的天空若傾下暴雨,也定會迎來晴天。
包括約克和格林伍德,聽音樂和做音樂的人都在變老。如果新的作品不好聽,悲傷、焦慮、嗔怒又有何意義?真實的東西,原來也可以很美麗。

The Smile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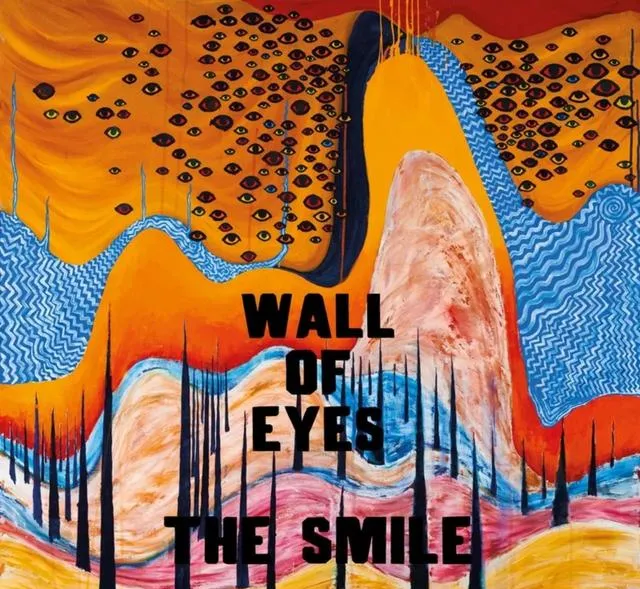
【Wall of Eyes】封面
從第一首乘Bosa Nova的風跳躍而來的【Wall of Eyes】開始,在滿墻窺視的電子眼後面,你還是你嗎?日常變成醒不來的夢魘,溫暖的熏風仍在徐徐吹送。「One, two, three, four, five……」無序的音符不改美麗的律動。「我能在下一個早晨醒來嗎?」
(【Teleharmonic】)起初斯基納的打擊樂像絲綢下隱現的凸起,與合成器的遙遠鳥鳴呼應。你要把我帶去哪裏?再會,再會。再見時你會在冰裏,還是火裏?這首歌曾以另一個名字出現在【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中,在另一個湯姆(男主角湯米·謝爾比)噩夢裏扭動。
但它沒有遁入虛空。接下去的兩首【Read the Room】【Under Our Pillows】,一躍重返熱鬧人間。前者的吉他riff太好聽,好聽到需有更靚的音階來接住它。Motorik的節奏滾出豐富的紋理變幻。約克邪氣又優雅的唱腔罵人時亦不失莊重。「當時機成熟,結局到來,也許你無法,你根本不可能無動於衷。」(【Read the Room】)
【Under Our Pillows】神經質的樂句啟用沈睡的神經,「枕頭下傳來如此的欣悅」。在人人被迫和人分享血肉的今天,「我」拒絕被眾人分食,拒絕改宗換信。不知不覺,光輝的電吉他被烏雲遮住。人聲退場後,還要耐心等待兩分鐘,才能等來陽光穿透雲山。嘲諷還在繼續。【Friend of a Friend】,露台上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電話總是占線,問題拖延不決,你口袋裏的錢,怎麽跑去了那個人的口袋裏?溫馨的民謠開場,步入竊竊私語的怪異場面。弦樂升起,鋼琴下沈,歌聲像一根絲線拉住兩端。想要彌合矛盾,最終還告失敗。
所以,【I Quit】。「我投降,我的腦袋被點燃。這是旅途的終點。」吉他的微風,輕吹後腦勺的發絲。存在一條新的路,不知通往何處,但願路上沒有瘋狂。

The Smile組合
八分鐘的【Bending Hectic】是一個長鏡頭,靈感和【Friend of a Friend】一樣來自社交隔離期間,意大利人在各自陽台上唱歌的奇妙場景。歌裏,在意大利山區開一輛六零年代的軟頂跑車,已準備好松開方向盤沖下山崖。時間停住,「沒有什麽可以打敗我,除了我自己」。吉他音符慢煮,渣滓在水面翻滾。幾番沈浮,積聚足夠的勇氣之後,那雙手重新握住方向盤,轉向,轉向活路。它有一個像樣的高潮,像任何一個自詡為搖滾的現場。每種器樂都盡力發出最高分貝,不再克制內斂,因為不知路的盡頭是什麽在等待。
一顆偏執的心繼續前進,蕩入鋼琴、弦樂與合成器的宇宙氛圍。「你說你對我了如指掌,這不可能。水下的城鎮裏,沒有什麽是我的。」
(【You Know Me!】)是這樣的。聽歌的人,即使唱歌的人以鋒芒對你,你對他一無所知,只要好聽,就放下防備,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