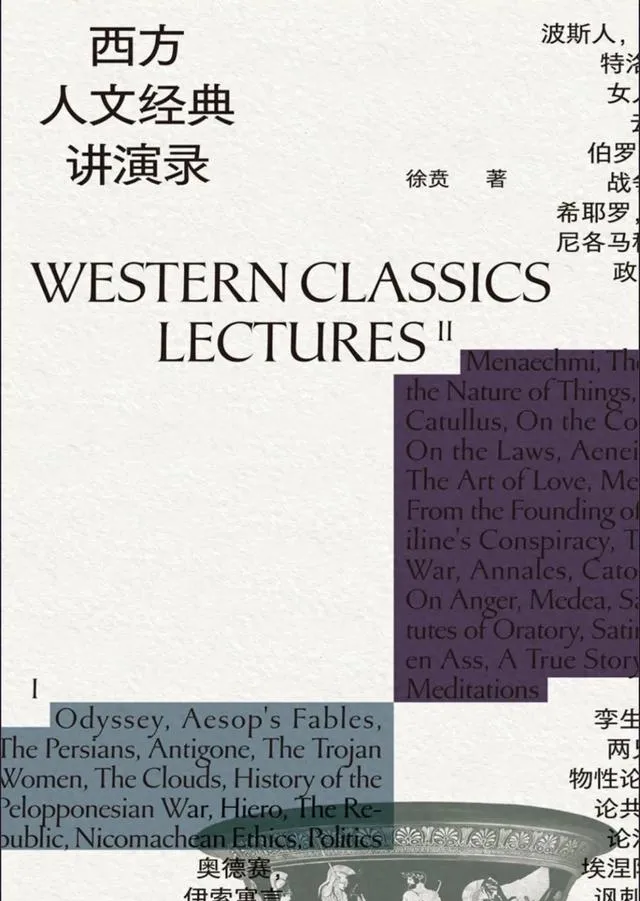
1、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创作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记录了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各自盟友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同,修昔底德采用了更加严谨和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被视为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修昔底德出生于富有的贵族家庭,35岁就担任希腊军队的将军,由于一次征战失败,被雅典的公民议会判处流放,直到战争结束。流放期间他四处旅行,收集材料,从事他的历史写作。修昔底德去世是在战争结束后第四年,此前他似乎一直在写这部著作。他去世后,遗稿被编辑为八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3、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是讲述这场战争,而不是写一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是历史学的产物,「历史学」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史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不仅是史实本身,而且注重对史实事件的起因与后果的分析、评价。这样的历史学在古希腊时代是不存在的。
4、战前的斯巴达内部辩论,辩论双方都诉诸「爱国」这个基本价值,尽管斯巴达国王发言较长,主张和分析都显得相当理性,以劝说斯巴达人从长计议,谨慎行事;但还是不如主战的监察官,几句口号式的、不到国王的七分之一的简短发言更能打动听众。
5、这样的辩论场景在今天能够给我们很大的联想空间,让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这似乎是一场显示爱国主义的辩论。反抗雅典,这是斯巴达人最容易表现也最容易接受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这种公开表决的场合,就算有普通人同意国王暂不宣战的说法,他们也不太可能像国王那样公开说出来。
6、修昔底德让我们看到,这种和说话的人的身份有关的「爱国情感」或胁迫性「爱国」,其实古代就已经有了。国王劝斯巴达人三思而后行,没有人会怀疑他「懦怯」或「不爱国」,但一个普通民众就不同了。因此,普通人会更倾向于在公开表态时做出「勇敢」和「爱国」的表示。而且由于是公开表态,「爱国」会变成「超级爱国」。
7、在修昔底德那里,斯巴达不是一个傲慢或穷兵黩武的城邦,而是一个因为雅典的崛起而感受到威胁的正常城邦。修昔底德更多的是从雅典和斯巴达人的不同性格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两个民族的性格截然相反,一个敏捷、好冒险,另一个胆小、迟缓。所以他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8、今天,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这样解释修昔底德本人对此事的观点:第一,斯巴达人惧怕雅典日益增长的势力;第二,战争是强加到斯巴达人身上的,不是因为雅典人首先攻击斯巴达人,而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就有了现实的战争危险。这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9、「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是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但事实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身无法支撑艾利森的说法。因为仔细阅读第一卷可以发现,修昔底德并没有把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为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相对能力的变化充其量只是战争的间接原因,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10、在斯巴达内部确实有「战争派」和「和平派」的分歧,然而,「战争派」并不害怕雅典,他们有信心发动一场速战速胜的行动;而「和平派」则寻求通融,因为他们对雅典的实力有准确的评估,并担心他们发动的任何战争有可能被他们的儿辈继承下来。斯巴达人参战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希腊的荣誉和地位,而这一地位受到雅典带头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威胁。
11、换句话说,斯巴达对雅典开战,不是为了权力或意识形态的争霸权,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战争并不是必然的,斯巴达人可以选择要战争,也可以选择不要战争,而「与其他事情一样,战争是他们在危急的关键时刻做出误判的结果」。他们没有在战争的火星刚闪烁的时候扑灭它,而是「允许一个遥远而无足轻重的定居点的内乱升级为雅典和斯巴达及其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全面冲突」。
12、修昔底德在书里的观点是相当清晰的:尽管有利益冲突和国民性格的不同,但战争并不是必然的,双方领袖人物都有多次可以选择不发起战争的机会,却没有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陷阱」的话,那对于真正有智慧的政治领袖而言,也还是有不往陷阱里跳的选择,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13、科西拉内战其实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代理人战争,革命的一方开始时力量较弱,因此寻求外来势力的帮助,而另一方在外来势力的干预时失去力量的优势,所以就求助于另一个外来势力。如果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还有英雄,那么屠杀自己人的内战中是没有英雄的。在修昔底德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如果内战有英雄,那么连同室操戈或者匪徒内讧也会有英雄了。
14、修昔底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革命暴力败坏公共语言的思想家。他指出,由于辞句的意义被扭曲和改变,以前的好事现在变成了坏事,而以前的坏事现在成了好事,诸如:「瞻前顾后」变成了「畏缩不前」;「不择手段」变成了「足智多谋」;「残忍」变成了「勇敢」;「同情」变成了「懦弱」;「权术」变成了「智慧」。
15、这样一来,事情便不再有本质的对错或是非分别,任何事情,我去做就是对的,别人去做就是错的。凡事都必须有敌对观念,有敌我之分。凡是敌人赞成的,我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要拥护。任何坏事,任何阴谋诡计,只要是我去做,就是正当的对敌斗争手段。敌方的任何行为都必须朝最坏处去设想,都是阴谋诡计。这种敌对思维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16、在党派和敌我斗争思维的驱使下,残忍、仇恨、暴力、不守信用、背信弃义都成为一个人在敌对斗争中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在这样的敌对斗争中,越是善于运用欺诈手段,越是不遵守常规的道德习俗,就越能获得成功和胜利。修昔底德指出,一个国家里这种政治行为的败坏,会变成国民品格的败坏。
17、瘟疫是捕捉到人性本身最深处黑暗的一个时刻。因为瘟疫让人们普遍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和无意义,因而陷入一种道德危机。人们有理由在轻松的快乐中寻求快速的满足,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做被认为是高尚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在实现这个高尚目标之前,他们是否会死死是不确定的。无论是对神灵的敬畏还是对法律的敬畏,都没有人退缩,因为人们认为无论他们是否崇拜神,都是一样的灭亡。在瘟疫之前,人们的这些倾向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被对众神的恐惧和人类的法律所压制。
18、关于「强权即正义」。「强权」的普遍原则是,你不做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你对我不是绝对服从,就是绝对不服从。强权逻辑是,打你是因为你弱,只要你弱,没有反抗的力量或手段,我就可以打击你、压迫你。强权逻辑是,希望要有希望的本钱,弱者连希望都不配。强权逻辑是,谁都是利字当头,谁都不会做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所以,分化对手,各个击破是最好的战略。既然神和人一样把实力看得比道义重要,那么强权就是天经地义、就是理所当然的正义。
19、有两种不同的双重道德标准:第一种是,对外国似乎非常友善和平等,甚至慷慨解囊、无私地援助;但对自己的老百姓却蛮不讲理、百般盘剥;第二种是,对自己人很讲道理也很有羞耻感,但却能对外国人做出非正义之事而不感到羞耻。对自己的事情,他们互相之间要求基于正义的权威,但对外人,他们却不在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