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嫂在當下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越發清晰了起來。社交平台上流傳著「90後」「00後」高學歷年輕女孩當住家保姆的vlog(視訊日記),隨著這些玩轉社群網路的一代人的分享,讓職業育兒看護在大眾生活語境中變得更加受人關註。她們看起來具備專業知識、在家庭勞動中具備一定程度的職場技能,最重要的是,能夠分擔母親的角色,給予兒童高品質的陪伴。
這些特征或許並非年輕一代專有,「賭王」的兒女們就多次公開分享自己由保姆們一手帶大,其中舐犢情深、湧泉相報的部份往往引發討論:母愛是可以被替代和外包的嗎?若不是就職於顯赫家庭,職業保姆的終身貢獻是否也有對等報酬?
有關母職意識形態的爭論常常發生在「職場媽媽」與職業看護之間。麥克唐納寫:「她本來想要一場革命,卻只能找到一個委內瑞拉人」,道出了這種探討的兩難。如今的社會框架下,存在更明晰、理想化,並且行之有效的答案——育兒的社會公共化,及其需要的政策福利和保障。在全球範圍內,不同國家亦有不同實踐。
在【影子母親】中,麥克唐納關註「微觀政治」,也即「權力在日常實踐中傳遞的方式」,其實懸置了透過廣泛的社會運動以爭取更多權益的可能性。她著眼於「母親」與那個「委內瑞拉人」之間的張力。誰在制造「影子母親」?育兒嫂的處境是否完全對等於家庭主婦?卡麥隆·林·麥克唐納在著作【影子母親:保姆、換工與育兒中的微觀政治】中探討了這些問題。
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
母親在兒童的早期發展階段要永遠在場、隨時提供關懷回應,是「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核心。具體來說,自從19世紀時以父親為中心的對下一代的教養轉變成以母親為中心,美國關於母職的論述就一直堅持孩子要由母親來「全面照顧」。麥克唐納談到這樣一種在科學性上乏善可陳的觀念是如何變成「母職理想」,並固化了以家庭為核心單元的社會結構的。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研究所(NICHD)關於兒童早期照料和青少年發展研究的第一期數據開始出現在媒體上。這一研究,尤其是媒體對該研究的「炒作」,對開創以科學指導育兒的新時代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母親要成為0到3歲兒童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戀物件(primary attachment),這種排他性的母子關系還要透過「高品質的陪伴」才能夠建立,與之配套的,是「可完善的孩子」的假說。嬰幼童的大腦在早期發展階段能夠變得更聰明、更有趣,這一假說給父母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並提出了中產階級文化理想中「好媽媽」角色的定義——如果你能培養出一個更好的孩子,就一定要這麽做,成為孩子最佳的看護者。結果是,比對自己與育兒手冊中的「理想母職」,媽媽們永遠覺得自己的母愛未達標準。

【影子母親】,作者: [美]卡麥隆·林·麥克唐納,譯者:楊可,版本: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
二十世紀以來,精神分析對新生兒行為的分析和洞察是為了打造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嗎?對理論的正本清源沒有那麽難:母親與孩子的關系是有關自我的問題,自我問題在心理學的誇大曲解中,變成了一種對個人主義的強烈渲染。其中最容易邁進的誤區,就是將嬰童想象成全然脆弱、被動的、等待照看的存在。迪迪埃·安齊厄在論述「自我-皮膚」精神外殼及其變型時,將母-子關系的二元反饋視作自我-皮膚的心理成因。在其對兒童專家貝裏·布雷澤爾頓1973年制定的【新生兒行為評估表】的分析中,我們或許能夠從嬰兒的視角看到主體的內部歷史,他們對「好父母」的內攝性認同與意識形態建制出的母親的犧牲與照拂有很大不同。
母親是最早的「他者」。梅萊妮·克雷因提出的「兩種位態」理論,使母親對於嬰兒來說有了作為「好客體」和「壞客體」的分裂,無論母親登入於哪一種位置,對嬰兒需求的滿足都不是一種施加於母親身上的衡量標準,一個母親會同時登入兩種位置,這在幫助主體確立精神邊界,通常在這一階段結束後,孩子能夠將母親領悟為一個完整的物件。新生兒在母性環境中接受復合的、合適的照料的同時,也在對周圍的環境發出訊號,以期讓照料更加精細化,同時探索物理的環境,尋找必要的刺激,以運用其潛能,激發感覺-運動的發展。嬰兒是主動的,其與母親的吸引和反饋回路是雙向的,連續反饋則帶來了內源性的控制力與心理驅動行為模型。布雷澤爾頓將這種框架概括為「母愛外殼(enveloppe de maternage)」與「控制外殼(enveloppe de control)」,前者由所有人與嬰兒獨立人格相適應的反應構成,後者由嬰兒借此圈住周圍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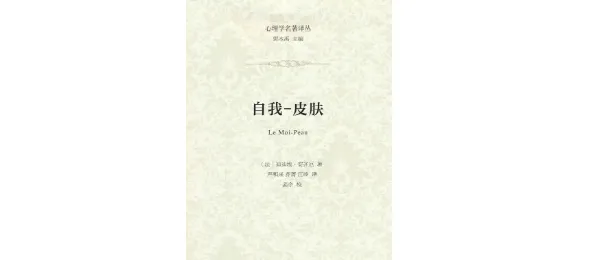
【自我-皮膚】,作者: [法]迪迪埃·安齊厄,譯者:嚴和來/喬菁/江嶺,版本:商務印書館,2023年10月。
迪迪埃·安齊厄在這一階段看到了新生兒這裏存在著身體性前自我,集合了各種感覺和資訊的沖動,具有遇見其他客體,對他們實施策略,並且與周圍母性環境建立客體關系的特性。這一點其實證實了,人一旦出生,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具有獨立的風格,且很可能有獨一的自體感受。
實驗心理學往往強調母親與嬰兒之間的「對稱性」,只有這種對稱才能讓母-子之間的關系趨向於一個穩定的系統。安齊厄則認為,只有平面(或軸線)才能得到對稱。安齊厄的理論建立於他認為觸覺和聽覺、聲覺一樣,是我們最早的覺知。隨著胎動、分娩時的擠壓和摩擦;隨著看護的觸摸與離開,嬰兒分別出「我」與「他」。觸覺是雙向同時發生的知覺,它使嬰兒意識到那包裹著自我的「精神外殼」,在初始階段,這外殼的一端是母親,一端是孩子,它為分離做好了準備。
「分界面」的提出,使我們得以看到,母親與嬰兒的關系不止是「刺激-反應」的模式,母親與嬰兒在這段關系裏都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母親的角色的重要性在被平面化成無微不至的看護者與愛的源泉之前,更深刻的是她與嬰孩的雙向關系。他們重新彼此確立自我,從而一定會從嬰兒需求必不可少的代言人的位置上退位。外殼中包裹著自我的想象,發掘自我,我們要關註幻想及與之相關的無意識沖突,而不僅僅是母親付出了多少。
誰在制造影子母親
麥克唐納提出「影子母親」的概念的同時,進行了對階級、種族問題的展演。雖然核心問題是母親被視作社會再生產的唯一負責人,麥克唐納對美國社會的研究使其無法放下對某一特定階層的關註。瞄準中產階層家庭的職業女性,就會看到資本主義市場的社會再分工是如何讓母親登入到「剝削者」的位置上的。
父權職場對個人提出一種預期:員工不必成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父權制下的階層社會又對家庭提出一種要求:兒童要盡可能地繼承文化與階級資產;中產階級職場媽媽的焦慮由此出現:如何透過中介實作階層慣習與文化資源的代際傳遞?保姆、換工、看護很難被視作共享母職的夥伴,或嬰兒周圍母性環境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她們必須是「影子母親」,執行母親幻想中的育兒方式,在親生母親回家時自動消失,代替母親為嬰兒犧牲,密集母職理想要如同幽靈般附體在代理的身上,才能讓媽媽們安心。

【母親】劇照。
如果僅看見代理母職的商品化,與保姆們被物化,是遠遠不夠的。麥克唐納執著於從文化資源、經濟階級、種族待遇的差異中找尋「不公」,盡管承認女性勞動是一種無酬勞的、發生在私人領域的勞動,卻無視了這種勞動性質的普遍性,仿佛全社會只有保姆這一特定人群擁有這種處境(或因為她們缺乏保障,在美國社會和經濟價值結構中處於最低位,而將其視作濃縮了剝削壓迫的階層)。與此同時,她不乏趣味性地提出對育兒領域的一種見地,保姆們往往主張孩童的自然成長,而職業母親們會傾向於參考指南資料「照本宣科」,這種二元對立顯然不利於母親們對專職兒童看護所執行的母愛代理的想象。
麥克唐納很快遭遇了其中的矛盾之處,保姆們的代理角色除了分擔了育兒中的雜活,也是一種情感勞動,比之工人的合理待遇,她們渴望情感上的認可,這種認可往往指向建立依戀——女性工作中最重要的報酬。她們會與孩子們的親生母親開展「能力競賽」,比誰能為孩子犧牲更多,這又導致了她們寧願犧牲自己的保障和待遇。麥克唐納雖然創造性地提出競爭性母職的概念,卻認為這種競爭源自母職的占有性與母性的脆弱,認為保姆與母親同樣是密集型母職意識形態的信仰者,從而導致了誰對孩子來說是唯一的?誰是真媽媽?誰在做最有利於孩子的事?誰在享受高品質陪伴的時光?

【坡道上的家】劇照。
這一系列的爭搶既看見了「意識形態」的作用機制,依舊著眼於「微觀政治」,容易陷入「車軲轆話」的陷阱。母性的戰場無法被轉譯成管理學的實踐。比如將母親對兒童護工、兒童成長的控制欲用服務行業的「三角」來理解,雇主-服務-顧客,由於服務總是發生在雇主/經理無法監管的地方,所以會采取崗位培訓的形式,讓服務盡可能「指令碼化」,透過日誌、匯報、突擊檢查來實施母愛監控。哪怕育兒學科用各種專家指南給予了監護人自信,育兒也依然不可能是一件指令碼化的作業。原因正如上一部份所述,嬰兒只要一出生就成為了獨立的個體,擁有獨一的自體感受,與母性環境生產獨一無二的紐結。
面對社會分工的結果,要想打破僵局,就得讓看護-母親從二元對立的位置上下來,回歸到她們共同的女性特質中。麥克唐納提到了一種女性「反意識形態」,兒童遊樂場,全職媽媽們在孩子們的社交空間交流、對照,獲得社會世界的經驗,發現「密集型母職」中對母愛不合常理的想象,比如少做了指南中要求的某件事對孩子也沒什麽影響,更認識到了自己與孩子的關系的獨一無二。職場媽媽似乎缺少了這一機遇,她們對制造一個「影子母親」的迫切和焦慮正是由於這樣一種實在經驗的缺乏。
女性普遍的辯證經驗正是如此,我們所反抗的像失序一般的東西,我們自身也一直參與其中。
解得開的結
在對母親-保姆的競爭關系的探討裏,孩子成長的控制權與歸屬權仿佛成了問題的中心,這就導致一個問題不斷被忽視,孩子究竟是否屬於母親?或者說,這個問題的提問者究竟是誰?
母親真的會覺得一個孩子屬於自己嗎?波伏瓦批評佛洛伊德的「陰莖嫉羨」時提到,如果真的存在這樣一種嫉妒,女人嫉恨的也不是男性逐獵的工具,而是他們的獵物。陰莖嫉羨是錯誤的,女性渴求的不是「有」的時刻,而是「是」的時刻。在實際經驗裏,孕育胎兒的過程往往喜憂參半,一方面孕婦落入了自然和物種的圈套,化作膠質的儲備、孵化器、卵子……另一方面,在某個階段,她是「生命」,是自為的存在,是具有固定價值的使人平胡的幻想。女性並不是母親。嬰兒是獨立的個體,母親也是獨立的女人,這組關系的復雜性在於主客體從母親的身體內部就開始膠著。

【母親】劇照。
正如實驗心理學不理解母親與孩子之間的界面,父權建制中的母親角色也用一種軸線或平面取代了母-子關系的復雜性。例如在「反墮胎」時聲稱胎兒不屬於母親,它是一個自主的存在,在贊美母性時卻說,胎兒屬於母體,不是消耗母體的寄生物。女性與胎兒之間的聯結永恒地使男人恐懼,只有將其建構為一種內容脆弱的東西。
麥克唐納眼中「解不開的結」正是此物。女人想象母親對孩子來說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這種想象的內在性不是理所當然的,是被內化的。透過神聖化母職,女人們在「輪到」自己做母親時,便占據了曾經的母親的位置,但在完全實作這一女性命運的時刻,她依然是物種命運的附屬品。女人並非在創作欲與自身的獨特性中誕育了孩子,她是在身體的一般性中完成的孕育和分娩,新生兒不是母親創作的作品。主客體正是在分離中綻出了獨一性,而並非在依戀之中。
麥克唐納的研究的最後一部份試圖以經濟管理學解開母親與代理母親之間的結:透過信任、自主權、雙向溝通、共同決策來建立母職中的夥伴關系。在她的研究案例中,那些尊重保姆的專業技能、「共享」出母職,欣然接受自己不會是孩子生命中唯一提供母愛的角色的母親們,建立起了健康、安全的依戀關系。這一答案似乎重新回歸了理想化,試圖彌合「為愛勞動」與「為錢勞動」之間的沖突。但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其中的突破之處,對母職的探討要突破意識形態的霸權。資本主義社會透過勞動分工使職場媽媽走到了剝削者的位置,以密集母職意識形態來客製需求,不論這份需求是否真的對孩童有益。不論是母親還是孩子,都無法從這個抑制結構中獲益。而真正試圖獲益的,才是「影子母親」的制造者。
作者/峖沛沛
編輯/走走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