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丁道勇長期關註教育哲學領域。在他看來,孩子們的語言未必指向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的確喚回了一種原初的「好奇」,它們展示出不受制於邊界的答案所蘊藏的直觀的沖擊力。
與其從「哲思」的角度透視兒童眼中的世界,丁道勇認為不妨借此去思考一個更具現實意義的教育問題,即「給答案」式的教育是否無意間弄丟了人之為人最珍貴的好奇心?我們試圖透過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吸引今天的成人將目光更多投向身邊的孩子,多聽聽孩子內心的真實聲音。與此同時,脫離「童年期」的成人或許也可借此回望,在同「內在小孩」的對話中找尋失落的生命力。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月19日專題【平視兒童世界——與孩子對話】的B02-B03。

丁道勇,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哲學。譯有【學習的哲學】【課堂生活】【課堂參與:沈默與喧嘩】等。
兒童像鏡子,照出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新京報:兒童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種哲學思維。在【聽孩子的話】中,作者記錄了她與孩子叮當一歲到九歲的對話,呈現了一個不同於成人視角的世界。比如兩歲的叮當曾將一切美好的東西命名為「甜」,於是會說:「我不甜,媽媽抱我一下,我就甜了。」你長期關註教育哲學方向,孩子們為什麽能做出類似有些「哲學意味」的表達?他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成年人有哪些不同?
丁道勇: 第一次當爸媽難免興奮,熱衷於記錄孩子們的童言童語,就是興奮期的一個癥狀。可惜的是,這個癥狀是自愈的,維持不了多久。在這方面,我想到了兩件小事。某年冬天,我女兒剛學會走路,一開始還得扶桌沿。北京的冬,是異常幹燥的。但是,我女兒的邊上就有一台加濕器,冒白霧的那種廉價貨。她伸手抓白霧,抓又抓不住。再一、再二嘗試過後,就不再去抓了。我親眼見證了這一幕。心裏高興壞了!看來這娃娃腦瓜子不笨嘛。女兒以非語言的方式,得到了一個具身的認知。她沒有再三去抓,就是這樁新知識在發揮作用的表現。

【聽孩子的話】,作者:蟲蟲 著 叮當 繪,版本:敏督利童書館|貴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另一件小事,記錄的是女兒三歲多時的一句神來之語:「屁屁是臭臭在尖叫」。這樣的發言,我會如獲至寶般地記錄下來。像我這樣的家長,不在少數。不過,這樣的東西真的適合叫做兒童哲學嗎?我覺得十分可疑。哲學的首要特點是清晰,而孩子們恰恰處在對於世界的迷茫和混沌之中。
包括哲學提問在內,真正有價值的問題往往是開端性問題。答案造就邊界,並且有了答案的事情,人們就不再疑問了。成人擅長答案,因此成人其實並不擅長提問。孩子們不擅長答案,所以孩子們還可以不受制於答案劃定的邊界。孩子們善於說出一些令人「吃驚」的話,孩子們會問一些看似有「哲學意味」的問題,原因恐怕就在於這種「無知」的狀態。這種狀態並不賴。社會化的成人有很多「常識」,就是你這樣想、很多個你也同樣這樣想的那些認識。因此,與兒童相比,成人反而更不善於提出開端性問題。成人生活在確定性的世界裏,反倒是小孩子還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對這樣那樣的不明白。哲學精神鼓勵不設限的追問,重視提問甚於回答,因此是「思無邪」「思無疆」。或許真是因為這一點,人們才會把小兒癡語誤認為哲學表達。
在我看來,與其把孩子氣的表達強拉硬拽到「兒哲」的高度,不如去思考一個更有實際意義的教育原理問題。如果所有問題有一個答案,並且只有父母、老師有資格提供答案,那麽這種給答案式的教育,是不是足夠好呢?孩子們如果一早就放棄了問問題,瞪大兩只眼睛四處找答案,那麽他們實際上放棄了一個自己最了不起的本領。先把好奇心弄丟了,後面是怎麽教也教不出來的。柏拉圖、王陽明都說過類似的話,人之所以能看到世界,是因為有「視力」的器官。要是沒有這個器官,誰也沒有能力教出「視力」來。我們辦教育,要基於孩子們已有的本領,不能憑空捏造。保護孩子們發問的本領,利用孩子們發問的本領,發展孩子們發問的本領,這是一項淺顯易懂的教育原理。等孩子們長大了、念了985大學的研究生,還跑來問導師:「老師,我該問什麽問題?」如果每個小孩子都這樣,那可怎麽得了。
新京報:近年來,的確有不少研究會傾向於將兒童的這些表述擡高至「兒童哲學」的維度。對此,你有怎樣的看法?
丁道勇: 你的問題,讓我想到一部動畫片,【小豬佩吉】。不知道你有沒有註意,小豬佩吉的鼻子永遠是側著臉的,故事裏的汽車永遠都會畫出四個輪子。這些畫面是用腦子在畫,而不是用眼睛在畫。畫面內容是根據幼兒的理解,而不是根據成人的透視。我收集過女兒的畫,她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畫人物側臉。當她開始畫第一張側臉人物畫時,我知道她的思維躍升了一大截。可以設想,一個畫家要是能理解兒童視角下的世界,他(她)就很有可能畫出完全不同的畫作來,就好像可以同時看到四個輪子的小汽車一樣。

【小豬佩吉】海報。
回到你說的「擡高」問題。在我們說這種「擡高」時,首先要明確是成人在「擡高」。對於孩子們來說,他們就是那樣想、那樣看的,無所謂高不高。其次,這種「擡高」是有價值的。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認為兒童和成人之間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差異。現在,人們更傾向於認為,兒童與成人有「質」的不同。當我們走到人生的某個階段時,我們樂意重新回到人類的「童年期」,想要「復歸於嬰兒」。那是因為,兒童像鏡子一樣,可以照出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透過兒童,成人反而獲得了某種「蛻殼」的可能。
最後,就我自己而言,我雖然不理解「兒童哲學」這個表達,但是我樂於看到這一類呼聲的出現。這類呼聲也授權以提供某種契機,誘惑家長和老師多看看身邊的小孩子、多聽聽身邊的小孩子。當這樣的「看」和「聽」多起來以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就很可以期待了。
新京報:那麽回到兒童的童言童語,如果說「兒童哲學」的判斷並不足夠恰當,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兒童這些表述中的「哲思」意味?
丁道勇: 這些帶點「哲思」意味的表達,我不知道是不是提出「兒哲」的事實根據。我更願意相信,這種「哲思」是兒童在特定階段的一種偏愛。在這個階段的前後,都不好叫「兒哲」。在教育哲學領域,有一位我很喜歡的專家,未來我會把他的書譯出來。他說兒童理解世界可以有不同的階段,其中就包含哲學階段。在哲學階段之前是浪漫階段,在哲學階段之後會進入反諷階段。
他說的哲學階段,是兒童開始用通觀的視角看問題,期待對世界建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識。我女兒有次在書中讀到了「atomsmasher」這個詞。她不知道這是什麽,就跑來問我。我也不知道,又犯懶不願意查,就望文生義,猜測這是什麽原子反應爐一類的東西。我們後來的談話內容,從原子的構造,到原子彈的原理,從宇宙大霹靂裏的「奇異點」,到【莊子】對【老子】的解釋,像是「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這樣的句子。把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連貫起來,當然是胡亂聯系,錯漏百出的。但是,對於熱衷於通觀思考的女兒來說,這就是有吸重力的。她現在11歲,很快12歲。可以想象,等她更年長一些,就不再會欣賞這種過度概括的認識方式了。那時的她,很可能會熱衷於挑刺,找每一個理論體系的毛病。那時候,她的認識就進入了反諷階段。

【歲月神偷】劇照。
返回頭,在她更年幼的時期,她也曾喜愛「美女與野獸」,喜愛把一切東西都人格化。她那時的思維,就處在浪漫階段。我不知道是不是說明白了這個理論?總之,如果參考這個理論,「兒哲」就只是孩子們在某個段落的偏愛。幼稚園孩子、小學低段孩子,很可能還不偏愛這樣的思考方式,所以他們也是不適合參與「兒哲」的。
「我最討厭別人誇我孩子聽話」
新京報:實際生活中,不少父母可能會忽略與兒童的交談。尤其是處於童年階段的孩子,成年人往往不會將其視為平等參與對話的主體,認為可以等到孩子們再長大一些再去定期溝通。從兒童的角度來說,這種交談是必要的嗎?
丁道勇: 對所有年齡段的孩子來說,交談都是重要的。小朋友看著是你的孩子,可實際上他們哪裏是「你的」。作為「孩子」待在父母身邊的階段,其實是很短暫的。親子關系和戀愛關系一般無二,越付出、越珍愛,沒有辛苦付出,在情感上就不圓滿。樂意在交談上花時間,願意改變自己一貫應付小孩的做法,這也是一種付出。
從兒童的角度來說,他們只是在生命歷程的某個階段才喜歡和父母「嘰嘰喳喳」。這個階段多麽珍貴啊!註意聽、不要輕易打斷、更不要手把手支招。要知道,家庭教育上遇到的問題,往往是癥狀,不是原因。今天遇到的問題,原因往往得到昨天去找。等到孩子不想理你的時候,病勢已成、病竈已顯,事情就難以補救了。孩子還在眼前,孩子還黏著我們的這段時光,好好珍惜吧。
最後,回到「關系」這個概念上來。關系長久不長久,最終都要看連線的多寡。只有一條連線,就只有一點微弱的穩定性。有多條連線,就可以有層層牽絆。如今,不少父母只扮演「移動提款機」的角色,親子間除了經濟生活,就根本沒有文化生活。這裏的文化生活,不是多麽高深的東西,跟父母的學歷無關,而是每個父母都可以給出來、都應當給出來的東西。
我一直相信,孩子成長的主要根基在家庭。老師也好、社會也罷,他們也許很專業、也許有豐富的資源,但是他們關心的往往不是眼前這個具體的孩子。只有父母才真正關心「這一個」孩子。家庭裏的「文化生活」,就是讓家庭在關乎「這一個」孩子的重大問題上,可以為「這一個」孩子掌舵。這樣的「重大問題」有很多,比如什麽人值得別人信賴、什麽人不值得別人信賴。家庭裏的「文化生活」,就是給孩子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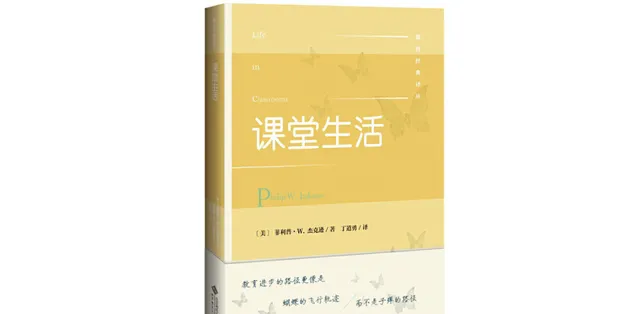
【課堂生活】,作者: [美]菲利普·W.傑克森,譯者: 丁道勇,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 2021年3月。
新京報:隨著兒童進入校園,親子間的日常交談大多都圍繞事務性內容展開,比如家庭作業、學習成績、校園生活等,孩子們的語言也會迅速被成人世界規訓。幼兒時期的那些「哲思」似乎慢慢消散了。這樣的交談可能很難真正關註到兒童內心的起伏。在你看來,我們應該如何提升與兒童交談的品質?
丁道勇: 時間是個大問題。可是,肉身的相處,並不是最關鍵的。即使沒辦法與孩子在一起,親子間也還是可以交談的。孩子知道父母在做什麽、知道父母會怎麽完成自己的工作,這本身就是一種有價值的交談。有些父母說的話很多,可是他們的孩子不願意聽。這部份父母有時間跟孩子說話,可是他們說的話孩子不愛聽。我們要努力讓自己說的話,有讓孩子們聽一聽的價值。這個「聽一聽的價值」,不會因為我們是父母、我們是為了他們好,就自動有了。
至於具體的言說技巧,我覺得父母能做的最直接的事就是「多聽少說」。說一個我讀來的故事。有個富人請教自己朋友,說自己總是和太太發生沖突,倆人常常說不到幾句就「談崩了」。朋友給他支了一招:「你重復她說的話。」富人回到家,剛進門就聽太太說:「你知道我今天去哪裏了嗎?」富人應聲:「你今天去哪裏啦?」太太笑說今天去了趙董娘家,富人回應:「哦!你去了趙董娘家啦?」太太繼續說:「你知道趙董媽媽穿了多高的高跟鞋嗎?」富人回說:「她穿多高的高跟鞋呀?」太太打手勢比劃說:「有這麽高」……在這個故事裏,富人差不多什麽也沒有說。管住自己的嘴,不著急支招、不著急評論,只是告訴對方,我在聽、我耐煩聽、甚至我愛聽,親子間的談話恐怕就不會那麽困難。
再說一點。父母容易把任何談話都當成一種「教育」。好累啊!孩子愛和你說話,你才有機會幫到他。要是有個人時時處處、處心積慮要來教育我,我才不稀罕跟他說話。有天晚上,女兒跑來跟我說:「爸爸,我今天怎麽總放屁。」我心想,糟糕,孩子估計是著涼了。不過,我嘴上沒這麽說。這件小事不值得說,加件衣服就得了。我嚴肅面孔,跟她說:「你千萬小心,別靠近火源。」女兒聽了這個話,知道我在打趣,也很高興地接話,開始形容人形火箭之類的場景。放松下來,說話誰不會?討教親子溝通技巧,多半還是指望讓孩子更聽自己話。可是,教孩子本身就不是單靠說話來完成的。更何況,我們當父母的有那麽偉大、正確,值得孩子一直聽話嗎?一直聽話,真是我們想要的孩子嗎?我最討厭別人誇我孩子聽話。

【學習的哲學】,作者: [英]凱瑞斯托弗·溫奇,譯者: 丁道勇,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 2021年10月。
父母也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的工作,講自己工作中的苦惱,講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講這個社會,講這個世界,講一講陽光燦爛,也講一講那些讓人氣悶甚至憤恨的壞東西。為什麽不呢?總是單向度地試圖挖掘孩子的內心,永遠一張教育臉,永遠不把自己的「後背」給孩子看,沒必要的。
總而言之,我認知的父母之道,恐怕只不過是一顆平常心。把用在職場上的待人正道,用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這樣的父母差不多就是合格的了。在職場上,我們會輕易幹預別人的意思嗎?會輕易失信於人嗎?會輕易允諾嗎?如果父母也能對孩子保持同樣的操守,那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帶著「玩心」去生活
新京報: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常常還會借助故事、繪本與他們交談,並試圖借此培養孩子們的各項能力,建立他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但不少家長困惑,為什麽現在童書的序列越來越完善,但我們的孩子反倒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
丁道勇: 這裏可能要拆分成兩個子問題來談。首先,童書序列真的日益完善了嗎?對這個判斷,我很懷疑。ChatGPT出來了,人們開始討論中文語料的枯竭問題。我也是憂慮派的一員。文風的刻板,會遮蔽人的感知。比如,我們說一個人沒意思,會說這個人言語無味。語言的刻板,損失的不止是語言本身。因此,中文語料的枯竭,是個值得重視的大問題。把【圍城】推薦給中小學生,和把【水滸傳】推薦給中小學生一樣,都是貌似合理而實則怪誕的因循之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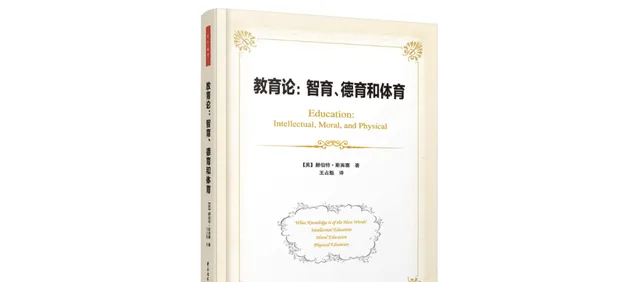
【教育論】,作者: [英]赫伯特·斯賓塞,譯者: 王占魁,出版社: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出版時間: 2016年12月。
至於孩子們的心理問題,我一直認為,孩子們的多數心理問題本質上是教育出了問題。斯賓塞的【教育論】裏區分了五種值得教給人的知識——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識(比如什麽能吃、什麽不能吃);間接保全自己的知識(比如讀師範、當老師);如何做公民的知識,如何度過閑暇時光的知識,以及如何做父母的知識。第四類、第五類知識,目前我們的教育供給是空缺的。親子間「雞飛狗跳」,這主要出現在學齡期兒童的家庭。此後的大部份家庭,不都進入到「父慈子孝」的新階段了嗎?所以,解決心理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先解決教育問題。基本的教育知識,並沒有我們想象中那樣普及。教育知識普及的工作,應當像科學普及一樣,花大力氣去抓一抓。
說回到「心理問題」,我是外行,我說的都是些外行意見。作為一個外行人,我認為很多心理病都可以歸於「獨孤病」。不管自己變成什麽樣子,這世上始終有一個人、永遠有一個地方會接納自己。如果一個人始終能確信這一點,那麽他恐怕就不會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家庭能不能成為這樣一個保底的地方?父母能不能成為這樣一個保底的人?不是好孩子,父母就不愛我了。這樣的孩子其實挺可憐的。
新京報:前段時間,「高鐵上的熊孩子」曾引起過討論。在公共場所吵鬧的兒童常被視為「難以交談」的物件,父母乃至周圍的成年人可能也很難找到恰當的與孩子溝通的方式。你怎麽看這種現象?當孩子們表現出成人看來的「情緒失控」時,這時的「交談」又該如何繼續?
丁道勇: 這背後有一個換位思考的問題。設身處地想一想,為打發一段封閉的高鐵時光,父母尚且要提前做些準備,更何況是那麽小、更不耐煩無聊的孩子們。出行前,父母也授權以幫孩子提前做些規劃,還可以讓孩子也參與到這個規劃中來,計劃一下自己在旅程中要做點什麽。另外,在孩子「情緒激動」時,最好先暫緩溝通,以安撫情緒為主。可以抱抱孩子,在停車間隙去月台走走。講道理的事情,放在事後去做。不要在帶情緒的人面前講道理,這是一條溝通鐵律。
新京報:再進一步,如何與兒童交談其實不只是屬於兒童和父母的課題。從個體的生命歷程來看,如何與兒童交談背後引出的是一個終生議題,即在一個人成年後,他(她)該如何與自己的「內在小孩」交談,如何在尊重自我感受的同時與外界建立能夠持續提供生命能量的互動。這在今天的社會尤其值得思考。你會怎麽看這個問題?
丁道勇:每個人都是基於各自的人生經歷來回應問題。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好玩兒」很重要。所謂「好玩兒」,就是「不這樣,又怎樣」。在生活中,偶爾來上這麽一句反問,很好。植物一旦停止生長,它就死掉了。可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不正是今時一如往昔嗎?我不覺得生命力是人內部的某種神秘東西。生命力是肉眼可見的。人只要還在生長,那麽生長過程就是這個人還有「生命力」的證據。

【一一】劇照。
我說的「玩」,不見得是玩遊戲,而是指帶著「玩心」去生活。能夠跳出來看目前的境遇,將視域放寬,問問自己「五年後、十年後還覺得這件事重要嗎」?有「玩心」的人,還沒有被自己身上這個「我」完全掌控。這樣的人「生命力」更旺盛,更不容易去打壓那些「生命力」旺盛的小孩子們。
采寫/申璐
編輯/王銘博 宮子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