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夜大雪,天地一白。雪窗閑讀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述及吳湖帆與名妓寶珠老九一段軼事。寶珠老九,即施畹秋。
如陳巨來所說,民國丙寅年即一九二六年五月,他經吳湖帆介紹,先後認識王栩緣、馮超然、穆湘玥等人。這些文人雅士相聚一處,經常飲宴達旦,且頻頻「叫局」招妓侍酒。而吳所經常招徠之妓,名喚「寶珠老九」。據吳湖帆親口告訴陳巨來,「寶珠,施姓,名畹秋」,原是吳湖帆居處「東鄰某氏之妾也」。吳氏「每於弄中見之,覺得美而艷,故常目逆而送之」。後來一日,吳氏於一枝春酒樓赴宴,再次邂逅這位女子,才知道她已重返花國,「下堂重墮風塵矣」,所以自此之後,吳每次叫局「必招之」。
未料後來,吳湖帆竟不滿足於「叫局」相膩,使出一招「瞞天過海」之計,在正夫人潘淑靜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偷納寶珠為妾,在滬上吳江路別賃「金屋」,與之同居三年。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二人偷情久之,終為潘氏所知,「大事詬誶」,又值吳湖帆黃金生意投機失敗,一時財乏,無力蓄妾「藏嬌」,遂托人給寶珠老九者遺金二千,欲與寶珠分道揚鑣、溜之大吉。不想郎情已斷、妾意未息,吳湖帆避走蘇州,寶珠卻癡情不悔,屢屢寫信求和,更有「生是吳家人,死為吳家鬼」之癡語。然而癡情並未換來郎回頭,寶珠傷情不已,某日哭訴於樓上鄰居、滬上大律師江一平之父江子誠處,引得江老爺子同情無限,感其「情意至正」,多次向吳湖帆請求「覆水重收」,不意吳湖帆應對無法,頗駁江老情面,氣得老人竟要其子代施訴之公堂。吳湖帆一時之間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病急投醫,寫信倩馮超然向陳巨來求助。後來在潘靜淑過問、陳巨來斡旋之下,事情終算擺平,負情郎吳湖帆順利逃身,深情妾寶珠則在數月之後再上青樓,重操舊業(詳見【安持人物瑣憶•吳湖帆軼事】)。
睹此一段「風流公案」,不禁有「二驚」:一「驚」吳氏畫藝精湛,一度稱雄海上畫壇,被奉為藝林盟主,不意竟也曾混跡北裏,浮浪營生,眠花宿柳,這與我平日所知之吳大師判若兩人。可見歡場之上,亂花迷人,就連吳湖帆這樣的人物也在所難免。二「驚」寶珠者何人,竟能贏得吳湖帆青睞有加。吳湖帆本世家子弟,交際既繁,見多識廣,為人向來乖傲,視人眼光尤高,藝林能得其青眼相看者匪多。其結發之妻潘淑靜為吳下「貴潘」後裔,家世顯赫,能詩善畫,與吳伉儷情深,二人所居梅景書屋,曾經是世人艷羨之所。潘歿後,吳氏續弦顧抱真,顧為潘之使女,雖乏樹春才華,亦賢惠持家,頗得內外認可。而據【吳湖帆與周鍊霞】作者劉聰精心考證,解放後吳湖帆尚與海上名女畫家周鍊霞另有一段不為世人熟知的銷魂情緣,同人間眾所共知,【佞宋詞痕】即是吳、周共赴情海之盟證。鍊霞不僅姿容絕妙,且詩書畫藝集於一身,素有「女鄭虔」之稱,早於民國二三十年代即蜚聲藝壇。她為人豁達,恣謔不忤,能言善舞,風情獨具,人送「煉師娘」之號。解放後,吳、周二人因藝結緣,往來漸多,更因同經「中年哀樂」,惺惺相惜,日漸生情,頻繁唱和,傳情達意,甚而賃館別居,戀情綿延近十年,然終因時勢造化,未能有情人成眷屬。
以吳氏之脾性,就潘淑靜、顧抱真、周鍊霞三者參而觀之,寶珠亦必有其過人之處、特出之美,否則何以引得吳湖帆折腰招徠,垂青鐘情三年之久?
於是,「寶珠老九」到底是何模樣,身世遭際如何,引起筆者的極大興趣。然區區一妓,青史誰會為之留名?幸而晚近民國,小報筍出,經常刊登名妓照片,於報刊則是制造噱頭、吸引讀者,於妓女則是高張艷幟、贏取花名,用今日之時髦話說,二者都是為了博取「流量」,雖屬低階趣味之相投,但亦商業社會之所驅,也算各取所需、各得其美。
余此時正值元旦假期賦閑,無事聊賴,索性不辭辛勞,翻檢民國舊刊,追尋佳人麗影,不意竟真得「名花寶珠老九」照片數幀,有幸一睹芳容月貌;又得閑情文章數篇,得窺其行跡之一斑。雜糅成文,饗之諸君同賞共析。
關於施畹秋的身世遭際,一九二八年【福爾摩斯】報上刊出【美秋老九之身世談】一文有十分詳細的介紹。寶珠老九,原姓施,名畹秋,一九二八年【金剛鉆】「白袷」所作【寶珠闔第光臨】一文雲她為「蘇之甘露人」,也就是江蘇無錫人。
施畹秋早年間曾在滬上安寧裏寶珠書寓討生,能歌善舞,「艷名甚噪」,滬上報紙說「凡老於花叢者,類能知之」。後來,她與一徐姓男子相識相戀,熱情高漲,遂論嫁娶。徐姓男子供職於火車站,雖然娶了畹秋,卻不絕「倡門之遊」,仍然經常尋花問柳不斷,後來不幾時竟移情別戀。秋扇見損,寶珠老九一度暗彈情淚,終於忿其濫情,忍無可忍,遂與這位「城北徐公」(【羅賓漢•美秋老九不忘舊情】語)決裂分手。
仳離之後,她拿著私蓄萬金,獨賃一屋而居,有時會到舞場消遣時光,為狀蕭散。為排遣心中苦悶,她曾與女友名妓雪雪老大到杭州等地遊玩,並曾在聖地普陀山拜僧為師,受戒從佛,可見徐子遺棄對其打擊之大。
然而,禍不單行。獨自幽居期間,施畹秋又被一柯姓男子所誘,致使蓄金散盡,恚恨之余,曾幾度自殺。受此大創,施畹秋日漸瘦損,一度頹病。至一九二七年仲春,新病才初療,但她已是「瘦骨支離」。為了緩釋身心,在友人建議下偶爾到舞場活動。
後來「生涯推板」(【嚕哩嚕蘇•美秋老九燒路頭】語,推板即上海方言「推班」,差的意思),迫於生活,她在其他妓女姐妹的勸解之下,於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間,不得不又在群玉坊樹幟招客,重操故業,棲身美秋書寓,易名「美秋老九」。
由於早有艷名,所以在她還未重新「出山」之時,滬上各報紙早已得到風聲,著名小報【晶報】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農歷丁卯八月十四日)第三版夾縫之中,刊出一「豆腐塊」文字,雲「寶珠老九,將於中秋節後復出,不延舊名」。果然,僅僅一旬之後,【晶報】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農歷丁卯八月十四日)第三版刊出新聞:「寶珠老九出山,在群玉一弄,易名美秋老九」。而她重墮風塵不久,便有了與吳湖帆的一段露水情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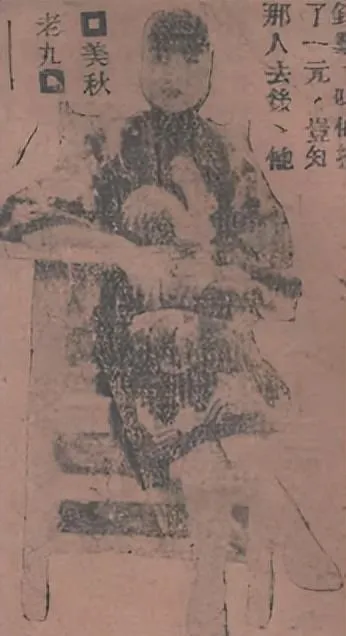
滬報說她「艷名甚噪」,恐怕首先是因她的容貌出眾。余力所能及查到關於「寶珠老九」的最早一張照片,為一九二六年【上海三日畫報】第一五五期第一頁上之「名花寶珠老九」,後署「小抖贈」,片中的「寶珠老九」雙股輕疊,坐態優雅,雖為黑白畫影,猶見明眸灼灼,風姿綽約。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農歷丁卯九月初六),【小日報】亦刊出「寶珠老九」廣告,配照片一幀,此照片較之前者,清晰不少,發髻整飭,目光柔和,形容端可稱「秀麗」二字了。其余則散見於一九二八年之【明鏡】【上海繁花】【駱駝畫報】【羅賓漢】,一九二九年之【大常識】等報刊。而【寶珠闔第光臨】則刊有「故名畫師」瘦腰生「嘗為速寫一幀」,也就是所謂「寶珠老九造像」一副,圖中人短發齊耳,面圓似月,黛眉清秀,雙眸剪水,極有豐神妍態。

通觀這些舊年照片圖畫,雖多顢頇不清,然稍作細辨,仍可見其明眸閃閃,似含秋水,頗為動人,「紅柳」說她「有雙人眸,黑如點漆,玲瓏善睞」(一九二八年【明鏡】八月十三日【寶珠雙珍記】語),誠的評也。除雙目目炯炯有神,她的面相溫婉淡靜,自有一種嫻雅沈靜之華,絕無艷國脂粉之氣,細品則如紅蓮出水、清新脫俗,如果不說是風塵女子,倒有幾分碧玉身段。
其實,施畹秋的容貌在當時是公認的秀美。一九二七年小報 【嚕哩嚕蘇】載「紅金龍」【美秋老九燒路頭】一文,說她的容貌「也很美麗」,「行頭亦很挺刮」。一九二八年,上海灘頗為著名的舞廳桃花宮開幕第一日,已易名美秋老九的施畹秋,與同是妓女的「韻秋老六」同來。【美秋老九之身世談】的作者「花偵」同場參加活動,彼時尚不識施畹秋,一面之緣,驚嘆其「豐神獨絕」。不幾日,「花偵」又在爵祿舞場再次遇到了施畹秋,「方與我友鳳律師,環抱作舞」,隨後詢之於友人,才知道是「群玉坊美秋老九也」,也就是施畹秋。說道施畹秋的容貌,他寫到:「九(即美秋老九)玉貌清麗,娟媚入骨,舞時姿態曼妙,美莫可言。」談及其被徐男離棄、柯男誘騙事後,又說「九之容貌,本甚豐美」。可見施畹秋容貌確實是有超人之處。而文章所配施畹秋玉照一副,眼波顧盼,頗有楚楚可憐之態,直讓觀者生「我見猶憐」之感。

作為女子,施畹秋如果僅僅是容貌姣好,恐怕也未必能讓吳湖帆傾囊納其為妾。陳巨來評其「態度殊娟雅而秀麗」,江子誠稱之「幽嫻貞靜」,那麽到底她的性情如何,我們不妨來看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農歷丙寅十二月十九日)【羅賓漢】報上刊出的一篇文章來佐證。
這篇姓名標示「鷹眼」的文章名為【寶珠老九挨針】,文字雖然是小報慣用的「米湯大法」,頗為猥瑣下流、引人綺想,但卻留存了一段對寶珠老九的評價:「明眸善睞,巧笑多姿,尤妙在溫文爾雅,相對可以忘憂,絕對沒有咄咄逼人、不可向邇的飛揚意氣。」「明眸善睞,巧笑多姿」,再次印證時人對於這朵北裏名花的一致看法。而「溫文爾雅」四字,向來是誇贊閨秀碧玉的「專詞」,卻用在一位寄身風塵的妓女身上,可見施畹秋絕無一般流螢艷女的輕浮之表。「絕對沒有咄咄逼人、不可向邇的飛揚意氣」,則凸顯施畹秋性格之溫婉柔和,平易近人,絕非久居下層那種性格張揚、舉止粗俗之輩。

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農歷丁卯八月十四日)【晶報】第三版刊出「寶珠老九出山」訊息時,則說她「芳姿如舊,惟略清瘦,頷下稍削耳。」「芳姿如舊」,可證施畹秋之美貌是公認的美好。「惟略清瘦」卻不免使人有「人比黃花瘦」的聯想,畢竟她甫經徐姓男子的絕情離棄,又疊加柯姓男子的誘騙失財,可謂身家蕩盡、身心俱損,難免身形消瘦,這也似乎從一側面證明其「情意至正」是一貫秉性,不惟對吳湖帆,即對前任,也是如此,絕非臨時的歡場戲碼。

上述【寶珠闔第光臨】一文,再次談及「寶珠老九」。文中說,「昔清和坊,風軒月館,林林總總,不下於今日之群玉會樂也。茲則惟寶珠一家,如魯靈光之仍屹然對峙其中焉。其室凡二上二下,而人材亦稱最盛。曰三,曰四,曰六,曰九。四工酬對而九艷麗獨負時譽,瘦腰生絕賞之,比日燕息逆旅。生友黃者宓者,或嫟三,或眷四,粥粥羣雌,每一門蒞止,善謔者稱為‘闔第光臨’,事亦趣矣。」而寶珠老九「工歌,大小嗓俱能,霸王別姬一劇,神韻雅似畹華。」畹華,即京劇大師梅蘭芳,梅蘭芳最擅之戲即【霸王別姬】,以「畹華」譬「畹秋」,可見施畹秋技藝之高。「白袷」雲施畹秋不僅能歌善舞,而且居處潔凈,庖廚有術,「其鯽魚之美,尤膾炙人口」,連老饕客也神往不已。(其實,這樣的「人間樂土」,試問誰人不向往?)同時,施畹秋久作紅倌,十分善於交際,報紙上說她「每折沖樽俎間,能使外人貼然不敢稍動,亦倡門中之巫師也。」(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福爾摩斯】語)
總而觀之,施畹秋雖許身煙花之地,不惟貌麗秀容引人,更加之性葛文順可人,其性也沈靜,其行亦低調,其居也潔凈,其烹也佳妙,又善於交際,真人間妙女子一枚。不枉昔日一代大家吳湖帆與之裏弄相見,日漸傾心,酒樓重逢,愛而親近,頻頻招徠,最終納其為妾、同居一室(不惟吳氏喜歡,恐怕但為男子,沒有不喜歡的吧)。
吳湖帆與施畹秋相戀之具體事跡,已湮沒在歷史塵煙之中。據陳巨來回憶,當時吳湖帆曾為伊人集宋人詞句,作【臨江仙】詞一闋,並題其玉照之上,此為吳氏作詞之始。因這首集句詞寫得極好,甚得大曲家吳梅贊賞。從此,湖帆肆力於填詞,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寶珠」者,可謂吳湖帆詞藝啟蒙之「繆斯女神」也!(惜乎手頭並無吳詞人之詞集,無法驗證之)

依陳所說,吳湖帆與施畹秋之決裂,則是在民國己巳年,也即一九二九年。東窗事發,馮超然曾告訴陳巨來「湖帆瞞著夫人,娶施為妾已三年矣」。以此推算,吳湖帆如納施氏為妾,當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兩年間。吳湖帆是在寶珠老九「重墮風塵」後與之邂逅酒樓,所以,二人的正式交結當然應該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之後了,而納施為妾也自然早不過一九二七年八月了,即使至一九二九年年底,滿打滿算也不過兩年三個多月,可見馮超然「納妾三年」之說的「三年」當是虛數。
二人情事雖不多見諸文字,但在杭州西湖水樂洞,卻有一段壁上題詞,見證了吳、施二人往日的情好繾綣:戊辰年閏月江南吳湖帆攜施氏畹秋遊此題名。
西子湖邊,西泠橋畔,自古就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淵藪。吳湖帆老來相好周鍊霞與夫君徐晚蘋一九二七年的新婚蜜月,便在杭州度過,而二人所居的南山煙霞洞與水樂洞相距不過數武,一年之後的戊辰年閏月,即公元一九二八年農歷閏二月,吳湖帆攜施畹秋也來到了這裏消遣閑遊。

我們可以想見,是時佳人相伴,俊侶偕遊,吳湖帆興之所至,題名留念,短短數十九字,時隔九十余年,仍可感知吳氏當年的情濃意滿和舒心愜懷。有人考證,吳氏後來所作【祝英台近•煙霞洞】中,有「玉洞猶繞煙霞,劉郎憶前度。回首凝情,當日舊題處」之句,實際上是懷念與施畹秋同遊水樂洞題名事。
然而,當日同遊水樂洞的二人,何曾想在翌年就情緣消盡,鴛鴦鏡破,勞燕分飛,甚至一度鬧到要對簿公堂,翻覆之間,令人唏噓不已。可憐多情女子施畹秋,遇人不淑,屢遭遺棄,終於只能重作馮婦。而吳湖帆事後決絕之狀,比之經年之後與周鍊霞相戀時念念不忘、至死不渝之情態,真是天壤之別,這也再次驗證:男歡女愛,兒女情長,固然難免始於肉體之吸引,皮囊之誘惑,然終須靈犀相通、興趣與共,才能建立對等長久之關系,相知相守。正是:畹秋有心難著意,湖帆無情易遠去。
(作者原創,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