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維克托·漢森

19世紀末,英軍的戰術在歐洲已經相對落伍,但其獨特而嚴格的訓練仍然最能體現希臘羅馬以來的歐洲軍事傳統。從希臘羅馬開始,大部份時間內歐洲軍隊的紀律性在全球獨樹一幟,其背後是民主共和制度塑造的平等主義和愛國主義,可見軍事確實是政治的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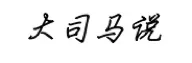
請輸入標題 bcdef
本文歡迎轉載。
祖魯戰爭專題:
1879年,日不落大英的軍隊為何敗給非洲原始人
幾千祖魯人持先進火槍,為何吃不下英軍百人小隊
祖魯人使用英軍的槍炮,為何仍不敵英軍
非洲原始人面對英軍,為什麽戰績遠勝大清
英軍:技術落伍與紀律封神
在1879年,世界上還存在著比英國殖民軍規模更大、組織更出色的歐洲軍事力量——尤其是在法國和德國。
殘酷的美國內戰(1861~1865年)和短暫而激烈的普法戰爭(1870~1871年),宣告了大規模騎兵和緩慢行進整齊戰列戰術的終結。機槍、新式連發步槍和榴彈摧毀了王公們最後的貴族自負情懷,開啟了近現代工業化戰爭的黎明。
與此相反,英軍在滑鐵盧(1815年)之後進行的殖民戰爭,除了個別例外(比如災難性的1854~1856年凱瑞米亞戰爭),對抗的敵人都沒有現代化的武器、精心打造的要塞或者復雜的戰術。
結果便是 英軍成為一支特別的反潮流的軍隊 ,他們越來越發現自己被排除在時代之外,遠離現代西方大規模征召並裝備新兵的策略。
維多利亞式軍隊反映了英國社會的等級劃分,在海軍中這一點尤為明顯。由於英國軍隊沒有受到其他更現代化的歐洲和美洲軍隊的挑戰,因此直到最後一刻都沒有拋棄過去時代的戰術,並且仍舊以血統出身而非功績作為晉升的首要標準。
只是在祖魯戰爭前十年,英國戰爭部次長愛德華·卡德韋爾才進行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革嘗試,比如取消軍官職位的購買,改善入伍條件,並力推采用現代步槍、火炮和格林機槍。
然而直到1879年,仍然 只有18萬英國士兵——遠少於羅馬帝國的25萬——鎮守一個跨越亞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的帝國 ,在這個帝國內部,混亂頻頻出現在印度、阿富汗、南非和西非。
英軍的問題,並不僅僅在於數量不足和內在的等級偏見。這支軍隊還承受著長期債務危機的折磨——這導致薪餉不濟和武器過時。
即使在禁止貴族逐級購買軍官職位後的19世紀晚期,相當多的軍官還是些思維僵化保守的老古板,他們懷疑地看待科學以及隨之而來、促成社會工業化的機械專業。
盡管指揮蹩腳和缺乏資金,傳奇式的紀律和訓練還是挽救了英軍。 大英帝國仍舊擁有一支非常有效的國家軍隊。
絕大部份英國紅衫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軍隊都更加訓練有素、積極求戰。當組成他們著名的方陣時,這些軍人能進行持續、精準而致命的步槍火力齊射,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當之無愧的最好的士兵。
在羅克渡口攻勢之前的幾分鐘裏,沒有一名英國正規軍士兵在數千祖魯人接近前加入殖民者和土著部隊的逃竄行列。相反,不到100名能夠行動的人,在16小時內倚靠圍墻連續射擊超過兩萬發步槍子彈。
在此前幾個小時的伊桑德爾瓦納血戰中,英國正規軍第24團幾乎所有正規連隊都在原地覆滅,而不是逃之夭夭。一名參與屠殺的祖魯老兵烏胡庫後來這樣回憶英軍最後的頑抗:
他們被包圍得水泄不通,背靠背站立著,把一些人環繞在中間。他們的彈藥現在打完了,除了一些近距離還能打到我們的左輪手槍。我們從短距離上投擲阿塞蓋短矛,殺死很多人後才能破壞方陣。我們終究用這個方法戰勝了他們。(F.克蘭恩索,【祖魯戰爭歷史及其源起】,413)
祖魯人到達羅克渡口前一刻,查德中尉的人射殺了一名和史蒂芬森上尉的那托土著分遣隊一起逃竄的歐洲軍士。查德覺得沒有必要在報告中提到這次射擊,英國軍官團也承諾不調查這次行為,畢竟這明顯是擊斃擅離職守的殖民地軍士的公正舉動。
後來,加尼特·沃爾斯利甚至批評了在伊桑德爾瓦納英勇拯救女王軍旗的兩個人——梅爾維爾和科格希爾少尉。
沃爾斯利的觀點是,當麾下被圍攻的士兵還活著並仍在戰鬥的時候,英國軍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離開營地。在步兵抵抗崩盤後,逃離伊桑德爾瓦納的少數騎兵部隊後來順理成章地受到了質疑。
在因通比河那場較小的災難過後,哈瓦德中尉由於在麾下士兵被祖魯人包圍時自己跑出去求援,受到了軍事審判。
盡管哈瓦德被軍事法庭宣布無罪,沃爾斯利將軍還是堅持要將他的異議在全軍各團前進行宣讀。 沃爾斯利厭惡一名英國軍官拋棄自己的士兵卻只是抱歉了事的想法,他闡明了自己對軍隊傳奇式紀律核心的信任:
一名軍官越是發現他的隊伍處境無助,就越應該忠於職守與他們共命運,不論結局是好是壞。因為英國軍官的地位為世人所尊敬,他在軍隊士兵中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士兵們會覺得,不論發生什麽事情,自己在危機中能夠絕對信任的是軍官,任何情況下軍官都絕不會拋棄士兵自己逃走。 我們軍事史裏記載的大多數英勇行為,應歸功於這種英國士兵對軍官的信任 ;由於這項軍事法庭的判決動搖了信念的根基,我覺得有必要將我對該判決的重要異議正式公布出來。(D.克雷莫爾,【祖魯戰爭】,143)
英國軍隊的主力會組成橫隊和方陣。在橫隊當中,每列有三到四排士兵——通常分別俯臥、跪地和站立——這些士兵按照命令輪流開火、裝填,五到十秒鐘後再次開火。即使是使用單發的馬蒂尼-亨利步槍,整個連隊準確的射擊次序依然能夠確保近乎穩定的彈幕覆蓋。
而如同盒子般四角為直角的方陣,則能夠保證輜重處在安全的中心位置,庇護傷員和預備隊——方陣的完整性保證沒有英國士兵會在陣形邊沿的任何一點逃跑。
為了確保對火力的控制,英軍時常會在戰場上每隔100碼的距離上打下木樁,讓槍炮軍士修正開火順序,讓步槍手校準目標。

令全球聞風喪膽的英國龍蝦:紅衫軍
英國槍騎兵對祖魯人的屠戮,同樣因其訓練有素的周密步驟而顯得可怕:
劍橋公爵屬第17槍騎兵團是個充滿驕傲的部隊。「犧牲或光榮」是他們的座右銘,巴拉克拉瓦戰役中的英雄表現是他們曾獲得的榮耀。德魯裏-勞(該團團長)將他們精心排好,就像是在閱兵一樣……看著身穿藍色制服、臉龐白皙的騎手們跨在高大的英國馬上,他們看上去像是機器一般,制服規整一絲不亂。德魯裏-勞領著他的團呈縱隊前行,當地形擡升時,他下達命令:「小跑——組成中隊——組成橫隊!」然後,將士兵排成兩列縱深,「快步跑!」戰馬向前騰躍,然後當鋼鐵騎槍隨之向前時,三角旗搖曳招展,「沖鋒!」接著步兵在方陣中爆發出喝彩。這個騎兵團迅速追上撤退的祖魯人,騎槍也像阿塞蓋短矛一樣毫不留情,騎手攻擊一個又一個祖魯武士,槍起槍落,無情地刺穿著敵人的身體。(D.克雷莫爾,【祖魯戰爭】,214)
何謂西方式紀律?
遭到攻擊時,展示勇氣是任何戰士共同的美德。無論來自哪裏,任何戰士都能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英勇。
在服從指揮的同時又能展現勇氣的特征,也並非西方軍隊獨有。原始部落和文明化軍隊都從恐懼乃至戰士們對首領、將軍、國王或獨裁者的敬畏中獲得勝利。
在羅克渡口英國基地的北部圍墻上,緊抓紅色的馬蒂尼-亨利步槍槍管的祖魯人,和幾秒鐘後用點45口徑步槍彈沈著地將他們撕成碎片的英國人一樣勇敢。祖魯武士幾乎和英軍士兵一樣服從自己將軍的指揮,他們無所畏懼地用人浪沖擊著駐防陣地。
然而到最後,是祖魯人——只要國王點個頭,他們就會被處決——而不是英國人,逃離了羅克渡口:
這看起來很矛盾,為何進攻中如此英勇的人,會在行動最終失敗後驚慌逃竄。不過這對祖魯人而言似乎也並不矛盾。對他們來說,如果其進攻最終失敗,他們就會認為,逃走是理所應當的事了……一旦一個人開始逃離戰場,影響將會蔓延全軍。就連恰卡自己的團,有時也會逃跑。這就是祖魯人戰鬥的傳統結局。他們要麽摧毀敵人,要麽就是以潰逃收場。(R.伊格爾頓,【他們像獅子一樣戰鬥】,188)
在羅克渡口戰役的幾個小時以前,大多數「伊普皮」在伊桑德爾瓦納取得他們最大的勝利後,就帶著戰利品解散回家了——相反,六個月後英軍在烏倫迪屠殺祖魯人之後,兇殘的英國槍騎兵連續若幹小時追殺踐踏敗逃的祖魯軍隊,根本不停下來休息。
為什麽勇敢又順從的祖魯人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和同樣勇敢且順從的英國士兵相比缺乏紀律呢?
從古希臘時代起,西方人就在探索,怎樣能將個人的勇敢、對領袖的服從,與更廣義上的來自紀律、訓練與平等主義的更為制度化的勇氣區分開來。
自希臘化時代的傳統開始,歐洲人便已經著手將所謂的不同勇氣型別,從個人行動的大膽輕率一直到將整條戰線凝聚起來的共有勇氣構造成一個層級體系——按照他們的說法, 前者只會偶爾成為贏得對手的原因,後者才是取得長久勝利的關鍵。
舉例來說,根據赫洛多德在普拉提亞會戰(公元前479年)後的記載,斯巴達人沒有獎勵阿裏斯托得穆斯的勇猛,後者因為在溫泉關沒能參戰而受辱,就在此戰中直接沖出己方陣列,近乎自殺式地攻擊波斯人。相反,斯巴達人給予波西多尼烏斯很高的評價,因為他勇敢地和同伴一起在方陣中戰鬥而「沒有盲目求死」(赫洛多德,【歷史】,9.71)。
赫洛多德暗示阿裏斯托得穆斯並沒有理性地戰鬥,這名瘋狂的戰士之所以如此作為,只是因為去年夏天,他因故錯過了在溫泉關光榮戰死的機會,被人認為失去榮譽而想加以挽回而已。
古希臘對於勇氣標準的建立,與訓練和紀律密不可分:重裝步兵憑借冷酷的理性而非狂熱戰鬥。
一個合格的重裝步兵理應珍愛自己的生命,並且樂於為城邦奉獻一切。他在戰鬥中取得勝利的標準,並不在於他殺了多少人,或者展示了多麽了不起的個人勇武,而在於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戰友前進,或是戰敗後如何保持秩序,以及在遭受攻擊時能否保持陣形。
對群體神聖性的強調,不僅僅是斯巴達人的精神,也是通行於整個希臘城邦世界的普遍法則。 在古希臘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頻頻發現關於士兵之間團隊凝聚力的相同主題——只要獻身保衛自己同胞和文明的事業,所有的公民都能夠成為優秀的戰士。

希臘重步兵最看重紀律而非武勇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中,雅典將軍伯瑞克利在葬禮演說上提醒公民大會,真正勇敢的人並非那些狂暴的人,這些人「只因處在邪惡的狀態下,便有了不珍惜自己性命的最佳借口」。這種人,按他的說法,「不奢望過上更好的日子」。當然,真正的勇氣則體現在「‘那些即使承受著災難,其表現得也相當與眾不同的人’身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2.43.6)
我們從希臘著作裏,了解到堅守行列、一致行動和嚴守紀律的必要性,這些因素遠比單純的力量和勇武重要得多。
普魯塔克寫道,士兵們攜帶盾牌是「為了確保整條陣線的利益」(【道德論集】,220A)。真正的實力和勇氣,是帶著一面盾牌屹立在陣列中,而不是在捉對廝殺裏殺敵無數並成為史詩和神話的良好素材。
色諾芬告訴我們, 這樣的團體凝聚力和紀律,來自自由擁有財產的業主們:「戰鬥和下地幹活一樣,離不開他人的幫助」 (【家政論】,5.14)。會被懲罰的只是丟棄盾牌、破壞陣形或是引發恐慌之輩,而絕不是那些沒能殺夠敵軍的人。
同樣的,西方人在看待裝備華而不實、高聲嚎叫或是發出恐怖雜訊的部落戰士時,如果對手在這樣的展示中,沒有秩序井然的行進以及對行列的保持,那麽他們的眼神裏也只有蔑視。
「可怕的外表可不會造成什麽傷害」,埃斯庫羅斯如是說(【七雄攻打底比斯】,397-399)。修昔底德描寫斯巴達將軍伯拉西達進攻伊利裏亞村民時的演講,是西方在古代對部落式戰爭的輕蔑總結:
進攻開始時,他們會給沒見過他們的人帶來恐懼。他們的人數似乎多得可怕;他們的高聲叫喊令人難受;他們在空中揮舞兵器的方式很是嚇人。但是當他們遇到那些能夠堅守陣地,抵抗他們進攻的軍隊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作戰時毫無秩序;他們沒有固定的陣形,因此一旦他們的軍隊在作戰中受到壓迫,他們並不羞於放棄自己的陣地;既然逃跑和進攻一樣不失榮譽,他們的勇氣甚至永遠難以經歷考驗……這種烏合之眾,一旦他們的第一次沖鋒遇到堅強的抵抗,他們便會退去,遠遠地發出威脅,以誇耀他們的勇敢;但如果對手在他們面前退卻的話,他們就會迅速地進行追逐,極力利用他們的優勢,表現他們在沒有危險的時候是多麽勇敢。(【七雄攻打底比斯】,4.126.5-7)
在進攻強固的陣列時,祖魯人遠比伊利裏亞人能堅持到底;盡管如此,修昔底德對於戰場上兩種不同行為——叫喊、虛張聲勢,與堅守陣線(所謂的「常規戰鬥秩序」)的對比,套用到英國-祖魯戰爭上也並不顯得過時。
在這兩場相隔千百年的戰爭裏,能夠以陣形進行操練、接受並執行命令、服從中央指揮鏈的士兵,在戰鬥中更可能以團隊和陣列的方式共同行進、停止和撤退。
時間將證明, 這樣有序的戰鬥體系,相比一群隨意進退的亂軍,能更有效地殲滅敵人。
希臘、羅馬
兼有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亞里斯多德作為希臘時代思想家中的典型,解析了勇氣的特性,對其與利己主義、服從和紀律的關系進行了最為系統化的分析。
在解釋為何某些型別的勇氣比其他的更可取、更具永恒性(跟國家的理念和對政府的信賴不可分割)這個問題時,他幾乎與其他希臘思想家都所見略同。
他謹慎地分析了五種軍事行動中的勇氣,並將其中之一公民勇氣放在優先位置。 這種勇氣只屬於公民士兵,因為在國家與同胞公民們面前,他們不希望表現出懦弱的一面,而且他們還渴望獲得公眾給予無私奉獻之人的榮譽認可。 「人,」亞里斯多德附和伯瑞克利的說法,「 勇敢起來不應當是被迫的,勇氣本身就是高尚的事物。 」(【尼各馬可倫理學】,3.8.5)
亞里斯多德同樣認可第二類明顯的勇氣,那就是訓練有素或裝備精良的士兵能具備的勇敢,這種勇敢源於他們握有的物質優勢。但是他警告人們, 這些據稱是勇敢的人可能名不副實:一旦他們短暫的優勢消失,很可能就會逃離戰場。
此外,亞里斯多德承認第三類表面上的勇敢,常常被誤認為真正的勇氣:這種勇敢是那些瘋狂的戰士所具備的狂熱之勇,他們毫無理性,因為痛苦、癲狂或暴怒而戰鬥,對於死亡或同伴的福祉毫不關心。 這同樣是一種曇花一現的勇氣,當魯莽的勁頭停住時,它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亞里斯多德眼裏的第四和第五類勇敢,盡管分別來自盲目的樂觀主義和無知,同樣也能夠滿足關於勇氣的準則。
有些人在戰爭中表現出英勇,僅僅是基於錯誤的認識,因此也難以長久。有的人勇敢則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的偏好判斷事物,相信此時命運站在自己這一邊;然而此類戰士往往會對戰場形勢做出錯誤的估計,同時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有利條件是變化無常的,可能在幾秒鐘之內就徹底改變。
無論何種情況, 他們的勇氣都不是基於價值觀和內在特點,更不是來自有序產生的精神支撐,因此無法持久,在戰鬥的白熱化階段也不夠穩定。
由此類推,某些人在無知狀態下的勇猛戰鬥,只是因為他們錯誤地感覺優勢在自己一邊;一旦他們意識到自己身處險境,他們馬上就會逃離戰場了。與樂觀主義者的情況一樣,這種無知無覺的狀態帶來了相對的勇氣,卻無法形成一個絕對的價值觀。
柏拉圖在他的對話錄【論勇氣】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在書中他借蘇格拉底之口辯稱,真正的勇氣,是士兵在行列中奮戰和維持陣列的能力,即使他知道將要面對怎樣的逆境也毫不退縮——這和那些看似英雄的人,只因為所有條件都有利於他時才奮勇作戰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在西方文明體系裏,人們很早就將紀律的理念制度化為堅守陣列和服從長官的行為,在他們看來, 長官們的權威來自憲法賦予的權利。
雅典少年們——那些守衛比雷埃夫斯港和阿提卡內陸地區的年輕新兵,會進行一年一度的誓約儀式,其中包含如下的承諾:「無論我身處戰線哪個位置,我都不會拋棄戰友……任何時候我都準備好服從明智行使權威的人,服從已經公布施行和未來將會生效的審慎明智的法律。」[M.托德,【希臘歷史銘文】(牛津,1948)第二卷,204]
像色諾芬和波裏比烏斯這樣的作者,將軍隊比喻成一連串墻壁組成的壁壘,每一面墻都是一個連隊,每塊磚都是一名士兵——是紀律的砂漿將士兵和連隊固定在準確的位置,確保整個壁壘的完整性。用色諾芬的話說,缺乏紀律約束的軍隊一團混亂,「像一群人離開一個劇院時一樣」。(【論騎兵指揮官】,7.2)
古典時代的文化不鼓勵民兵畏懼掌權者,也不煽動魯莽沖動之勇。士兵們在戰鬥中的位置和移動,以及頭腦和精神上對指揮的接受程度,都應當是可預見的。
在戰鬥的高潮階段,所有人在面對死亡時,都可能會丟掉對國王的敬畏。勇敢——如亞里斯多德所言,也可以成為易變的情緒。
哥薩克人就像現代軍事史學家筆下的遊牧戰士一樣,在追擊中膽大妄為,但是當角色反轉,他們在發現自己與敵軍部隊展開沖擊戰時,則變成了可憐的膽小鬼。
羅馬軍團走得更遠,他們試圖將公民的勇氣與官僚制度結合起來,透過訓練、緊密陣形中士兵的密切聯系、軍團制度以及否認個人勇武的態度達到這一點。
在羅馬,1世紀初的著名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對羅馬人的戰場優勢曾做出過評論,這段評論相當著名,時常為人引述:
倘若你看到羅馬軍隊的行動的話,就能理解,這個帝國完全是他們的英勇所造就的,而不是命運的賜禮。他們不會等到戰爭爆發才來操練武器,也不會在和平年代無所事事,只在需要的時候才動員起來。完全相反,他們似乎出生時手中就拿著兵器;他們絕不會中斷自己的訓練,或是等到危急時刻才行動……他們的演練就像不流血的戰鬥,他們的戰鬥則不過是血腥的演練。(【猶太戰爭】,3.102-107)
近400年後,韋格蒂烏斯在4世紀撰寫了一本羅馬軍事體制手冊,他再次將訓練和組織視為羅馬取得勝利的根基:「確保勝利的不是單純的數量和天生的勇氣,而是技巧和訓練。我們可以看到,羅馬人民之所以能夠征服世界,無非是因為他們在軍營裏進行訓練,在戰爭中進行實踐。」(維格蒂烏斯,【羅馬軍制論】,1.1)

比希臘方陣更強大的羅馬軍團
韋格蒂烏斯的著作在法蘭克和其他中世紀西歐日耳曼君主中相當流行,因為他強調建立嚴守紀律的陣線和縱隊來進行戰爭。
在蠻族君主的眼中,他的作品展示了如何恰當引導條頓式的狂熱戰士,將其轉變成精力充沛但嚴守紀律的步兵。
陣列戰術與平等主義
源自歐洲軍隊的紀律是透過訓練和機械記憶來制度化一種獨特勇氣型別的嘗試,這種紀律能夠在士兵穩定佇列、保持秩序時得到最好的體現。
西方人執著地熱愛操練密集隊形,這並非是沒有道理的:倘若戰場上局勢不妙,所有人都想要逃跑的話,訓練和信仰就能阻止這種集體潰逃的發生。
解決問題的關鍵,並非在於讓每個人都成為英雄,而是創造出一群戰士,他們在總體上比缺乏訓練的人更能勇敢面對敵人的沖鋒,即便激鬥正酣時還能服從上級命令,並始終忠誠保護自己的同袍。
他們對永久性的、持續存在的公民體系保持著不變的順從,而非追隨某個暫時性的部落、家族或友人。
人們怎樣獲得紀律,然後又將其保持若幹世紀之久?古希臘、羅馬和後來的歐洲軍隊,從訓練體系以及士兵-國家間的明晰成文協定中找到了答案。
17世紀的指揮官,比如拿索的威廉·路易,他將歐洲人集中使用火力的傾向,和古希臘羅馬作者筆下強調維持緊密方陣與軍團的戰術直接聯系起來。
秩序井然的行軍方式,以及組成戰線的能力,都帶來了直接而更為抽象的優點。當軍隊以密集陣形移動時,能實作更快速和有效的部署,傳達命令也更為便捷。密集縱隊和橫隊的陣形是火力集中化的基礎,這兩種布陣方式使得步槍隊的持續齊射成為可能。
此外,訓練體系本身還能從思想意識上強化士兵對命令的貫徹程度。與戰友同步前進的意願,來源於一名西方士兵對指揮官命令迅速而準確的執行。
如果一名士兵能在陣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同伴一起協調前進並保持行列的話,這樣的人相比那些無紀律的雜牌兵,肯定更能服從其他關鍵性命令,在良好的指揮下使用武器,最終徹底擊敗敵人。
西方人特別強調一種奇特的觀念,即適時集中兵力:
但事實上很明顯的是, 這種密集陣列的操練方式,並沒有出現在大多數國家的軍隊和軍事傳統中。 從世界範圍看,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及近現代的歐洲人利用心理效果來適時集中兵力、保持團隊的方法,只是一個特例而已,並非軍事史上的通行原則。那麽,為何歐洲人在發掘密集佇列操練的非凡潛力方面,擁有一技之長呢?(W.麥克尼爾,【始終在一起】,4)
麥克尼爾繼續給自己的問題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答案,但他整個探討的核心依舊是公民社群理念,或者說,是 自由人與軍事組織達成協定,由此獲得相應的權利並承擔對等的義務。
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是高度個人主義的西方人,也不會將軍事訓練看作是壓迫,而是將其當成平等主義的體現 ——在這樣的訓練中,所有背景各異的士兵,都被轉化成身著制服,外觀統一而行動一致的整體,此時個人特征和差異化的地位都暫時消失了。
麥克尼爾相信, 訓練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希臘羅馬自由概念的銘印,是積極的、共享的公民權」。
我們可以補充的是,在希臘重裝步兵方陣的密集佇列中,每個人都占據著一個與其他人相當的位置,就像在公民大會中的情況一樣,每個男性公民都具有和其他人一樣的權利—— 古希臘鄉村從根本上促進了平等主義,那裏農場星羅棋布,沒有大地產的存在。
如果要舉一個更為現代的例子的話,這就像青少年們進入維吉尼亞軍事學院(簡稱VMI)的新生班級後的情況一樣。
在那裏,他們馬上會被剃掉頭發,拋棄平民的服裝,並且學習如何步調一致的行進和操練——在這裏,他們的等級觀念、種族思想與政治態度都消失了,一切元素統統都融入軍校生統一外觀、步調一致的高唱頌歌的佇列中。
即使是最兇暴的街頭流氓或摩托車匪幫——他們帶著烏茲衝鋒槍,多年來在對抗同類暴徒中積累了豐富的槍戰經驗——他們依舊是一群烏合之眾,無法在戰鬥中抗衡武裝起來的VMI學員團。
和暴徒相比,VMI學員中或許沒有人品行不端留下前科,或是在盛怒之下射殺過他人,但他們依舊擁有更強的戰鬥力。
當然,這些學員與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軍隊裏走正步的步兵相比,仍然有不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完全明白自己的服役狀況,同時軍法體系也會保護他們不受隨意的懲處——與此同時,這些人也同意,倘若他們恣意妄為地使用暴力,就會受到重罰。
這就是訓練和紀律的力量,透過文明的洗禮,人們從部落式和血親家族式的義務體系中,昇華出公民軍隊的忠誠理念。
以某種觀念來說, 在行列和陣形中進行戰鬥的方式,恰恰是西方式平等主義的基本表現, 在思維一致、訓練有素的同伴組成的磨滅個人特質的方陣中,戰場外所有的等級差異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可以推測,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迦太基人雇用斯巴達戰術大師科桑西普斯,和19世紀後期日本人征召法國和德國野戰教官的行為,是基於同樣的理由:不論是方陣兵還是步槍手,他們試圖創造出自己的士兵,希望這些戰士能夠在行列中操練和前進,以西方人的致命方式進行戰鬥——羅馬人和美國人都很快發現了迦太基人和日本人的進步。
約2000年前的韋格蒂烏斯,就概述了西方軍隊中這種強調訓練的獨特狀況:
對新兵進行軍事訓練之初,就應當進行走正步的操練。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無論行軍時還是戰鬥中,首先要勤加註意的,便是始終使全體士兵保持一致的步伐。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只有依靠堅持不懈的操練,如此才能使士兵們學會在快速運動的同時保持陣形。如果一支部隊在遭遇敵人時被分割,而又不能保持嚴整的隊形,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羅馬軍制論】,1.1.9)
歐洲人軍事紀律傳統的核心,就是對防禦的強調,或者說,正如我們在赫洛多德的著作中所見到的,歐洲人相信,士兵堅守在佇列裏的行為,遠比成為一名優秀的殺手更為重要。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7.1324b,15ff)中,講述了 非城邦人民的古怪風俗,這些人都異乎尋常地註重殺死敵人 ——斯基泰武士在殺死一個人之前,不能從一個儀式性的杯子中飲酒;伊比利亞人將尖刺環布在武士墳墓的四周,代表他們在過去戰鬥中殺死敵人的數目;在交戰中砍倒一個人之前,馬其頓人都必須在腰間綁韁繩而不能掛腰帶——這些與城邦人民的習慣形成了鮮明對比。
祖魯軍隊同樣遵從古老的部落傳統,武士接受柳條編成的項鏈,後者標誌著一名武士得到證實的擊殺敵人的數目。
就像亞里斯多德也曾指出的那樣,西方軍隊強調的內容包括防禦時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與軍隊的訓練和秩序有著緊密的聯系,同時也對保持陣地或陣形的完整極端重視。
西方軍隊中所有的軍事條例都清楚表明,懦夫是不顧形勢逃離陣形或是拋棄佇列的人,而非沒能成功殺敵達到某一特定數位的人。
一名阿茲特克武士,靠著擊倒和捕獲一連串的貴族俘虜來建立威望;而一名西班牙的火槍手或長矛手,則以保持在戰線中的位置為自己的最高使命,對他來說,自己保持橫隊或縱隊的協同一致最為重要,他應該支持己方的隊形,幫助整支軍隊默默地碾碎敵人的陣列。
在祖魯戰爭中,英國人和祖魯人一樣,有其固定的進攻模式,戰鬥的方式也可以被預見。然而,英國人的軍事體系突出陣形、訓練和秩序,並將能夠維持以上這些軍事要素的人視為戰場上的勇者。
從理論上來說,士兵應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戰鬥——他們發動齊射,有秩序地進行集群沖鋒,沒有命令絕不後退,從不輕率地發動追擊,也不會在追擊時花費太長的時間——這樣的軍人,才能擊敗敵人,取得勝利。
1879年的英國-祖魯戰爭,為祖魯式勇敢與英國式紀律的較量,提供了極好的註腳。 然而,盡管祖魯軍人經常被描述成像英軍一樣英勇的戰士,卻沒人會聲稱他們是擁有紀律的士兵:
關鍵的發明是國家的產生,也就是用公民社會取代血親家族的社會。公民政府是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線。
只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才能支撐起龐大的軍隊。同樣只有國家才能用紀律約束人民,使其成為士兵而非蠻勇的武士。唯有政府能指揮士兵走向戰場,而非要求武士參加劫掠;也唯有政府才能懲罰拒絕作戰的人…… (大司馬按:此處的政府特指公民政府。)

希臘羅馬公民兵強大的戰鬥力
背後是民主與共和的國家
原始部落的武士,缺乏有組織且結構完善的政府的支撐。這樣的野蠻人不願屈從於紀律,也沒有能力或者耐心服從明確的指揮。他只能從捕殺動物的過程中,學習到某些膚淺的戰術準則……同時他也太過關註眼前的戰鬥,而無法從長遠考慮,策劃戰役的進行與發展。(H.特尼-海伊,【原始戰爭】,258)
羅克渡口的參戰者中,有11人獲得了維多利亞十字章——幾乎有十分之一的參戰士兵得到了這一獎勵。盡管我們有若幹目擊材料顯示,英軍的神槍手們遠距離射殺了大量的祖魯人,但 並沒有人因為殺人的數量而獲獎。
現代評論家認為,這樣濫發獎勵的行為,正是為了緩解伊桑德爾瓦納災難帶來的負面情緒,同時消除公眾對英軍士兵戰鬥能力的質疑,這種質疑在維多利亞時代可謂極其常見。至於真實情況,或是或否,沒人能說清。
然而,在漫長的軍事歷史中,很難再出現和羅克渡口相似的例子:一支兵力處於一比四十劣勢的軍隊,在敵人的圍攻中非但能夠存活下來,而且每損失一個防守者,便能殺死20名進攻者。
當然,在那個年代裏,世界的其他地區幾乎沒有和歐洲士兵一樣訓練有素的戰士, 絕大多數歐洲士兵在戰場紀律方面,也難以匹敵19世紀末的英國紅衫軍 ,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精銳中的精銳。
本文節選自【殺戮與文化】,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先發。該書解析從希臘羅馬開始,西方總是在戰爭中占優勢的原因,認為首要的是平等主義的觀念,以及支撐這種觀念的制度和社會,解讀非常精彩,大司馬強烈推薦。
歡迎關註文史宴
專業之中 最通俗 ,通俗之中 最專業
熟悉歷史 陌生化 ,陌生歷史 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