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太陽與梵高的向日葵
「你的眼睛閃爍著光芒,仿佛那太陽燦爛輝煌。」這首舉世聞名的【我的太陽】經由帕瓦羅蒂的演繹傳到我耳畔時,我早已有過我的太陽,而且不是比喻,是真正意義上的那輪太陽。
「小小少年,很少煩惱,眼望四周陽光照。」在「紅太陽照邊疆」的歲月裏,在小學的第一堂美術課上,小小少年用鉛筆為並不很圓的太陽以及毫不對稱的光芒塗了上黑色。老師看到後並沒有呵斥,而是耐心地問:「你每天見到的太陽是黑色的嗎?」每天溫暖我的太陽當然是金色的,但我只有黑色的筆。老師微笑著說,那就不要塗色,不能再這樣畫太陽了。
瞧我多麽無知。自第一堂美術課遭遇滑鐵盧之後,我再也沒有畫出過與所描摹之物有一絲相像的東西,說明我壓根兒就沒有這方面的任何天賦。看著同學能夠把向日葵、牛、羊都畫得那麽逼真,我十分羨慕。到了初中,終於明白,我連立體圖形都想象不出來,想畫成圖畫,這不是天方夜譚麽?有精神動力,但缺乏智力支持啊。不過,這倒更加喚起了我對繪畫的好奇。雖然我根本就不懂,但人有我無,便想時時看上幾眼,艷羨人家的獨門絕技,附庸風雅而已。
「畫法稚嫩,畫上有黃色的太陽,一團團卷曲的雲霧,畫面上方一隅有兩只卡玫基飛過一艘四方形的船,船上有四個鉛筆畫的小圓圈。」愛爾蘭作家科倫·麥肯在【無極形】中塑造的這個十歲女孩顯然比我有天資得多,我老頭兒應該仰望之。我常看到大人們在逛商場時將小孩臨時寄放在遊樂角,孩子們既可玩樂,亦可隨意繪畫。那些稚嫩的畫作充滿想象,色彩搭配得恰到好處。這些童稚給我當老師綽綽有余。我外甥女零基礎,學了半年就能畫人物肖像,惟妙惟肖,令我驚嘆。
日前去了一趟著名的大窯文化遺址所在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大窯村,眼界大開。這裏家家戶戶的墻上全是美術作品,卻自稱「塗鴉」。人物肖像、天空圖景、老物件……裝點著這個小小的村落。這是我第二次見識塗鴉部落,上一次是在台灣省台中市的彩虹眷村。一位老軍人在那個地方的墻上畫滿了彩虹線條及動物、花朵、人物,構建起了一個童話世界。結果,整個村子成了旅遊景點。這位老人顯然不是畫家,連畫友甚至都算不上,作品是名副其實的「塗鴉」,畫法非常稚嫩,像是兒童隨意所作,但色彩斑斕,讓人眼花瞭亂,覺得新奇。但平心而論,倘使讓我去畫,我仍然不如人家。我連簡筆畫都畫得走樣,更別說照貓畫虎。

如同有些人喜歡把裝幀豪華的書擺在家中顯著位置,以昭告別人自己有文化一樣,我也將梵高的向日葵燒制在了一塊玻璃小墻上,以示我這個畫盲知道這位繪畫大師及其作品。其實,我對這幅畫根本就不懂,只是為了裝樣子,生怕別人以為自己不高雅,虛榮心在作祟罷了。
在這種虛榮心的驅使下,我葉公好龍,遊走於各種美術展覽場所,在上海博物館參觀了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畫展,見到了高更、莫奈、梵高、塞尚、雷諾亞等著名畫家的傳世作品,據說是真跡而非復制品;在浦東美術館觀看了現代派畫展,一竅不通,毫無感覺;在內蒙古美術館見識了當地畫家的不同畫風的作品,只覺得畫得挺好,無法用專業術語進行評判。

在各種參觀中,我只是一個打卡者,立此存照而已。有些帶著孩子的大人,邊看邊講,頭頭是道,行家一般。我悄悄跟在人家後面,邊看邊聽,倒也收獲頗豐。此時,我這個小白慨嘆學識不如人家,人家雖非高山,但足為我師,也令我仰止。
我還買了很多畫家寫的書以及描寫畫家的書,時時翻翻,想接近人家的神奇世界,結果始終站在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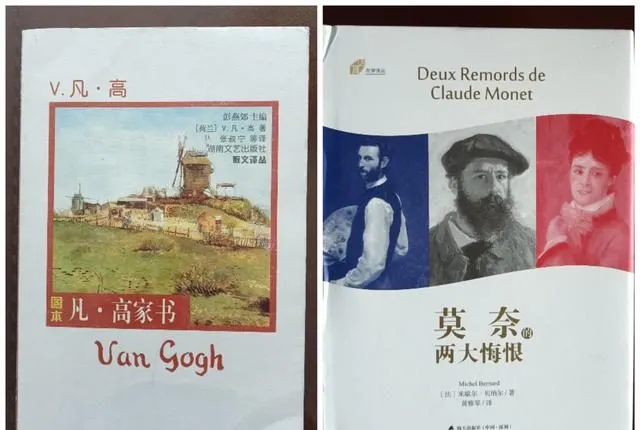
米蘭·昆德拉在【不朽】中說,「世界上所有的美術館都擠滿了人,就像從前的動物園一樣;有愛看新奇事物癖好的旅遊者凝視油畫,仿佛這是關在籠子裏的動物。」這位大師閱盡人間滄桑,一下子就看穿了像我這樣看星星的瞎狗。既湊熱鬧,又裝模作樣,還怕露餡。結果,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我們的「裝」被戳穿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憶錄【一個規矩女孩的回憶】中說,「白天我去參觀畫展,久久地在盧浮宮的畫廊裏遊蕩。」她也不是畫家,但生在法國,每天在盧浮宮徜徉,誰能說人家是在附庸風雅,更何況人家是哲學家波伏瓦呢!
上海明珠美術館舉辦【維克多·雨果:天才的內心】畫展時,我遠在天邊,否則一定會前往領略一下這位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在繪畫方面的高超造詣。倘使生命中真的有這樣的參觀,那我就可以說,這次中文狗可不是附庸風雅,而是在擴充專業知識。
我雖是美術的門外漢,但周圍卻不乏有繪畫天賦者。一位暌違已久的朋友用彩色鉛筆畫各種水果和鮮花,在抖音上曬。當得知人家系初學時,我羨慕不已。呼倫貝爾那家我曾工作過的單位竟然有兩位畫家。我離開後,我們先後在同一個條線工作。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從未向大師索畫,人家更未曾表示有興趣贈我大作。倒是在與兩位大師交往的過程中,我赴了數不勝數的飯局,喝了不計其數的啤酒,也領略了一些他們身上氤氳的藝術氣質。

在上海的田子坊、豫園、南京路到處都有為遊人畫像的攤點,畫漫畫像、肖像畫,立等可取。畫師皆濃發長髯,年輕有為,極富藝術範兒。我曾觀摩數次,每次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人家腦袋與我的大頭結構不同。稍稍覷你一眼,即能抓住你的特點,寥寥幾筆,你就躍然紙上。於專業人士而言,這或許只是雕蟲小技,但在我看來,這已勝那個黑太陽少年千萬倍矣。
文學與繪畫本來相通,有人樣樣皆精,有人獨擅一門。對通才我向來欽慕,就像活躍於【中國詩詞大會】的康震教授,專業乃中文,但畫得簡潔傳神,口才亦相當了得,小我五歲的這位陜北人是我心中的男神。
其實,我大學時的老師班瀾先生更是我心中的老男神。老師詩書畫俱佳,吟詩作文皆信手拈來,亦常常【班瀾說畫】【自說自畫】,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遺憾的是,作為學生,我未得老師學問之萬一,慚愧啊!有文友讀了我的一些作文後,稱我為班老師的高足,我真是愧不敢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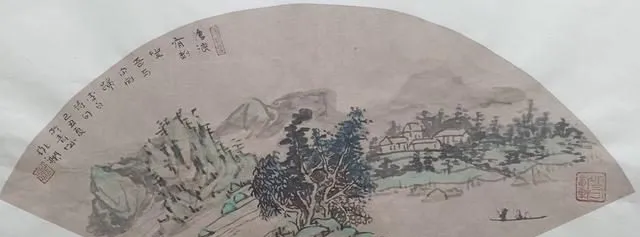
老師學富五車,藝作等身,八秩揮毫著文不輟,而我略識之無,粗通作文,就憑我在參觀畫展時的那個無知樣,僅可算先生之劣徒,豈敢妄稱高足,以辱班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