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時光當鋪NO1 2024-01-10 06:02 發表於廣東

詹姆士·萊特(James Wright 1927.12.13~1980.03.25)生於俄亥俄州馬丁斯,就讀於肯庸學院,曾師從大詩人勞勃·弗羅斯特,後與勞勃·勃萊一起建立「深度意象」詩歌流派。成為美國戰後反派詩歌的主要陣地。1957年以詩集【綠墻】獲得著名的耶魯青年詩人獎,從此顯露文壇。1963年出版的詩集【樹枝不會折斷】確立了他在美洲詩壇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垮掉派」和「紐約派」相對應的地位,詩歌中新穎的實驗品質讓評論界迷惑又震驚。他的【詩歌集】於1972年獲得普利策詩歌獎。他終身在大學任教,兩度獲得古根海姆獎。1980年因癌癥在紐約去世。但他留下的詩作卻足以使他在二十世紀美國後現代詩歌中占有一席之地。
A Perfect Indian ,Sinéad O'Connor - Universal Mother
詩人也是手藝人
巴黎評論 VS詹姆士·萊特
巴黎評論:萊特先生,您曾在明尼蘇達大學與約翰·貝裏曼一起任教。作為詩人,您對他的感覺如何?
詹姆士·萊特 :約翰·貝裏曼是一位非常偉大的詩人,他的作品將不朽。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手藝人,還因為他在詩歌中揭示了一個事實——我認為他還沒完全實作——即一首詩不僅是一件可被創作的、構思精美的獨立作品,而且詩歌也是一種可以被不斷創作甚至幾乎可以實作一種自我再造的事物。透過他作品的生長——他從未停止過生長——他表明,在人類的想象力中,詩歌是一種類似春天的事物。威廉士醫生之所以是位偉大詩人原因也正在於此。
貝裏曼的偉大當然包括他對語言技巧的徹底掌握。但他也證明了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擺設,詩歌與生活本身,與我們的生存方式之間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
巴黎評論:成為一名詩人意味著什麽?
詹姆士·萊特 :我只能告訴你這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麽。我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手藝人,一個賀拉斯式的手藝人。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愛德華·湯瑪斯,我想成為的大師是賀拉斯,他能用完美無瑕的詩句幽默而親切地寫作。我這輩子可能已經實作過兩次了,而這就是我想成為的。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型別的詩人。比如傑克·芬尼根。愛爾蘭詩歌有一個傳統,詩歌本身就是對某人提出的問題的回答。我認為這是一種文學傳統,你不會相信的,但我在上帝面前發誓這是真的。我還想提及另一個愛爾蘭傳統。它基於純粹的傲慢和對生活的決心。詩歌能保持生命本身的活力。只要你能唱出它,你就能夠忍受幾乎任何事情。
巴黎評論:你覺得做一個詩人很痛苦嗎,就像背靠墻對著空口袋演奏音樂一樣?
詹姆士·萊特 :如你所知,我也是一名教授。我寫過詩集,但我是一名教授。對我個人來說,教學是一門帶給我更多快樂的藝術。我沒有試圖把自己看成詩人,我說的都是真心話。也就是說,與我的學生接觸,閱讀書籍,嘗試與學生分享我的想法和感受,給了我更多的快樂,我將其視為一門高級藝術。記住,老師包括耶穌、蘇格拉底、悉達多、梅斯特·埃克哈特。簡而言之,便是如此。
巴黎評論:這背後是否有一種感覺,作為一名詩人,要對太多的事物太過在意?
詹姆士·萊特 :不,對我來說並不如此。我在意很多事物,僅僅是那些碰巧很陌異的,碰巧對我來說很陌異的事物。雖然我說我的理想是成為賀拉斯式的詩人,但我懷疑這些事情也曾發生在偉大的賀拉斯身上。有時,有一種生命的力量,就像春天一樣,在你甚至還沒有請求它成形的情況下就神秘地成形了,這很可怕,太可怕了。這或許在我身上已經發生了幾次——有幾次我幾乎可以毫不費力地完成那首詩。
巴黎評論:哪些詩?你還記得哪些詩歌是一氣呵成完成的嗎?
詹姆士·萊特 :一首題為【父親】,另一首是【祝福】。如果你問我,它們從何而來?我或許只能答道,我怎麽知道?作為一名詩人,有時,你得任由自己被生活擺布,但生活並不總是仁慈的。
巴黎評論:你教過創意寫作?
詹姆士·萊特 :我試過教過一次,但完全失敗了,因為我所能做的就是坐下來和全班同學交談。有人會問我一個問題,某事我會怎麽做,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咕噥。這並不是說創意寫作無法教授,它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就像我們所知的狄奧多·羅特克的工作,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老師。
巴黎評論:他教了你什麽?
詹姆士·萊特 :他主要傳授技藝,和洛厄爾及貝裏曼一樣,他是個完全自覺的手藝人。他明白,技藝和神秘想象之間的關系,並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有人認為非常精細、自覺的技藝會抑制你的感受,但羅特克明白,精細、自覺的技藝可以解放你的感受和你的想象力。
巴黎評論:我知道你獲得了創意寫作碩士學位。但我不清楚有多少詩人在科班學習過創意寫作。這真的有用嗎,或者說一個詩人必需自學那些最基本的事物?
詹姆士·萊特 :我讀創意寫作碩士,是為了盡快讀完它。難道你不應該靠自己來學習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嗎?史坦利·庫尼茲曾對我說:「你必須進入自我的深淵,真正的深淵,然後你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爬出來。這不可能是別人的方式。它必須是你的。」
我來告訴你我為什麽透過寫一本詩集來拿碩士學位,我想成為一名認真的教師,我想透過非常途徑拿到碩士學位,這樣我就可以認真攻讀博士了,我做到了。我博士寫狄更斯。作為一名教師,我的主專業是英語小說史。
巴黎評論:在【綠墻】的附註中,你提到了羅賓森和弗羅斯特的影響。
詹姆士·萊特 :嗯,那時我年紀大了一些。寫那本書的時候,我二十七歲。我能告訴你當時都在考慮些什麽。我寫過一首名為【聖猶大】的十四行詩,在這首十四行中,我試圖在技術層面做兩件事:寫一首真正的彼特拉克體十四行,同時也是一首戲劇性獨白。這是從羅賓森那裏得到的啟發,他有一首十四行詩叫【安南代爾是怎麽出去的】。然後就有了我那首關於猶大的詩,我覺得,猶大是最終迷失了的背叛者。我不認為那首詩是對羅賓森的刻板模仿,但我明白,如果沒讀過羅賓森的十四行,我不會寫那首詩。
巴黎評論:你從弗羅斯特那裏學到了什麽?
詹姆士·萊特 :我想,首先是他面對宇宙時深邃、令人生畏且極具悲劇意味的視角,於我而言這就是真實。我從沒說過生活是無意義的,我說過它是悲劇性的。我認為這一點非常寶貴。天啊,有時我覺得自己太快樂了,不知道該拿自己怎麽辦。這真是太痛苦了。而且,從技藝上講,弗羅斯特也有獨特之處。他懂得如何剔除形容詞。一個例子是他的詩【倒伏】。這是首很短的詩,裏面有一個副詞——「的確」——那個副詞,在我看來,子彈樣一擊必中。
巴黎評論:弗羅斯特——美國偉大的自然詩人。你會稱自己為自然詩人嗎?
詹姆士·萊特 :部份層面,會。
巴黎評論:我之所以要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你早期詩歌部份是自然詩,但也有很多關於人的詩。【樹枝不會折斷】幾乎完全是一本自然詩。【我們聚在河邊好嗎】則是另一回事,更個人化。而那些可能源於你在紐約的生活的新詩歌,幾乎都是都市詩。我的意思是,這裏有都市景觀,而不是早期的明尼蘇達和俄亥俄的景觀。
詹姆士·萊特 :人類不幸地成了自然的一部份,也許自然會有自我意識。哦,我多麽想成為一只山雀啊!但我不可能成為一只山雀,我所能成為的就是我自己。我熱愛自然世界,我意識到其中的痛苦。所以我是一個書寫自然中的人類的自然詩人。我愛尼采,他稱人為「生病的動物」。
巴黎評論:你最喜歡自己哪本書,覺得哪本最好,這麽問公平嗎?
詹姆士·萊特 :是的,很公平。我最喜歡的詩集是【聖猶大】。在那本書中,我試圖接受我感受到的自己生活的真相,那就是一個人做了很多來尋求幸福,但他卻並不幸福。我沒有幸福的天賦。但有些人的確有。在【聖猶大】中,我試圖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不是一個天生幸福的人。有時我很幸福,但從本質上講,我是個可憐的混球。我試著用我能找到的最清晰、最完美的形式,用所有傳統的方式來接受這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自衛行為,因為當時我很痛苦。在我完成那本書之後,我就永遠完成詩歌了。我當時真的相信,我已經盡可能清楚、直接地說出了我必須說的話,對於這門藝術,我已沒有什麽可做的了。
巴黎評論:你以前跟我說過。當時遇到了什麽問題,你又是怎麽重新開始的?
詹姆士·萊特 :那時候,出於個人原因,也出於藝術原因,我走到了一條死胡同。當時我很絕望,通常能安慰我的是詞語——我總能求助於它們。但突然間,在我看來,詞語本身死了,我的意思是在我體內死了,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給勞勃·勃萊寫了一封長信,因為他的雜誌上有格奧爾格·特拉克爾一首詩的譯文。幾年前,在維也納大學,我讀過特拉克爾的德語詩歌,而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麽處理那些詩歌,不知何故我意識到,那些詩歌具有一種生命的深度,正是我所需要的。特拉克爾是一位用平行結構寫作的詩人,只不過他忽略了對一個意象和另一個意象之間的關系進行中介性和理性的闡釋。我覺得,特拉克爾對我的影響不亞於任何人。有趣的是,他的回復只有一句:「來農場吧。」我就去了那個農場,我們一見面就開始一起轉譯特拉克爾了。
巴黎評論:他當時是否對你的創作產生了可歸因於他的強烈影響?
詹姆士·萊特 :是的。他讓我清晰認識到,我試圖掌握的詩歌傳統並非唯一,而且在這種傳統中,我已走進了死胡同。他提醒我,詩歌是一種可能性,盡管所有的詩歌都是形式化的,但存在很多形式,就像存在很多感受的形式一樣。
巴黎評論:隨後出版的是【樹枝不會折斷】。這些詩歌是怎麽出現的?
詹姆士·萊特 :這本詩集的中心,是我重新發現了早已被我遺忘了的,身體的無窮樂趣。每個星期五下午,我都會去勃萊的農場,那裏有很多動物。西蒙是一只艾爾谷犬,大衛,我美麗心愛的大衛,那匹凹背的帕洛米諾馬,西蒙和大衛經常去勃萊的谷倉。他們允許我加入他們,和他們一起眺望著玉米地和大草原。我們就待在那裏。所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有時我也可以很快樂,但我卻忘記了這一點,而和這些動物在一起讓我回想起了這些。這就是這本詩集的主旨:重新發現。我一點也不討厭自己的身體。我非常喜歡自己。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的譯者角色——譬如你和勃萊的合作轉譯——對你自己的詩歌創作有什麽影響?
詹姆士·萊特 :這讓我擁有了進一步的可能性,去言說一些我想從一開始就想言說的事物。不幸的是,我認為自己被詛咒了,我覺得我必須言說,要麽我會死。我認為現在世界上大多數人活得都很不幸福。我不希望人們不幸福,我很遺憾人們不幸福。我希望我能做點什麽。但我要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無能為力。我想自從我開始寫作,我都一直在努力言說。這也是我詩集的主旨。
巴黎評論:【樹枝不會折斷】及後來的詩,被描述為超現實主義,你對此有什麽反應?
詹姆士·萊特 :它們不是超現實主義,而是賀拉斯主義和古典主義。如果它們看起來像是超現實主義作品,只能說明我試圖達到一種清晰之境的努力失敗了。它們不是超現實主義作品,我也不是超現實主義者。超現實主義的關鍵元素不在於結構和形式,而在於它很有趣。法國的超現實主義者以喜劇作為回應,而我們唯一理解這一點的美國超現實主義者——不,我們有兩個。一個是馬爾科姆·考利的【流放者歸來】。不,我們有過三位——E·E·卡明斯是另一位理解這一點的人。而唯一一位理解法國超現實主義原則的美國詩人是來自俄亥俄的——還能是哪裏——傑出詩人肯尼斯·帕欽。
巴黎評論:在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我們相聚在河邊吧】(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我最喜歡的一點是它的完整性和連貫性。換句話說,它不完全是一首敘事詩,但也不僅僅是獨立詩歌的集合。你對這本書有什麽看法?
詹姆士·萊特 :我非常小心翼翼地寫作這本詩集來迫近那種效果。至於它是否成功,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該由我評判。絕不該!我非常清楚這本詩集結構完美,而且從第一個音節到最後一個音節,我都確切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巴黎評論:那是指什麽?你在做什麽?
詹姆士·萊特 :我試圖從死亡走向復活,再走向死亡,最終挑戰死亡。好吧,如果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當時試圖寫的是一個我愛的女孩,她已去世很久了。我試圖在書中和她一起歌唱。我不是重新創造她,你無法重新創造任何人,至少我不能。但我想,也許我可以接受那種在我心中縈繞已久的感受。這本書被詛咒了,因為它是如此精心編織的夢。
巴黎評論:你在創作詩集時,腦海裏通常都有連貫性的構思嗎?
詹姆士·萊特 :每次都有。我有沒有和你提過勞勃·弗羅斯特的話——這是一句非常賀拉斯式的話——如果你有一本二十四首詩的詩集,那本書本身就應該是第二十五首。我每次都努力如此,每次。
巴黎評論:好吧,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你在詩集【綠墻】中的組織原則是什麽?你采用的是什麽結構原則?
詹姆士·萊特 :我試圖從人的墮落開始,並且承認人的墮落是一件好事,一種快樂的過失,一種愉悅的罪過。然後我嘗試用我的方式穿插編織自然詩和在自然中人類的苦難,因為他們是具有意識的。這是我的構思。但我不認為這本書在結構上很連貫,你知道,那本書刪掉了大約四十首詩。
巴黎評論:你對單首詩歌也這樣做嗎?重寫和修剪它們?
詹姆士·萊特 :是的,我經常重寫我的詩,以至於有時我會搞不清楚哪一版才是最終發表的。在我認為我已經把一首詩打磨得恰到好處之前,是不會輕易放手的,而這就涉及各種奇怪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你重寫它,你得知道什麽時候該停下來。
巴黎評論:你曾說過,對於一名詩人而言,如何成為一個手藝人是個問題。這是什麽意思?
詹姆士·萊特 :因為我在詩歌中的主要敵人就是口若懸河。我的家庭背景有一部份是愛爾蘭裔,這意味著很多事情,但在語言方面,這意味著有時說話太輕易了。我一直在思考賀拉斯的觀點,貝倫在一封寫給默裏的信中非常準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寫得輕率,讀得遭罪。」我的毛病就是口若懸河。我說話和寫作都太輕易了。史坦利·庫尼茲是我的心目中的大師,他告訴我他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的書都很簡要,我的也如此,他一直在竭力精簡它們。我毫不懷疑,有些詩人透過某種天賦就達到了旁人渴求的難度。但無論詩歌是什麽,它都是一種掙紮,而詩歌的敵人,致命的敵人就是口若懸河。這也是我努力精簡詩歌的原因。
巴黎評論:當你坐下來寫詩時,會發生什麽?你是從一個想法、一個主題、一個節奏開始的嗎?
詹姆士·萊特 :就我自己而言,通常是從節奏開始,而非想法。我不知道自己將要寫些什麽,我寫完之後的四分之三的時間裏,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寫了什麽。我不會說我是一個失意的音樂家,但我熱愛音樂,我想這就是我通常以這種方式開始一首詩的原因。音樂讓我對詩歌中的數量的可能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巴黎評論:但你能做到嗎?真能把音樂性的品質轉變成文字嗎?
詹姆士·萊特 :伊莉莎白時代的詩人們的的確確做到了。當他們發明素體詩時,不知為何他們也領悟到這是一種可唱可念的方式。但他們並沒讓這種形式支配他們。見鬼,能找到一萬個例子——莎士比亞在他的戲劇中融入了歌曲,賓·瓊生寫了許多優美的歌曲,約翰·道蘭爵士,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當時正值巔峰。約翰·哈靈頓爵士、約翰·戴維斯爵士和他的【認識你自己】、喬治·皮爾。他們都是。
華特·惠特曼也懂得怎麽做。雖然他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麽,但他做到了。讓我舉個例子,他的詩歌【我聽見了你,莊嚴甜美的管風琴】有這樣的詩句,你不需費力就能聽出效果:「秋風,我漫步於黃昏的樹林聽到你在上空長嘆憂傷如斯。」
巴黎評論:我們在談論詩集裏的條理性。在整理【詩集】時,你腦海中有沒有一種整體統一性的考量?有位評論家稱他發現你所有早期詩集中都存在一種探尋,但這種探尋在「新詩」部份得到了解決。
詹姆士·萊特 :等著看我的新詩集。我出版【詩集】是因為我正在寫一本新詩集,而之前的詩集都在阻礙我往前。我想這(出版【詩集】)可能是把它們從脖子上拿下來最實用的方法。一旦我完成了某事,我就必須擺脫它。我之所以出版【詩集】,也是因為我是時候滾出該死的美國了。
巴黎評論:新詩集名為【兩個公民】,書名意義何在?
詹姆士·萊特 :我的妻子安妮,她對我太重要了,她介紹我去歐洲,我們都喜歡歐洲。但我們清楚,我們也愛美國。安妮幾年前曾在羅馬海外學校和巴黎的美國學校教過書,所以她讓我試著去法國和義大利。我自認是一個維也納人,嫻熟德語。安妮能說點兒法語和義大利語。我們是兩個公民,混球王八羔子美國的公民。但我們同樣也是歐洲公民。
【兩個公民】以對美國的詛咒開篇。在那本詩集中,有一些關於俄亥俄我的家鄉的野蠻詩歌,如果沒有遇到安妮,我是寫不出這些詩歌的。她給了我力量,讓我可以同時坦然接受我所愛和所恨的事物。在這本書的中間,在詛咒和最後的悲傷表達之間,有一長串的愛情詩。我從沒寫過這麽令自己厭惡的書。不管別人怎麽看,我覺得這就是最後一本了。如果我再寫另一個,就讓老天收了我。
盡管我不喜歡那本詩集,但我喜歡它背後的東西,因為它直接源於我的新生活,我和安妮的生活。我們原計劃去歐洲旅行,但那時已是暮春,我正在努力完成【詩集】。我感到很空虛,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二次認為自己永遠與詩無緣了。我當時一直覺得我永遠與詩無緣了。後來我們在巴黎住了好幾天,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又開始寫詩了,它們變成了情詩,感恩的情詩。
巴黎評論:你的詩【詩藝:最近的批評】是關於文學批評的嗎?
詹姆士·萊特 :不是,這是首關於我的長輩艾格尼絲的詩,她是一個遭受了巨大痛苦的女人,緩慢垂死許多年。我對這個國家文學批評和現實生活之間的差異感到非常憤怒,我想我可能會寫一首自己的詩歌,講述這個國家真正發生的事情。
巴黎評論:你認為理想的批評應該是什麽樣的?
詹姆士·萊特 :向年輕詩人傳授技藝和想象力之間關系的至關重要性。因為沒有技藝(我指的是積極運用智慧),想象力這種神秘而可怕的東西,就不可能自由。我們必須自己學習很多東西,而你們,年輕詩人們,能夠看到默溫、迪基、勃萊、金內爾、斯塔福德和瑪麗·奧利弗(她有著獨特的純凈和溫柔),我的意思是,美國的可能性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形式可能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教材和課堂。
巴黎評論:在我們的交談中,你提到了幾位非常優秀但幾乎被遺忘的詩人——愛德華·湯瑪斯、魯伯特·布魯克等。當然,你還有一首間接寫給艾德娜·聖文森特·米萊的詩。為什麽我們總是忘記這樣的好詩人?
詹姆士·萊特 :我沒有答案。你怎麽解釋人們把約翰·多恩遺忘了幾百年的事實?我們不可能一下子記住所有事物。我們確實擁有一些人物,他們理解面對死亡和痛苦時生活的強度和真正的美。除了愛,我們還能擁有什麽?我們必須擁有它,因為除此之外唯有死亡和痛苦。我認為,這就是那句震撼人心的話的意義,「上帝是愛」。整個文化都是圍繞這句話而建立的。(刪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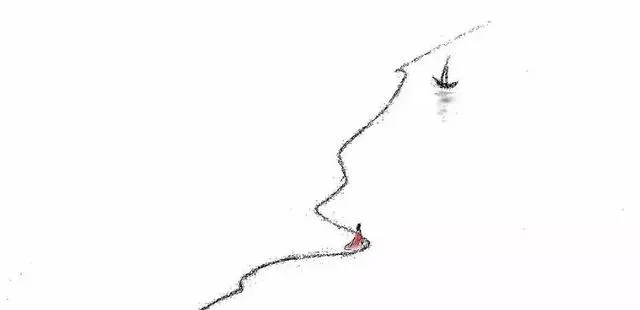
昨夜的龜
——詹姆士·萊特
我記得昨日暮色中他清秀的樣子。一下雨,他便在老地方登場了,他從殼裏露出來,盡情伸展著——腳,腿,尾巴,頭。他似乎很享受雨,甜美的雨,從上阿迪傑地區¹的山裏一路飄過來,涉過湖水找到他。我從沒有這麽近距離看一只龜完全攤開身體愜意地沐浴。傳說中那些風燭殘年的臉,頷下堆疊的肌肉,充滿野性和敵意的鼻孔,露著兇光的雙目,都從我腦海中消失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甜美的山雨,他的青春活力,他獨自洗澡時的莊重,他虔誠的臉。
今天早上,我坐在窗邊,對著下面的青草看了很久。就在剛才,那裏還是一片空曠。可是此刻,他在綠色陽光裏馱著斑駁的龜殼爬上爬下,喘息著經過。一條看門的黑狗在他旁邊抽著鼻子熟睡,不過,我相信他倆誰都不怕誰。我看見他仰起臉。對著光亮挑起眉,下巴極其輕微地轉動著,那是一種古老的喜悅,一種渴望。
他的喉部有些暗黃色小褶皺,那顏色跟甘菊花田飄搖過來的花粉一般無二。從他臉部的線條中,你只能看到愜意,還有他對青草的微妙洞悉,猶如我在俄亥俄一位流浪漢臉上看到過的專註和柔情,那流浪漢坐在貨運火車的無蓋車廂上,對著無人的麥田揮手致意。
如今,那列火車已不復存在,龜也已離去,只在空草地上留下了一個圓圈。我對著他逗留過的地方看了很久,但是,空空的草地上找不到一個腳印。還剩這麽多的空氣,這麽多的陽光,但他還是走了。
註1:上阿迪傑地區(Alto Adige),義大利北部的一個區,全稱為「特倫蒂諾-上阿迪傑」,曾屬於奧地利。該地區有 30% 人口以德語為母語。
(張文武 譯)
詹姆士·萊特:【再度喚醒世界】

時光當鋪 NO1
萊特:【河流之上】簽名本

時光當鋪 NO1
保羅·策蘭:我聽見石頭開花了

時光當鋪 NO1
詩論訪談專輯:
巴黎評論:
詹姆士·萊特:巴黎評論訪談
訪談隨筆:
「從現實到超現實」——記詩人馮晏詩歌創作&朗誦交流會
陳先發:中國藝術報訪談
娜 夜: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訪談
宋曉傑:詩探索訪談
湯養宗:詩探索訪談
詩論禮記:
朱賓:詩者,天地之心
趙屹:寂寞是上帝授予詩人的一枚勛章
趙屹:我們的寫作應該從什麽地方出發
趙屹:想象是一個詩人的護照
趙屹:孤獨是寫作最好的處方
趙屹:每一個漢字都是通向神的
【時光當鋪】特別推薦
李元勝主編詩人最滿意的10首
【我是你獲得世界的一種方式】68元
【這世間有我已經不能更好了】68元
陳超【生命詩學論稿】布面精裝58元
李元勝老師主編的詩人自己最滿意的十首詩二輯,堪稱當代「 詩三百 」,陳超老師的【生命詩學論稿】是經典的詩論詩評,讀這三本書,了解當下詩壇動態。
可以掃碼加微信購買,或者掃文末時光當鋪書店付款碼直接輸入資訊購買,備註也需填寫才能付款!簽名本很有限哦…… 更多好書可以點選手機屏底的選單欄:時光書店→掃碼購書
備註:詩歌,圖片,音樂,視訊選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冒犯請聯系我們立即刪除,致敬原作者 。



詩論訪談專輯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