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四度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詩人勞勃·弗羅斯特(1874-1963)。
一、詩是意義之音
「詩」是龐然大物,是雲間漂浮的一頭並不輕易現出全身的「大象」,也可以是一棵小草,在微風中搖曳,給它下一個簡單而確定的定義並不容易。也許是為自己的詩辯護,勞勃·弗羅斯特給詩下過很多定義。沿著這些「定義」掘出的小徑,或授權以抵達弗羅斯特詩歌的秘境。
什麽是詩?弗羅斯特給出的第一個定義是:「詩是已經變成了行動的言辭。」這句話與緊跟其後的一個表達可以互釋:「詩是實際說話之語音語調的復制品。」(【幾條定義】,【弗羅斯特集】第905頁,曹明倫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以下參照該書,僅註頁碼)這個定義,特別看重詩歌語音語調的獨特性和準確性,強調口語的力量,奠定了弗羅斯特一生的語言風格。
所謂「已經變成了行動的言辭」,意味著詩是言語的定型,並且本身便是一種行動。怎樣才能使詩成為一種行動呢?弗羅斯特說:「不論長短,每一首按格律寫成的詩都是一種信念,對一條道路的信念,意誌必須沿這條路一步一步去實作一個承諾,直到有個圓滿的結局。」(第991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行動是意誌展現的過程,是一個「猛烈消耗」的過程。意誌源自真實的生活,源自生活和世界本身,但並非所有的日常言語都是行動,行動意味著詩人必須對現代及現代人說話,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另一方面,「詩是實際說話之語音語調的復制品」,表明弗羅斯特看重口語語音語調的再現,並早在尚未成名之時就提出了「意義之音」(sound of sense)這一術語。
什麽是「意義之音」?弗羅斯特認為,近代詩歌的成就基於一種基本假設——即詞句的音樂性是個使元音輔音和諧的問題,斯溫伯恩、丁尼生等人就曾把主要目標放在二者的和諧上,眼下大多數詩人在走同樣的道路,而這是一條死胡同。他不吝自誇地說:「在用英語寫作的作家中,只有我一直有意地使自己從我也許會稱為‘意義之音’的那種東西中去獲取音樂性。」然而怎樣才能得到那種抽象之音呢?他說,「最好是從一扇隔斷單詞的門後的聲音之中」。在他看來,意義之音「是純粹的聲調——純粹的形式」:
意義之音也不僅僅是音韻。它是意義和音韻二者之結合。有價值的格律只有兩三種。為使其有所變化,我們依靠的就是意義之音中重音的無限變化。情感表達之可能性幾乎全在於意義之音和單詞重音的自然融合。一種精妙的融合。(第871頁)
「意義之音」這個神秘的術語,是弗羅斯特的一個「發明」,他不滿足於英語常用的抑揚格、揚抑格的音步變化,強調語調的表意功能。他追求的不是眼睛(視覺)之詩,而是耳朵(聽覺)之詩。在【會想象的耳朵】這篇演講中,他說:
在我自己的寫作和教學中,我總想引進活生生的口語聲調。因為某些句式依賴於聲調是個不爭的事實;——譬如說,請註意鄉下人用「我想也是」這句話表示嘲諷、預設,或懷疑等時的不同聲調。但重要的問題是,你能把這些聲調寫在紙上嗎?你如何辨識聲調呢?根據上下文,根據在活生生的語言中得以表露的情緒。而你們認為有多少種聲調在飛來飛去呢?有許許多多——許許多多還沒被寫進書裏的聲調。(第891頁)
他曾對自己那首總是被置於卷首的【牧場】加以分析,列舉了每一行詩句的語調,試圖證明輕松的語調、告知的語調、自由的語調、勸誘的語調、邀請的語調究竟是怎麽樣的,還借助其他詩句解釋何謂威脅的聲調、說笑的聲調、質疑的聲調。在寫給華特·伊登的信裏,又列舉了自誇、揶揄、懷疑的聲調,他所關心的「只是捕捉那些尚未被寫進書中的句子聲調」,那是真正原始之物,在字詞出現之前就已存在。弗羅斯特的這個概念,是在遵從傳統格律的同時,捕捉現代口語的調式,從而構成了獨特的語調和韻律。究其實質,這是一種語調意義的自我指涉,即語調本身在傳遞態度、情感和意向。
除了語調,弗羅斯特認為「詩永遠都是語言的新生」,「是那種使我們永不疲憊的東西」,「是那種使世界永不衰老的東西」。他所說的語言的新生,一方面指的是「一種對意義的執著——執著地要凈化字詞,直到它們又重新具有它們應該具有的意義」(第962頁),另一方面則是從日常語言中發現隱喻,基於情感更新詞語。他說:「情感可透過比喻使字詞暫時離開其原位,但通常的情況是最終將其移到新的位置。習俗、形式和言詞都不得不有規律地或無規律地從精神實質上被更新。這就是真正的激進之信條。」(第1013頁)情感是新生的原動力,而新生意味著詞從原來熟悉的位置上移到一個新的位置,並因此獲得飽滿的漿汁。這種詞語的位移,弗羅斯特稱之為「挪用」或「遠距離挪用」,即透過隱喻、類比、諷喻或其他遷移手段來實作跨領域的語意對映,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陌生化」。

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1885-1972)。
從寫作生涯的一開始,與埃茲拉·龐德、艾略特走向晦暗的自由詩不同,弗羅斯特傾心於一種源自口語的格律詩,透過「凈化」來為普通詞語「灌漿」,為的是讓詩走向大眾。他1913年11月5日致約翰·巴特利特的信中寫道:
請時時記住一個值得記住的事實:有一種叫「受到尊重」的成功,而這種成功是靠不住的。它是指一種由少數被認為懂行的評論家吹出來的成功。但若要真正達到以詩人的身份獨立於世的境地,我必須走出這個圈子去面對成千上萬買我的書的普通讀者。我也許沒有能力做到這點,但我堅信這樣做會有益處——在這一點上你不必為我擔心。我想成為一個雅俗共賞的詩人。我不能像我的朋友龐德那樣,以成為那幫高雅之士的魚子醬而沾沾自喜。(第873頁)
這是詩人一以貫之的理念。1918年1月致瑞吉斯·米紹的信說得更明確:「我堅信口語化是任何一首好詩的根,正如我堅信民族性是所有思想和藝術的根一樣。只要這些根名副其實並紮在該紮的地方,你就盡可以讓你的作品之樹長得高聳入雲,枝繁葉茂。人個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而且我正想冒昧地說另一半就是口語化。」(第897頁)從弗羅斯特的詩歌生涯來看,他完美地將地域性、口語化融於一身,獲得了民族性的同時,也獲得了世界性。
二、詩是對憂愁的過分誇張
弗羅斯特關於詩的第二個定義如下:「詩始於喉頭的一陣哽咽,始於一絲懷鄉之戀,始於一縷相思之情。它是朝向表達的一種延伸,是想得到滿足的一種努力。一首完美的詩應該是一首激情在其中找到了思想、思想在其中找到了言辭的詩。」(第906頁)這個定義可以分成兩部份理解:前半部份指向詩的起點,後半部份指向詩中情感、思想與言辭的關系。
詩,緣起於悲哀,也緣起於歡欣。弗羅斯特在【始終如一的信念】中說:「寫詩動筆前的唯一要求就是內在情緒,那種至少能讓詩人哪怕是牽強附會地寫下一兩個字的情緒。這就好比穿針時線頭最前端那一截肉眼幾乎看不見的細絲,它必須最先穿過針眼。詩人必須為那種準確的預感而欣喜若狂。」(第993頁)那麽「哽咽」「一絲懷鄉之戀」「一縷相思之情」便是那個「線頭」。不過要完整把握這個定義,需與弗羅斯特晚年「詩是鋪張」定義聯系起來理解。1962年11月27日,已經八十八歲高齡的弗羅斯特在達特茅斯學院進行了一次演講,提出了「從很多方面看,詩也是一種鋪張」的主張。年至耄耋,依然精力充沛,思慮精深,可以說這是弗羅斯特詩學的最後一次宣示。這種「鋪張」,首先是對痛苦與憂愁的誇張:
詩是對憂愁的過分誇張。不滿是一種可以消除的東西,而憂愁卻沒藥可治。你只有懷著一種快樂的哀愁接受憂愁。(第1117頁)
這或許是關於詩歌本質最好的表述之一。弗羅斯特有資格這樣說。他的一生,頂著一代詩傑的桂冠,飽嘗了親人死亡的憂愁痛苦滋味:二十六歲,年僅五歲的長子病逝,年底母親病逝;三十三歲,女兒出生三天即夭亡;六十歲,女兒產下一子後患產褥熱去世;六十四歲,妻子去世;六十六歲,兒子用獵槍自殺。但是詩人很少直接描寫這些死亡,而是把它們深深掩埋起來,以一種象征性方式「鋪張」出來,比如他的【家葬】一詩。在【悲傷與理智】中,布羅茨基對【家葬】進行了逐句細讀,將男女主人視為理智與悲傷的象征,而敘述者則是二者的結合。這篇出色的細讀文本,忽略了(或不屑於關註)這首詩的事實層面。【家葬】收錄於【波士頓以北】,很可能與女兒埃莉諾·貝蒂娜的夭亡有關,逼真地再現了夫妻之間的分裂與隔閡。布羅茨基敏銳地洞察了詩中的戲劇張力和象征意蘊,如果多關註一些事實層面的哀愁,將更完美。

在【悲傷與理智】中,布羅茨基(上圖)對弗羅斯特的【家葬】進行了逐句細讀。
弗羅斯特曾為艾德溫·阿林頓·羅賓森的【賈斯帕王】寫過一篇序言,是弗羅斯特是探討悲哀的一個重要文本。弗羅斯特身上有其狡猾、世故的一面,當他應邀為羅賓森詩集作序時內心不情不願,並在給友人的信中對羅賓森大加嘲諷:
這個無精打采的老酒鬼是徹頭徹尾的浪漫派。他對詩人的想象如白朗寧夫婦對【賓·瓊森】的想象,他看待出軌的情人和戴綠帽子的丈夫的方式和【崔斯坦】裏的完全一樣。全是文學俗套!我好像置身在熱氣球裏的熱空氣中一樣。我完全無法接受他。自從他出版【河下遊的小鎮】,我沒讀過半次他的詩。我的耳朵根本受不了所有那些維多利亞時代之後瞎扯的亞瑟王時期的胡話。(轉引自傑伊· 帕裏尼著、雷武鈴譯【勞勃· 弗羅斯特和生存之詩】,【上海文化】2018年5月號)
傑伊· 帕裏尼認為弗羅斯特從羅賓森那學到不少東西,欠著一份不肯承認的恩情,我倒認為弗羅斯特的序言寫得如此完美,主要不是欠了羅賓森的情,而是在自抒懷抱。他從羅賓森那裏看到的悲哀,實際上是他自己的悲哀。他在序言中說:
但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喜歡抱怨。不管它們是哪裏出版的,我發現我總是輕輕地把它們放到一邊。我喜歡的是悲哀,而且喜歡它們羅賓森式的深沈。(第946頁,譯文有改動)
弗羅斯特傾向於讓散文、小說來表現不滿,「允許詩歌流著淚去走它自己的路」,「悲而不怨」。他接著評價羅賓森:「在無數另一類痛苦者中,羅賓森是傷心者中的傷心王子。他用以工作的真誠全是悲哀。他維護詩椎心泣血、歌其極悲的神聖權利。讓刁鉆小人去動肝火吧。我深知何處去尋找憂思。」他緊接著給出一個又一個警句:
抱怨是急躁的一種形式。悲哀是耐心的一種形式。
悲哀走多遠,理性和信心也走多遠,絕不多走一步。(第949頁)
弗羅斯特聲稱自己手裏攥著「堅韌不拔的悲哀」,同時又高度贊美羅賓森「從不讓悲哀能走多遠就走多遠」。難道這不是弗羅斯特在夫子自道嗎?難道同樣的聲音沒有在他最後的演講中再次喧響過嗎?「節制的傷感」,幾乎與弗羅斯特等值。在這篇詩一樣的序言中,悲哀的聲調一直復沓、延伸到結尾:
給我們一些無法消除的悲哀吧——一些我們沒法對付的悲哀——一些明確無誤的悲哀。然後演戲吧。演戲是惟一的手段。演戲是惟一的手段。德行盡在「仿佛」之中。(第953頁)
「演戲是惟一的手段」,是哈姆雷特的立場和把戲,難道不也是弗羅斯特後半生的立場和把戲嗎?穿過長長的歲月的甬道,他扮演著信念、勇氣、悲哀和智慧本身。「仿佛戰爭已結束」,但並沒有結束,弗羅斯特的生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跟悲哀的舞蹈還要跳上三十年。
三、詩是慢慢流出的激情
關於【家葬】一詩,布羅茨基還說:「我想,他所探求的就是悲傷與理智,這兩者盡管互為毒藥,但卻是語言最有效的燃料,或者如果你們同意的話,它們是永不褪色的墨水。」「悲傷越多,理智也就越多。」說得真好啊!它是進入弗羅斯特詩歌世界的不二法門,可是似乎還不夠。「一首完美的詩應該是一首激情在其中找到了思想、思想在其中找到了言辭的詩。」要理解弗羅斯特的思想和智慧,需要我們對弗羅斯特第二個定義的後半部份更進一步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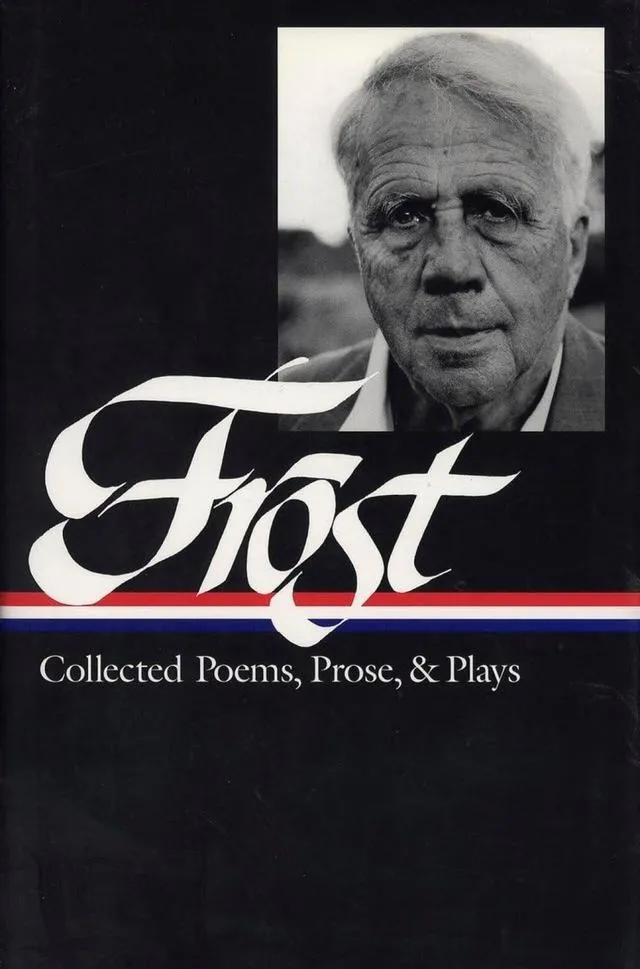
美國文庫版【弗羅斯特集】。
何謂理智?從詩歌美學上來說,理智是對「混沌的暫時的遏制」,是將悲哀控制在一定量度之中的技藝。這種節制,透過詩歌的韻律排程、語調掌控、詩節設定、結構安排體現出來。他的詩基本上采用抑揚格或揚抑格,詩句較長,節奏舒緩,很少出現強烈的情感。不滿常常流於憤激與對抗,悲哀則是內斂的,張力也是內斂的。需要註意的是,弗羅斯特所說的「詩是鋪張」,並非毫無節制的放縱,也是在一定規矩下的「鋪張」。他說:
激情之流必須被攔住並被規矩控制在理智磨坊內,不能任其奔湧咆哮如脫韁之馬。若不用規矩堵住堤壩所有細孔而只留出一個出口,激情之力量很快就會耗盡。須知情感應該慢慢流出。(第1013頁)
這段話完美地解釋了弗羅斯特的節制美學。詩並非華麗的辭藻,也不是放縱,而是「慢慢流出」的激情。
1960年,接受【巴黎評論】采訪,弗羅斯特說:
在一首詩中你能展現的技藝可謂多種多樣。你會涉及形象,涉及始終都在變化的音調。要知道,當我有三四個音節時,我的興趣總是在於句子在詩節中的組合方式。我不願讓句式在詩節中毫無變化。每首詩都像這樣:某種技藝的成功展示。有人說過,除了是別的什麽之外,詩尤其是智慧的結晶。它也許深藏在什麽地方——智慧的結晶。詩中必須得有智慧。而許多矯揉造作的詩基本上沒考慮這點,壓根兒就沒有智慧的火花。
「技藝的成功展示」是美學上的,智慧則是思想上的。理智並不必然通向智慧,它是工具和方法,仰賴於反省、洞察和領悟,才能抵達智慧。他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詩乃心之所悟。我相信那就是卡圖盧斯的mens aniums 所表達的意思。」(第1243頁註)卡圖盧斯的這個拉丁語措辭,即是一種「野性的條理」,是思想感覺到的東西,是「對混沌的暫時遏制」,是高於理性的一種智識。早在高中畢業致辭中,弗羅斯特就堅定地認為「生活是一種反省」,「詩人對事理的洞悉便是他的反省。那是改變了節奏的心跳,是與自然的交流。而最偉大的思想往往產生於最末一行詩寫成之際」(第841頁)。終其一生,弗羅斯特屬於比較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具有很強的反省性,小到割草、走路之類的農事,大到國家政治,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的洞察和關切。在那篇短小的【幾條定義】中,他區分了兩種現實主義,一種是拿出的馬鈴薯總是沾滿了泥,來說明他們的馬鈴薯是真實的,另一種則把馬鈴薯上的泥弄幹凈才感到滿意,弗羅斯特屬於後一種,這意味著藝術要做的就是「凈化生活,揭示生活」。
一些人總是抱怨時代很糟,弗羅斯特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人世間的所有年代都很糟糕」,一個人不可能知道我們所生活的年代是否最糟糕的年代。重要的不是世界多糟,而是「畢竟世上還有那麽多好東西,這就允許形式的存在和形式的創造」。1956年4月,他在奧勒岡大學演講時再次強調:「詩歌必須與現實生活全面關聯。詩中總有一個核心句子來自生活中的瑣碎言語所包含的洞見之一,也就是智慧。詩歌若不具有這樣微妙之處,我就不認為它有價值。」(【勞勃·弗羅斯特校園談話錄】第89頁,愛德華·C·拉什姆編,董洪川等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7月版)他既不是悲觀主義,也不是樂觀主義,而是洞察了黑暗與混亂,試圖為之尋找美學形式。這是詩人的使命。
弗羅斯特的詩中,不僅有悲哀和智慧,還有泰瑞林所揭櫫、布羅茨基展開來的恐怖,後者源於前者,又強於前者,而且常常是對死亡魅影的凝視。弗羅斯特的【步入】【雪夜林邊駐馬】等詩,呈現出一個樹林、動物、黑暗的意象系統,是詩人的核心原型,多次在詩中復現。凝視「從遠處立柱支起的黑暗」以及可愛、深邃、幽暗的樹林,便是凝視死亡。詩人沈迷於此,但是理智阻止了這種沈迷。他一則說:「我是來看星星的。」再則說:「我還有諾言要踐履。」在弗羅斯特看來,每首詩都是巨大困境的一個縮影,是意誌勇敢地面對陌生障礙物的一個想象,智慧把人從中喚醒,提供了「脫身之道」。
四、詩適於我們所擁有的最深刻的思想
詩要保持節制,那麽如何控制其尺度呢?這需要引出弗羅斯特的第三個觀點:「詩可以從多重意義上來界定,而不是僅僅從一種意義上;它是有韻律的音步,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恰如其分的量,即我們能夠說出並願意說出的意思總量。最終評判我們所根據的就是我們知道該在何處戛然而止的那種敏銳感覺。」(第918頁)那麽怎樣才算「恰如其分的量」?如何達致那種「恰如其分的量」呢?

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上圖)1980年出版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已經成為名著,但這本書想要表達的意思,弗羅斯特早在五十年前就說過了。
這個恰如其分的量,並非客觀測量所得,而是主觀感覺的產物,需要借助形式、隱喻、語言、風格等要素達成。這個「恰如其分的量」,不是那種天然熱情的「震耳欲聾的呼喊」,也不是炫目的陽光,而是「透過智力折射而投撒在一種有色彩的螢幕上,投射過程從誇張——或者誇大其辭——的一端到輕描淡寫的另一端」,「是由暗色線條和多種色彩編織的一道長帶」,「擁有穿過一種思想時的全部色彩」(第923、924頁)。也就是說,這個「量」是一個情感和隱喻的對映區間,是「受隱喻控制的熱情」。弗羅斯特是一位隱喻大師,早在1930年就指出隱喻是人類最基本的認知方式,全部思維都具有隱喻性,這比萊考夫等人早了五十年。喬治·萊考夫和馬克·強森合寫過一本【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較為通俗地論述了人類的這一認知方式,開篇感謝了一大堆人,唯獨沒有提到弗羅斯特。這本書的觀點,只是弗羅斯特觀點的展開而已,書名或許也是從弗羅斯特那裏拿來的。弗羅斯特說:
詩始於普通的隱喻、巧妙的隱喻和高雅的隱喻,適於我們所擁有的最深刻的思想。詩為以此述彼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第924頁)
這種隱喻是「邁向偉大、莊嚴、永恒之思想的最初幾步」,那些千百年來所積累的「高貴的隱喻」全都具有思想性。這是因為「每一首詩被寫成,每一篇小說被寫成,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信念」,因為「一種美,一種莫可名狀的東西,某一事物的一點魅力,往往都是被作者感覺而非被他確知」(第931頁)。用技巧寫成的詩,安排得像個陷阱,靠信念寫成的詩則適於感覺。同時他還提出了因為詩的熏陶而形成的四種信念:自我信念、愛的信念、國家信念、文學信念。這聽起來有些矛盾。我認為弗羅斯特所說的信念不是某種定型、僵化的觀念,而是活生生的真實之感知,——其中確實存在著某種或一些信念,它們確確實實在那兒,但又搖曳不定,進而形成信念的色帶和區間。這種信念,或許就是弗羅斯特所說的智慧的一種形式。
關於這一點,弗羅斯特還有一段精妙的表述:
我的詩中有許多搖擺不定的東西。裏面有某種機敏,某種確定的東西,但它在其錨位上漂搖,在其確定的錨鏈上漂搖。而這當然就是它的趣味所在。(第1025頁)
這種確定性中的不確定性或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是弗羅斯特詩的本質特征,也是魅力源泉。例如【選擇某種像星星的東西】一詩,詩人仰望星空,跟一顆星星說話,那麽那顆星星到底指什麽呢?1962年在達特茅斯的那次演講中,他說那顆星可以指【一千零一夜】,可以指作者喜愛的詩人卡圖盧斯,可以指【聖經】中的某句話,可以指某種遙遠的東西,可以指某種在遠方樹林裏的東西。每個人可以依據自己的理解獲得領悟,然後一化為十,化為百千,不確定性與確定性和諧共處。這首詩最初的真正誘因,是從長期以來試圖理解現代詩人的努力中獲得的:「你們看,讓他們去神秘吧。那是我的寬宏大量——就叫它寬宏大量吧。」(第1149頁)這首詩雖然以感嘆詞「啊」領起,但開頭部份卻彌漫著對於那顆高傲的星星的嘲諷,這其實是對以艾略特、龐德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派的嘲諷,但並不是那種強烈的、不能共容的嘲諷。
五、詩是晨暉降臨的新鮮感
關於詩,弗羅斯特還有其他一些論斷。他說:「一首詩就是一種諧戲。」(第1023頁)這當然不是一個嚴格的定義。一個詩人發現詩意,就像一個喜劇演員發現了喜劇性。講笑話也有技巧,詩人和喜劇演員都不能毫無顧忌地把包袱抖出來,笑話必須要有點內涵,方式必須是個人性的,或許還需要點漫不經心,但總蘊含著天真、洞察力與機智。諧戲還要有度,流於諧謔便是對讀者的戲弄。
1959年,弗羅斯特跟新批評幹將庫林斯·布魯克斯、勞勃·沃倫有過一次關於詩藝的談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
我喜歡有保留地說,我可以這樣為詩下定義:詩就是在轉譯時從散文和韻文中消失的東西。那是指語言被彎曲(或隨你用諸如此類的什麽詞)過程中的某種東西——話被講的方式,你說話的方式。(第1064頁)
「彎曲」(curved)是一個富於弗羅斯特色彩的詞。那麽在「彎曲」的過程中消失的是什麽呢?其中一定有某些意義和文化的損失,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旋律和某種新鮮東西的遺失。很多詩轉譯成另一種語言,變得平庸了,在「彎曲」的過程中幾乎被折斷了。一個詩人彈撥琴弦,他也許在演奏兩種交合在一起的旋律,經過轉譯以後,那兩種旋律已遺失一大半,而兩種旋律所生發出來的東西則可能所剩無幾了。就像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雪夜林邊駐馬】一詩中間有許多「意義之音」,在轉譯中很難保留下來。比如「sweep,snow,stop,some,sound,sleep」這些以「s」開頭的噝擦音頭韻詞,模擬了雪落的「沙沙聲」,而「wind,wood,will,without」等以「w」開頭的頭韻詞模擬了風吹過的「嗚嗚」聲(參見汪翠萍【現代牧歌——勞勃·弗羅斯特詩歌研究】第19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在轉譯中幾乎都失去了。再如【海龜蛋與火車】一詩的前半部份,使用了以「k」收尾的「kick,tick,track,wreck,click,clank」等詞語,模擬了火車那種「哢嚓,哢嚓」的聲韻,轉譯過來也完全喪失了。再以艾蜜莉·狄金森的一首小詩為例:
奉蜜蜂-
與蝴蝶-
與微風之名-
阿門!(【花朵與漩渦】第32頁,海倫·文德勒著,王柏華譯,廣西人民出版社,2021)
在漢語語境中,這很難稱之為詩。回到狄金森的語境,詩味濃郁。它是對【聖經】「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的戲仿,「彎曲」以後,蜜蜂(Bee)、蝴蝶(Butterfly)、微風(Breeze)的頭韻以及象征性消失了,詩人以自然為宗教的立場幾乎也消失了,也就是說那種旋律和新鮮的東西一起消失了。因此,弗羅斯特對轉譯作品持有敵意:「對於感覺,當今的另一危險就是習慣於讀轉譯作品。形神兼備的譯詩非常少見,這應當是一種警告。」他承認有些譯文在適當的時候有用,但遠遠沒有被「馴化」為譯入語,對一個自信的人來說,「總會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遺憾」(第1015頁)。不得不承認,弗羅斯特的說法切中要害。

【弗羅斯特集】的中譯者曹明倫教授。本文所配圖片,均為資料圖。
同樣是在這此談話中,弗羅斯特還提出了另一個說法:「我經常說詩的另一個定義是天亮——當你在寫詩的時候,它是你朦朦朧朧感到的一縷晨暉,如果最後真的天亮了,它將隨著陽光的射出而消失。這種天亮的感覺——這種天亮的新鮮感——你在真正天亮之前並沒有仔細考慮過,你並沒有把它寫成散文然後再轉譯成詩。」(第1065)前一個定義強調詩在轉譯中消失的東西,這一個強調詩誕生時的感覺。最美妙的,是等待晨暉的降臨,抓住它,但不知道究竟會抓住什麽。作者如此,讀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勞勃·弗羅斯特詩學的核心是什麽?一言以蔽之,詩是悲哀與智慧的舞蹈,詩人的工作就是尋找忠實於真實生活的「意義之音」和形式。
(本文原題「悲哀與智慧的舞蹈」,現標題與小標題均為編者所擬)
張憲光
責編 劉小磊











